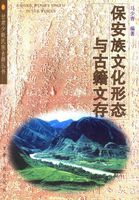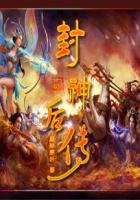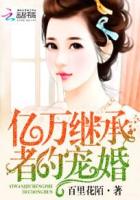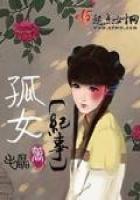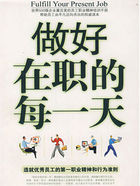在宋、明五百年的历史中,王阳明称得上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儒家人物。在哲学思想方面,其心学体系一反程朱道学正宗,引领明末清初启蒙思潮和实学思潮;在政治事业上,王阳明叱咤风云,扶保明朝江山。他顺利地践履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声名播于后世。
传奇辉煌的一生
王阳明(1472~1528),浙江余姚人,本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等人的学说,创立了阳明学派,形成自己独特的心学思想体系,在中国儒学史上影响甚大。
王阳明出生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2)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自幼酷爱读书,据说他5岁时还不能说话,11岁跟着父亲到北京的金山寺时却能够豪迈赋诗、出语不凡。王阳明于21岁在家乡中举人,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从此开始了官宦生涯,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主事。
正德元年(1506),武宗登基,宦官刘瑾弄权揽政。王阳明不顾兵部主事职小,仗义直言,结果遭害下狱,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驿丞。第二年在赴任的路上他又遭到刘瑾的心腹追杀,不得已抛弃衣冠,假装投江才幸免于难,最后于正德三年(1508)三月抵达龙场。就是在这个万山环抱、荆棘丛生、艰苦孤寂的偏荒之地,他悟到了“圣人之道”。
刘瑾死后,王阳明政治地位上升,被任命为巡抚,掌管一方军政。王阳明不仅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文才出众,而且能骑善射,武艺高强,尤其善于用兵。在赣南,他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消灭了数十年占山为王的“巨寇”。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造反,声势浩大,一举攻占九江、南康,进攻安庆,大有顺流而下夺取南京之势。此时,武宗自封“威武大将军”御驾亲征。不料王阳明率兵奇袭宁王大本营,将宁王活捉,而此时武宗的军队还在河北。
后世文臣武将树王阳明为楷模,不仅是因为他的“武功”,还因为他提出了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即“阳明学说”。
坎坷的思想历程
明代的理学在王阳明以前程朱学说盛行。程朱理学虽然势大,深得官方青睐,但由于其思想体系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思想和方法支离破碎,使为数众多焦灼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对其失望乃至望而生畏。
王阳明中举后随父旅居京师,遍读诸子之书,对于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思想很欣赏。按照朱熹的说法,“格物致知”就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意思是说事物的道理是可以逐渐得到认识的,今天认识一件事,明天认识一件事,日积月累,就会达到与事物的至理相通的地步。为此,王阳明与一个叫钱友同的好友一起到庭院的竹林深处去做“格”竹子的实验,来体会其中的道理。钱有同只“格”了3日,便心力憔悴。王阳明坚持了7天,最后也病倒了,没有“格”出一个所以然来。两个人最后的结论是圣贤做不得。
由于对朱子之学产生了怀疑,王阳明改攻辞章之学。但是随后他会试两次不第,于是读兵书、谈养生、留心于武事,兴趣有了很大改变。他31岁时回到家乡养病,在阳明洞中筑室研习道家导引之术。这一时期,他的兴趣非常广泛。湛甘泉说他“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直到谪贬贵州龙场驿丞,才真正归于儒家圣贤之学。
王阳明被贬贵州时,途中到湖南岳麓书院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讲学,又将岳麓书院的办学方法带到了贵州,在贬谪地创办书院。那时他对“格物致知”仍然不太理解,于是钻研佛老学说,也无所收获。在贵州龙场驿困顿的环境下,由于穷荒无书,他只得日绎旧闻,苦思冥想3年,终于在37岁那年的一天深夜突然悟出“格物致知”的道理,认识到“圣人之道”的基本要旨在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即只需自求于心,而不需求诸物。这就是所谓“龙场悟道”。
这里不得不说陆九渊的思想对王阳明的影响。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又提倡“心即理”的学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的学说,被称为“陆学”。陆学和程朱之学有很大不同,陆九渊和朱熹曾在鹅湖展开过有关“理”与“气”的大辩论。王阳明在龙场所悟之“道”,明显带有陆学的色彩。从此之后,他正式舍弃程朱,归心于陆九渊,并逐渐形成他独特的心学思想。
因此,从王阳明的思想历程看,他在为学的初期并不是反对理学,崇尚心学,后来才发生转变,是从程朱理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一位思想家。
博大精深的心学
王阳明的思想中包括知行合一说、格物论和致良知说三大主题,它们之间有着互诠互释,相互贯通的内在联系,这体现了王阳明思想的整合或合一的特点。
前面提到王阳明年轻时遍览朱熹之书,笃信其格物学说,后来他在实践中发现无论是即物穷理还是循序读书,都不能解决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因而对格物致知说产生怀疑,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这套理论的内在矛盾。王阳明认为朱熹注重学问致知而不重身心修养,导致后来者以为必须先知,然后才能行,将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割裂开来。他认为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弊病必然会危害现存的社会秩序。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学说的批判,王阳明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他的心学思想体系。
王阳明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理”也就是陆九渊所说的“心即理”。认同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一切从人的内心来寻找本源,所以他的学说又被称之为“心学”。在王阳明看来,朱熹将心与理一分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以至人们追求学问的同时忘记修身的本身,导致整个社会的人心叵测,道德日下。依据自身的良心说,王阳明认为进行一切道德评判的标准就是良心,良心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因而心外当然无物,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格物之理”。这样王阳明通过对自身主体的重视,尤其是确立所谓内心标准,彻底地改造了所谓的物由理在的观点。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还以本体之正。
针对朱学求知于圣人先贤和经典著作,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哲学概念,主张求知于个体之内心,通过道德的自觉和智识的磨炼来达到道德和思想的进步。“良知”之说来源于《孟子》,指“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把“良知”二字看得很高,将“良知”说成儒家文明最精华、最具永恒性的观念,能让人超脱患难生死。后来,王阳明又在“良知”前面加了一个“致”字,把它发展成为“致良知”的主张。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对朱熹格物致知说进行改造,突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良知即是天理,良知是先验于人们心中且不假外求的道德本源,“致良知”要求人们首先应该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把这种良知天理推及万事万物,万事万物也就都有它的天理了。通过致良知学说,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全过程,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体系中另一个重要内容。知识与行为从来都是生活中密切联系的两个内容。人们一方面需要从行动中吸取经验,提炼为知识,同时行为本身又在既有的知识指导下进行。知与行构成了哲学中的一对基本命题,受到中国哲学家长期的重视。王阳明对知与行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关于阳明的知行论,最受赞誉的是“行而后有真知”,他在《语录二·答顾东侨书》中说:“食味之美勿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那么知与行在时间和逻辑上是否合一呢?在这方面王阳明淡化时间问题,而突出逻辑上的一体关系。王阳明在《语录一》中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即知行两者逻辑上是一个整体,谈不上先后。这里的行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实际上是专指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一种所谓克己功夫。王阳明与朱熹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有所不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调和折中。他认为朱熹所着力强调的在知识增进上下功夫只是达到致知的途径之一,此外还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与朱熹、陆九渊等人齐名的儒学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形成了陆、王学术流派。他特别提倡书院讲学,并在书院教学中阐明完善其思想学说。明代书院的兴盛与王阳明有很大的关系,他桃李遍布天下,阳明学说也成为当时的显学。阳明学说出现,明代学者多蜂起从之,一时蔚成风气。自明中叶至清初,王学仍是主流,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可见其流传之久,影响之深。阳明哲学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学说还传至日本,形成日本的阳明学,在日本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王阳明学在韩国也很受人们重视。事实上,王阳明学构成了东亚儒学的重要成分,对于今天人们对东亚的文化认同,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