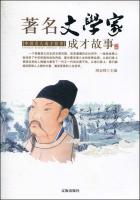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个负心的小国、达官显贵的妒忌和群氓的讥嘲,因此,由我来传布基督教也许是最合适的。明斯特主教的丝绒祭服和大十字勋章就留给我留作纪念吧!
个人——群体——由上帝来看。
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即使在公民大会上当众受人指控时,眼睛里见到的仍不是群众,而是个人。
灵魂的优点就是它看重个体,而且只重个体。可是,我们大多数的人仍是感性占上风,只要抬高了感性,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一旦我们只看到群众这一抽象群体,我们就偏离了本我。
但是在上帝眼里,在无数的灵魂眼里,芸芸众生,曾活着和正活着的芸芸众生,他们成为不了一个群体,上帝看到的只是个人。
那些批评家们,求你们手下留情吧,我实在受不了这些人,如街头流动的剃头匠那样背着剃刀箱尾随我,刮完了还要用湿漉漉的手指来捏我的脸。
我被我的工作逼近了能力的极限,我越来越紧张了,我孜孜以求用最清晰、最优美、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思想和我的孤独,心无旁骛。难怪大家把我看成疯子,并且怠慢我(因为我对别的东西漠不关心)。倘若我也学学现在那些所谓的大名鼎鼎的人物,花十分之一的精力去追求理智,十分之九的精力去追逐名利,只专注于平庸的工作能否最大限度地得来金钱和荣誉,那么我也可以成为大名人的,享受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一个作家的生命就应当是展示真理,我也毫不犹豫地这样要求自己,或者说展示基督教宣扬的观念中的真理的一个小小例证。这种真理,绝不是那些身穿斜纹绒面呢、丝绸和丝绒服的人在礼拜天瞎扯出来的真理。年轻人,你要当心!当心那些牧师和诗人。当心牧师在礼拜天对上帝的寒暄(因为到了星期一的时候,他也变成嘲笑你的人了,而且就在礼拜天当晚,他就已经待在俱乐部里到处打听最新消息了,看哪个傻瓜在狂热地实践他的教诲,然后好去嘲笑那些天真幼稚的人)。另外,还要当心诗人吟诵出来的赞美,因为在刻板乏味的日子里,诗人和那些喊着干掉他之类的话的愚鲁之人一样。滥赌、狂欢、嫖娼、偷盗、欺骗孤寡、散播谣言等,这些倒还可以原谅,唯独不能原谅的是,强迫别人在生活中一定要奉行牧师,必须做礼拜,又坚决不许怀疑,如果不这样,就威胁说会遭遇撒旦,这是万万不可原谅的。
或者/或者(一次即兴演讲)。
结婚,你会后悔;不结,你也会后悔;结婚或者没结婚,你都会后悔;无论你是结婚还是不结婚,这两样你都会后悔。对这世界的愚蠢加以嘲笑,你会后悔;为这些愚蠢伤心,你也会后悔;嘲笑这世界的愚蠢或为愚蠢伤心,两样都会让你后悔;无论你是嘲笑这世界的愚蠢还是为愚蠢伤心,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与之相似的还有,相信女人,你会后悔;不相信女人,你也会后悔;无论相信还是不相信女人,横竖你都会后悔。上吊自杀,你会后悔;不上吊自杀,你也会后悔;无论你是上吊自杀还是不上吊自杀,你两样都会后悔。各位,这就是哲学的Hanbaran意思是统统,全部。和实质。就像斯宾诺莎说的,我不仅是在某些时刻想以不朽看一切,而是想要永远以不朽来生活。很多人认为自己是这么活着的,因为他们自动地将对立面结合或调和了。但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永恒真理背后是不蕴涵或者/或者的,而是一早就暴露在人前。因此,这些人所谓的永恒只是一个个被忽略的瞬间的串联,这些串联的瞬间是痛苦的,它将被双重的悔恨吞噬了。我的哲学之所以好理解是因为我只有一条原则,我甚至懒得去推衍这原则。在这里,必须要区分蕴藏在或者/或者中的连续辩证法与永恒辩证法。所以,当我说我没有推衍自己那条原则,也并不表示就与推衍出来的原则相反,它是这一原则的否定表达,从这儿我们知道,这一原则与别的原则是对立的关系,这包括由它推衍出来的原则或不由它推衍出来的原则。
我从不推衍我的原则,因为无论我是否推衍了我的原则,我都会后悔,所以,如果有哪个听众朋友觉得我的话有道理,那只证明他的哲学才华非常一般;如果谁觉得我的论点是向前发展了,结论也是一样。但由于那些关注我的话的人的缘故,虽然我的论述没有什么新意,但我要勇敢地去兜露那永恒真理,因为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安分守己,它蕴涵更高的哲学,但不去多管闲事。因为我一推衍我那条原则,我就会发现自己忍不住将它一直推衍下去,因为一旦停下,我就会后悔,如果不停,我也会后悔,等等。但是,我如果从来不开始,那也就永无停止之时,而对我来说,永恒的起点就是永恒的终止。经验表明,哲学的开头一点也不难。它开始于无,所以总可以开始。但对哲学和哲学家来说,难的是怎样结束。我的哲学中早已经排除了这个困难。在座的各位如果有谁相信我简简单单地停止就停止了,那只证明他缺乏探究的眼光,因为我不是现在停止的,我是一开始就停止了。我的哲学非常简练,这可以说是一项长处,而且不能被驳倒,因为要是有人想找碴,我完全可以说他是疯子。这么说来,哲学家真是可以时刻在不朽中生活了,与那沉浸在神圣回忆中的圣坦尼斯,只有某几个小时为永恒而活截然不同。
为什么我没生在尼波特皇家海军为一辈子服役的水兵和他们的家属建造的住宅群名称。1817年,里面的孤儿院失火,有好几名儿童罹难。克氏在这儿用这个地名可能是联想到了这件事。?为什么我没死在襁褓中?如果那样,我父亲就会将我钉进木盒里,抱着它,在某个星期天将我带到墓地,然后撒上土,轻轻地念叨几句话就完了。只有在那年轻快活日子里,那埋葬在善人乐土里的婴儿才会啼哭,嫌自己死得太早。
我从未获得过幸福,可总觉得幸福就在我身边,紧紧地贴着我。快乐的精灵仿佛在我周围狂舞,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他们的眼睛在快乐的光芒里闪烁。只有当我走到人们中间,并且觉得如神灵一般幸福快乐的时候,他们就来妒忌我了,妒忌我的快活,于是我大笑起来,因为我从心里瞧不起人类,而且还伺机向他们寻仇。我从不想欺侮幸福的快乐精灵,但总是尽力让他觉得如果离我太近,就会受辱吃亏。每当听见别人颂扬自己的忠诚义节的时候,我就想偷偷地笑,因为我从心里瞧不起人类,并且还向他们寻仇。我一般很少对人硬起心肠,但如果我要故意这样做,我就做得像样,就好像我的心已经与人类情感完全背离和脱离了。每每听见有人感叹自己心地善良,见到人们爱戴地供奉这所谓的深广的感情,我就要大笑,因为我是真的瞧不起人类,并且还向他们寻仇。每当我见到自己因为冷漠因为无情而受人诅咒、忌讳、痛恨,我就要大笑,然后就不会再感到愤怒了。要是这些好人们真的能欺侮我,要是他们确确实实能让我心情不快去欺侮人——好吧,那吃亏就吃亏了吧。
毋庸置疑,这是我的不幸:我身边追随着的总是死亡天使,而我偏不去上帝选民的门楣上溅血,警告他应该避开。不,他进的正是自己要进的门——只有在回忆中存活的爱才能带来快乐。
即使酒也不能让我的心儿快活起来:喝少了我伤心,喝多了我忧郁。我的灵魂昏晕了,什么也做不了。我徒然地用刺马钉刺那快乐的腰窝,可它已倾尽了力量,再也不能支撑起那伟大的一跃了。我的幻觉也失去了。我即使纵身跃入快乐的无边大海也是白费心思,它已经无法托起我,或者说我已经无法支撑自己。要是这一切是真的,那就是快乐向我召唤了,我就会攀住它,驾轻就熟、安详、无畏、靠近它。慢慢地穿过树林,那感觉就像飞翔,而这时马身上已经全是汗水,几乎累倒在地,我似乎一动没动,看起来还是像以前那样孤独。看来,我被抛弃了,不是被人类,他们早已不能加害我,我是被快活得疯疯傻傻的仙子们抛弃了,她们过去总爱簇拥着我,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的,总是让我到什么地方都能遇到熟人,在任何地方都把快乐显现给我,就像一个醉醺醺的人身边围绕了一帮野小子。她们追随我,翩翩起舞,这些快乐的小仙子,我用微笑问候她们。我的灵魂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潜力。要是我有什么愿望,我一定不要财富和权力,我只要一种对潜在之物的热切的感受。这种感觉我曾经有过,但丢失了,我只想失而复得,因为永远年轻、热诚的眼睛永远盯着那可能之物。快乐让人失望,可能性却从不这样。世间没有一种美酒像可能性这般晶莹璀璨、芳香,让人沉醉。
音乐能进入阳光无法进入的深处。我的房间漆黑、阴沉,高墙几乎把白日的光隔绝了。从隔壁的院子里传来了音乐声,可能是某个流浪乐师在弹奏。是什么乐器?长笛?我听到的是什么——原来是《唐·璜》中的小步舞曲!我不可避免地被打动了,噫,这陪伴着少女的,让舞蹈变得感人的音乐是多么丰富美妙,而这时周围的情景是什么样的?药剂师敲着乳钵,厨子擦着水壶,马夫一边梳刷马儿,一边用梳子叩击大石板,只有我被这些音调吸引了,它们召唤——只向我一个人。啊!无论你是谁,请接受我的谢意!我的灵魂因此而更丰富了,更安适快乐了!
鲑鱼虽然是一种难得的珍馐,但太多了就是祸患,它会夺走你的胃口。有一次,大量的鲑鱼被捕捞后运到德国汉堡,警察局只好下令每个户主一星期只能让仆人吃一顿鲑鱼。对人们内心的伤感,我希望警察也下一道这样的命令。
烦恼是我受封的城堡。这城堡像鹰巢似的高踞在直插云霄的山巅,谁也没有办法攻下它。我就像鹰一样从高处冲入现实世界,擒获猎物,但我接着就飞回来,从不耽搁一分钟,我将猎物带入高高的根据地。我的战利品是一幅画,这幅画织成了我居住的宫殿的绣帷。我在那儿像死人一样生活着。我将所有的经验全部浸入到遗忘的洗礼中,使它们从此尘封并且永恒。遗忘抹去了所有短暂的偶然之物。我像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一样坐在那儿,头发花白,沉思无尽,我解释着一幅幅画,我的声音低柔得如私语一样;我身边坐着一个孩子,他在听,虽然在我开口之前,他便已明白了一切。
在某个星期的下午,明亮的太阳光闪闪地照进我的房间,隔壁房间开着窗户;街上,一切都是宁静的。隔壁少女住的花园里有云雀清脆的啼啭,我在这里能清晰地听见。我听见远处的街上传来一个男人卖虾的声音。空气温暖、轻盈、让人沉醉,但这座城市仿佛已经死了,于是我想起了我的青春和我的初恋,那时的我是多么强烈地憧憬着一切啊!那最初的向往现在又是多么难忘。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个梦。爱是什么?爱是梦的实质。
一件神奇的事发生了。我被提升到了第七重天堂,所有的神都围坐在那儿,他们特许我可以为自己许个愿。神的使者问我:你是想要青春、美貌、权力、长寿、美人,还是富贵荣华?他接着又说:你随便挑,但只能挑一样。那一刻,我真不知道如何选,然后就向神们宣布:最最尊贵的神们,我只想挑一样,那就是,我想在想笑的时候就笑出来。众神皆不回答,而是笑了。我的愿望被默许了。我还发现,神很懂得如何含蓄而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要是他们真的板起脸,很严肃回答我的问题,那就不太合情理了,像这样,嗯,你的愿望已被恩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