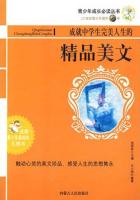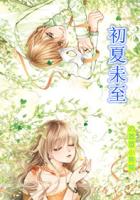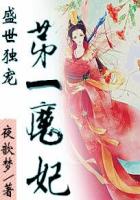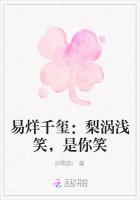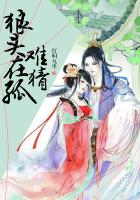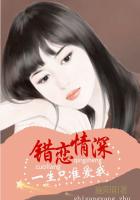2009年初,当《叙事》(中国版)第一辑正式出版时,作为主编,我心里实际上是惴惴不安的。在美国,《叙事》(Narrative)是非常有影响力和分量的一份学术期刊,其稿源来自世界各地,世界知名的叙事学专家经常在《叙事》上发表最新论文。当《叙事》经过长途跋涉,“旅行”到中国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时,她会以一种什么面貌出现呢?这无疑会引起中国学界同仁的关注。正是这份关注,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一份近乎崇高的责任。所幸的是,《叙事》(中国版)得到了国内外很多叙事学专家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肩负的压力转化成了动力和努力。国内叙事研究权威专家、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的申丹教授在听完我的计划后,不仅给我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还同意出任《叙事》(中国版)的顾问。2009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中国第二届国际叙事学研讨会”上,很多国内知名的叙事学者也都向我提到了《叙事》(中国版),并给予较高评价。云南大学的谭君强教授认为《叙事》(中国版)“为国内学界提供了国外叙事前沿研究动态,非常有价值”;四川外语学院的熊沐清教授认为《叙事》(中国版)“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用价值,将对国内叙事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对外经贸大学的许德金教授认为《叙事》(中国版)“为中外叙事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些知名教授的评价,既是对我们的首肯,也是对我们的期望。实际上,《叙事》(中国版)的宗旨就是:站在国际学术前沿,推动国内相关研究,提供高水平交流平台。
正是在这个宗旨下,我们组织了《叙事》(中国版)第二辑的编辑工作。经过主编、副主编认真思考和多次磋商,我们为本期选定的焦点话题是“病残叙事研究”。Narrative 曾经于2007年第1期组织了“病残叙事”专刊,我们从中选译了两篇,其中,《叙事、病残与身份》探讨的是残疾人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然后通过叙事来强化这种身份,并在法律上争取相关权利;《论病残案例中叙事的多重角色》则探讨在为病残人士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各方人士(包括律师、公诉人或者其他代言人)应如何克服社会对病残人士的刻板叙事,并尊重病残人士自己的叙事。这两篇论文均探讨叙事在法律中的作用,属于“跨学科”的叙事学研究。为了让国内读者了解“病残叙事研究”这一框架如何应用于虚构文学作品分析,我们特翻译了《叙事》2004年第1期发表的一篇论文《海明威早期的疾病叙事和〈此刻我躺下〉的抒情维度》。这篇论文认为,海明威的疾病叙事没有简单地叙述医生和病人之间如何通过交流,成功(或者没有成功)地找到疾病的治疗方法,而是将叙事重点放在病人经历创伤之后,如何再现自己的创伤经历。因此,海明威的疾病叙事不是单纯的治疗故事,而是具有“抒情维度”。在主人公的创伤叙述中,读者仿佛失去了主体性,无法把握故事世界中的一切,也无法对其进行阐释和伦理判断,但恰恰因为失去了主体性,读者能够把自己开放给他人,真正去面对他人的苦痛,从而证明海明威的疾病叙事具有列维纳斯(Levinas)意义上的惊人的“伦理力量”。
疾病叙事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①病人使用叙事来讲述自己的疾病和痛苦,以及重新建立被疾病所摧毁的身份(疾病叙事,包括病人亲属叙述关于疾病的影响);②医生使用叙事来归纳,传递医疗知识(关于疾病的叙事);③在医院使用叙事作为治疗工具(作为治疗工具的叙事)。其中,第一个研究领域为医学叙事学研究主流。病人(或其亲属)讲述他们的疾病,疾病产生的原因,疾病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后果,包括疾病为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自己的主体身份带来的变化。这样,病人可以重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语境和故事线索来探索疾病的意义。阿瑟·弗兰克(Arthur Frank)将疾病叙事归纳为三个阶段:①恢复(restitution)阶段,此时病人原来的生活(身份)没有改变;②错乱(chaos)阶段,此时病人原来的生活(身份)被彻底打乱;③追索(quest)阶段,此时病人追求一个新的自我。安·霍金斯(Anne Hawkins)认为疾病叙事经常基于某些反复出现的隐喻和神话,如战斗、旅行、再生等。疾病叙事作者可能使用规范的“文类”和叙事策略,以可辨认和可接受的形式来重组他们的生活和疾病经历,这些隐喻可以帮助病人组织讲述他们的疾病经历。本辑选译的论文《海明威早期的疾病叙事和〈此刻我躺下〉的抒情维度》虽然仍归属于以上提及的第一个研究领域,但该论文强调的是“创伤”经历讲述的限度,以及这类叙事的伦理内涵,因而有一定的创新性,希望对国内相关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在“《叙事》最新论文选译”一栏中,我们组织了四篇叙事大家撰写的论文。其中,英国伯明翰大学知名教授迈克尔·图兰(Michael Toolan)提出使用语料库文体学方法来研究短篇小说的叙事进程。纵观图兰教授的论文,他试图用统计学的办法来回答“哪些显著的文本因素可以成为读者期待的基础”这一问题。作为初步结论,图兰提出了八大类预示叙事进程的文本资源。很明显,图兰讨论的核心在于读者如何利用文本因素来预测短篇小说的走向,从而连贯地阅读叙事并对之作出准确的阐释。这一研究路径与芝加哥学派的Peter J。Rabinowitz以及美国短篇小说理论家Susan Lohafer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重点探讨读者阅读叙事之前会关注哪些文本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文本的意义和结构),后者重点探讨读者对短篇小说形成“终结感”(closure)的条件,即“文本信息与读者阐释之间达到平衡状态”。我们认为,图兰利用语料库研究方法来考察预示叙事进程的文本因素,虽然有借鉴意义,但也有缺陷,比如有些小说的叙事进程是由隐性文本线索来预示的,需要读者进行推导,在这种情况下,语料库研究方法就会显得力不从心。知名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使用其一贯的经典叙事学研究方法,对“逆向叙事”(backwards narrative)这一叙事现象进行了结构主义式的归纳总结。他超越热拉尔·热奈特的论述,区分了两类“逆向叙事”:闪回式(flashbacked)和持续式(sustained),然后根据闪回的时间长度以及持续的性质继续分类,直至分出六个“逆向叙事”类型。查特曼还用具体例证(均为影视作品)详细论述了这六个“逆向叙事”类型的表现形式。查特曼使用经典叙事学方法,关注古老叙事现象的新发展,说明即使在后经典叙事学占统治地位的今天,经典叙事学研究方法仍然有用,没有过时。除了图兰和查特曼,本栏目还收录了另一位知名叙事学家、《后现代主义小说》(Postmodernist Fiction)一书的作者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的新作《关于建构诗歌叙事学的设想》。麦克黑尔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叙事理论一直忽略了诗歌叙事这一重要领地。他提出了研究叙事与诗歌形式之间互动关系的构想。以讨论迪普莱西的“段位性”(segmentivity)术语为出发点,通过对荷马《伊利亚特》第十六章四种英译的个案分析,麦克黑尔重点探讨了叙事序列与诗歌文本的相互关系,以及叙事性与段位性之间的相互强化、相互对位、相互抵消的方式;显然,麦克黑尔的研究对我们很有启发作用:一方面,我们可以借用他的研究思路,继续探讨诗歌中叙事性与诗歌特有的段位性互动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特定时期的诗歌形式,探讨中国诗歌中叙事性的特征。鉴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特殊地位,我们认为,这也应该成为中国叙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建构“中国叙事学”的努力大部分集中在挖掘古代小说评点中隐含的叙事理论,以诗歌为对象进行的叙事研究在国内学界几乎还是盲点,我们期待麦克黑尔的这篇论文有助于改变这一现状。以色列海法大学的D。E。维康教授借助于俄国著名理论家巴赫金论著中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视角,对作为受话者与述行叙述者的主体—客体之“我”的叙事身份作了耳目一新的分析论证。相信,这对国内的叙事身份研究有较高的学术借鉴价值。
应用叙事学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重新阐释一直是《叙事》(中国版)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本辑选译了两篇论文,其中《无神论者的全知:论简·奥斯汀的“不犯错误的叙事者”》对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全知”进行了再思考。作者认为,奥斯汀小说叙事者的全知不是上帝般的,而是一种人力能及的技能:一个有感受力、勤于思考的人得到足够的时间和观察机会后,对别人的性格、思维过程和情感作出了准确的判断。这样,奥斯汀小说的叙事者既不能讲述他/她所不知道的过去和将来,也不能对人物作出高屋建瓴的评价,而只能依据已有的线索进行合理的判断。这篇论文的新意在于,作者将“全知”细分为四种表现形式,即无所不能的全知(omnipotence)、通晓古今的全知(omnitemporality)、无处不在的全知(omnipresence)、通晓心灵的全知(telepathy),并具体分析了这四类“全知”在奥斯汀小说中的体现。我们认为,这篇论文的价值不仅在于给读者具体分析了奥斯汀小说“全知”的特征,更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即使像“全知”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叙事现象,我们都可以对其进行重新审视,重新研究,并结合具体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我们从叙事学角度对作品进行研究时,往往喜欢使用涵盖范围极宽的“大术语”,这篇论文则告诉我们,即使是同样一个叙事技巧,不同作家使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深入探究不同作家的叙事策略。
为了凸现《叙事》(中国版)的交流性质,促进中西方就叙事理论进行探讨,本辑特向符号学领域国内知名专家赵毅衡教授约稿一篇,在这篇论文中,赵教授提出了建构“广义叙事学”(general narratology)的构想。顾名思义,“广义叙事学”旨在超越以小说为基础的叙事学,而将多种不同体裁的叙事作品纳入考察之中(比如影视、广告,乃至梦等)。以这一思路为出发点,赵教授提出了叙事的“最简单”定义,此定义包括两点:①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链;②此符号链可以被(另一)主体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然后从“虚构性”、“媒介”、“语态”三个纬度对不同叙事进行分类(详见本辑中赵教授的论述)。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叙事学通常把“叙事”定义为“事件/状态A朝事件/状态B变化的过程”,这一定义强调的是叙事的时间性和“事件/状态”的变化,虽然符合多数(文字)叙事的特征,但忽略了叙事的很多其他方面,比如非文字的叙事和即时性的叙事,叙事中隐含的主体和接受者等层面。赵教授的定义将叙事置于更为广阔的“符号”层面,超越了“文本”概念,同时结合现象学,将叙事讲述主体和叙事接受主体的意向纳入考察之中,从而超越了纯语言形式的定义。比如,在区分“虚构性”和“事实性”叙事时,就不能仅仅依靠形式特征(因为任何以语言或其他符号为媒介的叙事从本质上讲都只能是虚构),而应该考虑叙事主体和接受主体的意向:有些叙事,作者和读者会达成“合约”将其读成“虚构性”的,而另一些叙事则读成“事实性”的。
赵毅衡教授不仅在论文中提出了应该受到学界关注的“广义叙事学”这一概念,更提出了“中国叙事学界能否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以及“到底谁是西方叙事经典的权威解释者”这两个值得我们玩味和深思的问题。中国学界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要建立“中国叙事学”,但是照笔者看来,至今未看见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叙事学”理论出现,我们经常看到的仍然是对国外叙事理论的评价(以及一些细节性的批评)。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很少看到中国学界提出新的叙事学问题,更遑论作出解答。由此看来,赵教授的第一个诘问的确是有现实意义的。赵教授追问的第二个问题笔者更有切身体会。前不久,笔者给国内某权威期刊投了一篇稿件,试图对国外修辞叙事理论、可然世界理论、文本世界理论中蕴含的“阅读过程”理论进行比较鉴别。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修辞叙事理论中的“阅读过程”关注的是阅读的结果,可然世界理论中的“阅读过程”关注的是读者如何确定叙事世界的逻辑真值,而文本世界理论中的“阅读过程”关注的则是读者的认知过程。笔者的稿件通过该期刊的初审和复审之后,被送到某专家处进行“匿名外审”。不料,该专家只用一句话就判了该论文的死刑,认为论文“基础有错误”,因为可然世界理论和文本世界理论“本质不同”,前者仅关注“文本本身”,不涉及读者阅读过程,后者仅关注“认知过程”。这里就涉及“到底谁是西方叙事理论的权威解释者”这一问题,因为即使是西方“文本世界理论”(text worlds theory)的首创者(Paul Werth)和主要捍卫者(如Joanna Gavins)也都认为可然世界理论和文本世界理论的前提“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虽然在实际发展中,这两个理论的确有不同之处,比如前者更关注叙事世界的构成、性质,而后者更关注读者对叙事世界的认知过程。然而,无论是可然世界理论,还是文本世界理论,都是从读者出发,将叙事看成另外一个“世界”,两者都讨论了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的阅读活动。笔者提出的结论是:可然世界在讨论这一活动时重点讨论了读者如何确定叙事世界的逻辑真值,而文本世界则重点讨论读者的阅读认知过程。应该说,这一认识既指出了两个理论的相似之处,又指出了它们的不同之处,对国内相关研究可以产生一定作用,但那位匿名专家却拿出“唯一权威阐释者”的姿态,以不容辩驳的口气,对笔者的论文作出了根本性的否定。在此,我无意为自己的论文辩护(因为那位专家正确地指出了我那篇论文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只是赵教授的追问引发了我对学界的一些思考。
在Narrative众多优秀论文中,到底选择介绍哪些论文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幸的是,Narrative主编詹姆斯·费伦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就本辑而言,他不仅帮助撰写了“序”,还帮助我们选定了论文篇目。其次,我们还要感谢这些论文的译者,其中既有来自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同仁,也有来自国内其他大学外语院(系)的老师。翻译之难,众所周知,翻译不算学术成果,也众所周知,但他们都有为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不辞辛劳地逐字翻译,那份认真精神让我非常感动。在这里我尤其想感谢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杨晓霖老师,她不仅承担了大量教学工作,同时还兼做繁重的行政工作,但她仍然利用业余时间,认真校对了本辑中的很多译文。当然,我还要衷心感谢南方医科大学各位领导对《叙事》(中国版)的支持,我们相信:《叙事》(中国版)的编辑出版,将为把南方医科大学建设成“多科性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如前所说,编辑出版《叙事》(中文版)的最大初衷是为国内叙事研究同行打开一扇窗户,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国外叙事理论研究动态和水平,以便我们能够真正加入与国际同行的对话,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从而在国际论坛上发出中国叙事学者的声音。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标,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无论是所选篇目,还是译校功夫,都可能出现遗漏或偏误,请方家不吝指正。
唐伟胜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