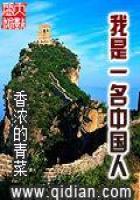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
忠实同志:
您好!
遵嘱拜读了您发表在《当代》第四期上的中篇近作《初夏》。杂志的编者把它放在一卷之首,它是当之无愧的。我读它,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亲切和喜悦的心情。
首先使我感到亲切和喜悦的,是您的作品保持着陕西作家在描写农村生活,处理农村生活题材时的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那种洋溢着渭河平原农村浓郁的生活气息的风格。在阅读之前,我曾问过读过这部作品的同志有什么观感。得到的回答是:像《创业史》,连一些人物都像。在我读完之后,却没有产生这种感觉,只是觉得在风格上有着上述共同之处罢了。
这种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上的共同之处,不是互相模仿的结果,而是来自作家们同人民群众、同革命干部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共同之处,是来自作家们同现实生活的关系的那种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中,摆在干部们之中。他们所描述的群众,是他们的父兄,姐妹,他们所描述的基层干部是他们的战友、同事,甚或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不把自己摆在生活之上,不认为自己是生活的见证人或审判官。如果有所针砭,有所干预,那他们也同时在针砭自己,或干预自己。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在作品中,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作家和他们所描写的人物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气氛,特别是同他在作品中所作的某种批评的人物之间的那种既严肃而又亲密无间的情调和气氛。您的《初夏》,正是在这一点上,使我深为感动。您对我们讲述了冯景藩老汉和他的儿子冯马驹的故事。您笔下的冯景藩,在当前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在一系列基层干部的形象中,可算得是一个新的人物典型。读着冯景藩的故事,只要是真正熟悉当代农村生活的人,就会一眼看出它的作者是从农村生活中走来的,是同冯景藩在农田基建大会战的工地上,或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中,是在一个麦草铺垫的通铺上滚过多年的。
您来自农村,来自基层,冯景藩们既是您的父兄,而您又曾是他们的领导。您曾同他们一起在一间茅草屋顶下度过困苦的生活,又同他们一道经历过解放的喜悦。您曾仰着脸看那年轻的共产党员冯景藩们是怎样的叱咤风云地带领群众反封建,斗地主,分田地;又曾见他们是怎样意气风发地率领群众,建立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迅跑。尔后,您又作为他们的同事和上级领导,带领他们在兴修水库,或在平整土地的大会战工地上,同他们一道,度过多少个风雪严寒而又热气腾腾的日日夜夜。你们有过共同的理想和欢乐,也有过相同的困难和烦恼。您是深知冯景藩们的,因而您笔下的冯景藩就显得格外真实和感人。在小说中,您虽然只用了极少的笔墨作了一点回叙,却也对冯景藩的一生作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这也正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公正的立场。
如果说,要寻找什么不足之处的话,我倒是觉得,您在描写冯景藩当前的思想行为方面,用文学行话来说,即人物的性格发展方面,是不是意念性的东西稍微显得多了一点?您告诉我们,冯家滩支部书记冯景藩,二三十年来,把他能献给冯家滩的一切都献出了,特别是出外当脱产干部的调令都拒绝了,然而到头来一事无成,联产承包使他感到幻灭,他从中作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自己忠诚工作吃了大亏。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度的变化,他认为现在对他来说,一是在公社养牛场给自己找个落脚之处,更重要的是给儿子在县上谋一份好工作,他因此而同当队长的儿子马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一切,您都写得很真实,合情合理,但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冯景藩毕竟是当过多年支书的老共产党员,大队的老干部,受过多年党的教育,在他和一心想把队搞好的儿子的矛盾冲突过程中,他的思想必定也是十分复杂矛盾,必定也同时在经历着剧烈的内心斗争的,绝不会像一个普通的农民群众那样简单,那样毫无顾忌。所以,您是不是把景藩老汉的思想活动,行动做法,对马驹的态度和举措,都处理和描写得简单了一点?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我便大胆地建议,您在出单行本以前,再加加工,从这个角度上,把景藩老汉好好地刻画刻画,我相信它将会带给您艺术家才能体会到的快乐。
您的其他人物:马驹、德宽、牛娃、来娃、彩彩,都写得很好。特别是马驹、德宽和来娃,形象鲜明,真实感人。而其中最突出的要数德宽了,您用您那惯常使用的朴素无华的白描手法所描写出的冯德宽,却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这儿表现出了您的艺术的功力。
还有一点我想要告诉您的,是从艺术地表现生活的广度和厚度上,在生活气氛的浓度上,同您过去的短篇小说相比,《初夏》可以说是个飞跃。您这些年来写过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普遍赞赏,我也是您的小说的赞赏者的一员。但您那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包括获奖的作品《信任》,您在艺术处理上,我这里说的是对生活的剪裁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剪裁得很干净。这是长处,也是短处。剪裁得过分干净,有时就会给人一种刮得太光太薄的感觉。《初夏》则颇不相同,生活的诗情画意之味,浓郁得多了,读起来令人常常沉醉。
只读了一遍,尚未细嚼,一点感觉和印象,拉杂写来,博您一笑。
您近两年来特大丰收,顺致祝贺!
握手!
王汶石
1984年10月8日
关于《夭折》的一封信
忠实:
您好!您发表在《飞天》今年三月号上的新作《夭折》拜读过了。祝贺您为读者献出了又一可喜的成果。
您的这部新作,不惟在题材上向新的领域突进,从您一贯塑造地道农民形象,进到塑造农村知识分子,写他们的远大抱负和坎坷经历,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显示出新的追求和新的特点。记得,在读了《初夏》后写给您的信中,我曾说过,您的小说,在艺术处理上,在对生活的剪裁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剪裁得很干净,它是长处,也是短处。剪裁得过分干净,有时就会给人一种刮得太光太薄的感觉。这个感觉,在读《夭折》时已经没有了。在这个中篇里,您通过对惠畅的半生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广阔的农村生活,特别是回乡知识青年的奋斗生活,读来令人感到亲切而又辛酸。由于您把惠畅这个人物放在农村广阔的生活背景上去描写,在写惠畅的生活和斗争的每一个环节上又处处不忽略其同周围生活的千丝万缕纵横交错的联系,因而,使人读起来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生活无垠和深不见底的感觉来。也许会有读者或某批评家觉得它不够精练,过分冗长,但这些缺陷在您是极易克服的。
在我看来,假如某个读者觉得冗长,那可能不是由于对生活素材剔除不够,而是由于情节不够,准确地说,是由于情节进展中的左冲右突和曲折不够,从而显得紧张力不够。当然,以写人写生活为主的小说,不同于情节小说,是不以情节紧张见长,也不要而且要有意避免以情节引人的。特别是短篇和小中篇。但即使如此,在故事进展中,也不能不注意情节,不能不注意主人公――不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结局是大团圆还是大悲剧――都是在曲曲折折的道路上行进的,几乎是一步一曲,一步一折,也只有这一步一曲折才会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关注,这也正是艺术与生活小有区别的地方。
我最感兴趣的是您的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真实感。在读您的作品时,我总好像置身于关中农村,一切都是那么熟悉、真实和亲切。无论对什么人什么事,抑或对任何年月的农村社会生活现象,好的或不好的,令人喜悦的或令人沮丧以至愤怒的事物,您都是既不夸大什么,也不回避什么。您的《夭折》正是这样一部小说,您的惠畅正是这样一个人物,您的秀花和马罗大叔也都是这样的艺术形象。多可爱的媳妇秀花和多可爱的农村长者马罗大叔啊!
您的小说题名《夭折》,是说青年文学爱好者、写作者惠畅夭折了,不过看您写的他的结局(其实还不算是结局),他并未夭折,可能只是一个大的曲折,照他现在在他的二层小楼上的作为,他很可能成为一位新时期的了不起的作家呢!
拉扯得太远,不便再耽误您的时间了。专此。
顺颂
文祺!
王汶石
1985年4月17日西安
旱原垅亩中的巨人
――读《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
陈忠实同志:
您好!
很高兴读到您和田长山同志发表在十月八日《陕西日报》上的报告文学大作《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您把您那秀美的文笔慷慨地献给了当代的一位普通而又优秀的社会主义新人,而且又写得那么生动感人。
社会主义文学像所有其他时代的文学一样,应该写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物,塑造各种不同的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真实典型,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品德和性格的人,自然也应该是它描写的对象。而且,为了给亿万群众树立新生活的榜样,它还应当把描写社会主义新人作为它的最主要的任务,用评论家的话说,当做它的主旋律。这也是党的一贯的文艺政策,是党的文艺政策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可是,曾几何时,在我们文艺界煽起了一股反英雄,反新人的妖风。一些人以反对“三突出”、“高大全”为口实,竭力诋毁和反对文艺作品塑造革命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他们以反对理想主义和写真实为理由,进而否认现实生活中有为社会主义而无私奉献的新人的存在。他们进而以寻根为由,鼓动作家艺术家,专门在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群众中挖掘和搜寻甚至臆造种种“落后”和“愚昧”,一时间,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充满了种种丑恶的以至不堪入目的描写;一时间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以至于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中国,倒成了一个浑浑噩噩、丑陋不堪的种族的世界了。这一切,客观上既是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盘否定,又起了为自由化精英们“全盘西化”和改换中国人种的狂叫而张目的作用了。
起初,在小说创作中,写新人受到了猛烈冲击;但在报告文学中人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描写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这是因为报告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评论界的那些反英雄反先进的好汉们,还不好否定现实生活中这些人物的存在,但是,这类作品的数量毕竟太少了,而且,到后来,那些专写落后阴暗的作家也进入报告文学领域,他们又专门搜寻和恣意渲染阴暗落后的东西,于是,报告文学以及受到人们重视的“纪实文学”,也逐渐向这边倾斜了。自然,揭露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人和丑恶的事,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痈疽,显示和抵制在开放改革中来自域外的和土生土长的种种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毒菌,同时也善意而严格地批评我们自身的缺点和失误,以维护和改善我们的社会主义肌体的健康,以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顺利地发展,这也是小说,特别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小说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也正是如此做的,其中虽然有些作品从社会效果上看并不理想,甚至会产生一些负效应,但其作者的用意,原本还是想要取得一些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效果。
现在已经很明白,也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虽然写的是个别事例或局部情况,但却透过个别涵盖一般,把攻击矛头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政治上另有打算,这一点,在“六四”前后,已由他们的代表人物说得很明白了。这个事实,人们是不应该忘记也不该避讳的。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人世间的事物总是循着辩证的逻辑在发展着,文学创作也在逐渐回到正常状态。近一年来,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又逐渐涌现在报刊、荧屏、银幕、舞台、广播、新闻通讯和种种出版物中,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文艺和种种传播媒介回到了党的文艺与新闻的轨道,而且在证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和性格的人,多如夏夜晴空的繁星;证明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并非像某些人说的是一种乌托邦,而是现实生活中真真实实的存在,且在日益发展,波澜壮阔,终将吸引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明天。不论这个过程需要多长多长。
我们现在所希望看到的乃是这一文学上的春风,能够从它已绿过的报告文学岸边,再以强劲之势,吹到小说创作的“原上”去。
您看,我一涉及这个话题,就刹不住车了,这是因为您一向也单是把笔墨主要献给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家,我也就有了按捺不住,一吐为快的心情。
现在说说你们的李立科。一如您一贯的风格一样,在报告文学上,您如在小说艺术中所崇尚的,表现出一种朴素自然的美,同别的报告文学作品是迥然不同的。
时下,或者说近几年来,报告文学最时髦的一种艺术手法是作者滔滔不绝的“画外独白”,创作者的所谓“主体意识”急剧膨胀,以作者自身的主体意识代替作品中主人公的主体意识。插入大段大段的独白,把古今中外各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拉来论说一番,把政论和哲学大量地有时是无节制地引入报告文学的艺术制造之中。我并不反对这种风格,相反,我倒常常喜欢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议论,只要适当,有时对报告文学来说,还是必须的,或者说作为文学的一个特种样式的报告文学,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因素,作者直接对人物和事件的适当评议,也便是这一文体的有机部分。事实上,不少这样的作品,其议论不仅对其思想内涵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也给人某种精神享受。当然,也应该说,相当多的这类作品是写得不成功的,它常常给人以与本题风马牛不相及和搔首弄姿故意卖弄的感觉,且不说那些故作高深,而实际上不懂装懂半通不通的掉书袋者了。
你们的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也正适合于描述李立科这样一位朴实自然的人。
无疑,李立科是一位形象高大的人,他所完成的业绩是壮丽无比的,引用多少古今中外名人名言来大段大段地赞美他,用多少“独白”的语言来颂扬他,都不会让人感到过分。李立科把他的灵感,他的智慧,他的热情,他的血和汗,他的健康,他的家庭和他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地献给了广袤的渭北高原,他用他鲜红的心血,把黄土高原染得更绿更绿。他使高原上的千村万户,光景过得日益峥嵘。
旱原,干旱高原,这个平常的字眼,只有在那儿生活过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它意味着什么。我自己从小生活在干旱高原上,与李立科从事科学实验的合阳县隔河相望,因而,我能够深深懂得合阳县以至渭北原上的成千成万的乡亲们,为什么对李立科副院长那样的亲,那样的爱,那样的信赖和尊敬。那儿,地面上没有溪流、没有涌泉,井,很深很深,汲一桶水,很难很难,人们惟一的依靠就是从天空降下来的雨水,人们把它蓄在土窖里,蓄在涝池里,人饮水,靠它,牲畜饮水靠它,一切需用的水全靠它;而地里的庄稼,对不起,它也只能靠天空洒下来的雨水来活命了,而干旱高原上的天,则是晴朗的日子多,降雨的日子少。旱地里的麦子、棉花、高粱、玉米、糜谷等等,全都是在如此严酷的水分极少的土壤上生根、拔茎、开花、结实,它们的收成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虽如此,自古以来,这儿就有着勤苦顽强的人民在生存繁衍,至今从未弃此而去的意思,他们世世代代在与天公干旱的斗争中,不断积累了一整套旱地农作的技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近代农业科学技术也来到了这块广阔的高原上。农业科学家来了,他们来,是要黄土旱原变低产为高产,贡献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陕西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李立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所领导的设在合阳县农村的陕西农科院甘井基地的科学家们,正是这样一个成绩卓著的集体。
李立科的思想性格,精神风貌,就像渭北高原的自然风貌一般,朴素无华,踏实沉稳,坦荡宽阔,浑厚纯真。他是一位掌握着近代农科知识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地道的黄土地的农民。他以科学家一丝不苟,锲而不舍的严谨精神,历尽风雪寒暑,日复一日地观察、记录、实验、研究,掌握旱原农作物生长状况,捕捉它的生长规律,探索出旱原作物生长的奥秘,总结研制出一整套旱原农作物增产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措施。他又像一位奋斗不息的教师,一村一村,一户一户,一乡一乡,一县一县讲授、示范,设计、推广;他同当地农民中的老把式一样,提耧、耙耱、赶车、扬场。干旱高原的农业起飞了,粮食和其他作物的产量翻番了,旱原人的生活面貌改变了。
李立科们是现代化农村的脊梁,李立科们,才是社会主义时代知识分子中的真正的“精英”,黄土地上的巨人。
你们的秀美清新、娓娓动听的报告,在表面的平静中跃动着火热的激情,让读者热血沸腾。最近,中共陕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全省人民向李立科同志学习,省广播电台,又连续广播了李立科的先进事迹,相信你们的报告将会吸引更多的读者。
如果有什么可挑剔的话,那就是有一个数字我心里还觉得不够踏实。你们文中说,直到一九八年,甘井乡小麦亩产平均只有四十八点五公斤,这个数字对我这个来自旱原的人来说,似乎有点偏低。就我的记忆,即便在过去,夏收场上,人们在张开口袋装粮时,总要议论一番当年收成。只要不是歉年,一般地说,平年一亩一桩,丰年一亩桩半(一桩四斗,每斗三十市斤)。解放后,虽然缓慢,但产量还是有所提高的。当然,可能是我错了,人们提供给你的数字,是一个乡的平均数字,自然会比我的一般印象科学而可靠。
我之所以对此敏感,是因为平时在听某些报告,或读报听广播,乃至读某些报告文学作品时,往往感到人们在肯定今日成就时,有意无意地压低甚至否定往日的成绩。因而,我们在采访和处理这类问题时,要格外谨慎。对待昨日的种种要实事求是,对待前人的业绩以至是非功过要公平,只有这样,才会有稳定与祥和,才会有发展与繁荣。我以为,这或许也应是当今我们的报告文学,自然也可以包括新闻通讯的写作,在作今昔对比时,应予以审慎考虑的。这当然是离开你们的作品的题外之话了。田长山同志不另。
顺颂
文安!
王汶石
199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