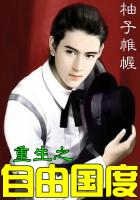在当时,猛烈攻击封建礼教比较出名的人物,还有吴虞。吴虞(1872-1949年),四川新繁人,早年留学日本,长期在成都教书,并在报上不断发表文章。1916年12月,他将自己的文章《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由成都寄给陈独秀,向《新青年》投稿,并给陈写了一封长信,表明自己的见解。陈对吴很赏识,称他为“蜀中名宿”,并把他的文章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吴虞对《新青年》能够发表自己的文章,感觉很荣幸,他在1917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之非儒及攻家族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此后,他便在《新青年》上不断发表文章。《新青年》三卷四号发表了吴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同时也发表了他妻子吴曾兰(香祖)所写的《女权平议》,他非常高兴。在1917年9月初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新青年》三卷四号一本,有余之《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篇,香祖《女权平议》一篇。香祖文后独秀识语云:‘此文作者吴女士,即又陵吴先生之夫人也’。可谓特别标识。”吴的文章,猛烈攻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孔子学说,特别对儒家提倡的孝、弟予以无情的鞭斥。他认为“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因而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于宗法社会,而不能前进。
吴虞早年思想,受老庄和李卓吾影响很多。他自向《新青年》投稿,参加新文化运动后,又受有鲁迅的影响。例如,他在《新青年》六卷六号(1919年11月1日)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教》,便是看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号,1918年5月)后引起共鸣而写的。吴虞说:“他(指鲁迅)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我现在试举几个例来证明他的说法”。
吴虞发表的激烈言词,曾震动一时,在思想界起了一定的影响,陈独秀说他是“蜀中名宿”;胡适说他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反对封建八股
八股文是15世纪到18世纪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
清代科举,沿袭前朝,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体为标准,分三级进行考试。每三年举办一次。县、府一级称院试,被录取者称秀才。省一级称乡试,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被录取者称举人。各省举人到北京参加最高级考试,被录取者称进士。进士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凡是考中举人和进士的人,就可以做官和享有社会特权。
因此,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是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孔夫子的教条。凡是违背这些教条的,就要被轻视、被申斥,甚至进“文字狱”。
那时的学者,在清初还是有些成就的,但从雍正、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后,学术的发展就停滞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与此相连,是考据学的兴起。如鲁迅所说:“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
清代八股文,不仅盛行于科举士人间,而且影响当时的文坛日趋摹古。雍正、乾隆年间,形成桐城古文派(以方苞、姚鼐为代表)。这一派主张“文以载道”,崇尚以“词章”宣扬“义理”,凡不合乎孔夫子的教条的,都不必写。这一派以唐宋以来古文派的正统自居,流行一时,成为清代封建文学思想的主要流派。和桐城派的散文相适应,还有“文选”(昭明文选)派的骈体文,刻意摹仿古典,滥用对偶排比,堆砌词藻典故。
俗儒好尊古,
日日故纸研。
六经字所无,
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
见之口流涎。
沿习甘剽窃,
妄造丛罪愆。
这是清末倡导“诗界革命”的维新派名诗人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中咏的几句诗,可说是切中时弊。“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凡是孔夫子没有讲过的话,都不能写进自己的诗文,这是多么严重的蒙昧教条啊!而这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清末以来,要求变革的志士仁人,早不满意这种蒙昧状况。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烂”。革命派陈天华则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体写出《猛回头》《警世钟》等那样妇孺皆能上口的宣传文字:“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猛回头》)。
清末也有人创制官话字母,提倡拼音文字,还有些人编了《白话报》、《白话丛书》(编者裘廷梁),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过,这些影响都不很大。
《新青年》创办时,其文学作品以翻译、介绍为主,大多是托尔斯泰(俄)、屠格涅夫(俄)、左拉(法)、易卜生(挪威)、王尔德(英)的作品,又由于用晦涩的文言文表达,所以影响也不够大。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在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大约从这时开始,《新青年》展开了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
胡适在留学期间,便不断向《新青年》投稿。1916年10月,他在寄《新青年》编者的信中,提出“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
接着,胡适将这八条,写成《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文字和顺序略有变动,但基本上还是那八条。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又将这八条名之为“八不主义”。
从以上的八条看来,胡适所说的“文学革命”,实际上只限于文体上的改革。这一点,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我的‘建设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1917年7月胡适回到中国后,到处演说“文学革命”,所宣讲的就是这种“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由此看来,胡适的所谓“文学革命”,就是提倡白话文的同义语。
新思想、新文学的反封建内容,需要新的形式去适应,以便于它的表达和传播。因此,白话文的提倡是有意义的。1918年后,《新青年》和新文化界比较普遍地使用白话文,有力地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学运动的开展。而且,白话文既然能够使语言和文字统一起来,就使文字更能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这对于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也是很有利的。
白话文有利于文学革命的开展,但提倡白话文并不一定就是文学革命。形式和内容并不是等量齐观的。白话文的形式,适合于新思想、新文学的内容,但它也同样可以装进反动的东西。文言文的形式,适合于封建思想、封建文学的内容,但它也并不是绝对不能为革命思想、革命文学所利用。把问题绝对化,就必然要犯形式主义的错误。
1917年2月,《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旗上亮明了三大主义: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样,《文学革命论》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仅限于文体,而是接触到内容了。
在讨论中,表现最激烈的是钱玄同。
钱玄同是一个激烈的语言文字改革者。他以“疑古”为号,表示对传统文化的坚决否定。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废汉文和废汉语的主张。他说:“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钱在这里虽然缺乏历史主义的分析,但他的改革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得很好的,仍然是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文小说的陆续出现,作出了典范,显示了“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些小说,“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这时(1918年),李大钊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他的《今》《新的!旧的》两篇著名论文,都是用白话写的。他还开始用白话写了一首《山中即景》的短诗,登在《新青年》五卷三号上。诗的原文是: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这是描写他的家乡昌黎五峰山的情景,读来给人一种清新、朴实、自然的快感,是自然的白话,是白话的自然,让人觉得新诗的可爱。
除以上所举外,当时积极赞助白话文的,还有刘半农。他在1917年3月就发表有《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在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后,他的作品主要是白话诗。
新文化运动兴起了。但由于这个运动没有和政治革命相结合,因此还没有引起敌对方面的注意。新文学家们“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可是“桐城”和“选学”却置之不理。这种情况,使新文学家们不免感到寂寞。为了引起敌对者重视,《新青年》同人不得不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扮演了一出双簧戏。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通信,用文言文的形式,以封建文人的口气,把反对新文学的主张一一罗列出来,表示对新文学的进攻(这封信用小号字体排印)。就在这封信的后面,刘半农作了一篇长达近万言的回答,对“王敬轩”的来信逐段(共分八段)进行了驳斥(这个回答是用大号字体排印的)。
新文学家们煞费苦心扮演的这场斗争,虽然也引起了一些反映(例如《新青年》的通信栏中有崇拜“王敬轩”者,也有反对“王敬轩”者),但是仍然没有引起那些“桐城”“选学”大师们的重视。
这种状况,到了1918年底和1919年初,文化革命和政治运动相汇合的时候,就有所改变了。那时,“新旧思潮的大激战”,已使新文学家们无寂寞之感了。
百家争鸣
社会历史当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时,随着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动,文化思想上也必然会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每一次的百家争鸣,又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诸子百家,学派林立,争辩不已。
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也先后在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地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恩格斯称那时“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这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而作为它们的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新文化,是必然要发生的。
但是,五四启蒙运动既不同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同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因为,它不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思想上的补课,而且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它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衔接起来了。
因此,中国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更显出了它的复杂局面。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两个阶段:
“五四”前的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新学”和封建主义的“旧学”之争。
“五四”后,即十月革命传入马克思主义之后,虽仍然是“新”“旧”之争,但是“新”的中间,却是百说杂陈了,有民主主义,也有社会主义;有马克思主义,也有修正主义;有国家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等等。当然,历史最后宣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但是,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正是“五四”前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所创造的百家争鸣局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当时入学者,为出身于举人、进士的京官,校舍在马神庙公主府。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一度停办。辛丑后,续办,并增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又增设进士馆(在太仆寺街)、译学馆(在北河沿)、医学馆(在后孙公园)等。清末宣统年间,改办分科大学,设有经、法、文、农、工、商、格知等科。
1912年(民国元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除经科归并文科外,余仍照办,(1914年,农科改为农业专门学校)。1916年,建寄宿舍于汉花园(旋改为教室)。
从1912年至1916年,先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者有严复、马良、何时、胡仁源等。历年各科毕业生数目如下:
蔡元培于1917年任北大校长后,将工科进入北洋大学,商科停办(商业学隶于法科)。这样,北京大学便逐步成为文、理、法三科。1919年,废去文、理、法各科名目,改称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采用分系制。第一院在汉花园,第二院在马神庙,第三院在北河沿。这时,学生人数有很大增加,1912年学生注册人数为800多人,而1919年则达到2000多人。教员人数也有很大的增长,1912年教员人数为53,而1918年则增长到217人。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重要改革是:
1.提倡学术研究。
1917年以前的北京大学,仍沿袭着京师大学堂的旧传统,不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而是一个谋求升官发财的阶梯。由于开办时收的学生是“京官”,所以学生一向都被称为“老爷”。有人回忆说:当时上体育课,教师发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而监督和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对教员的评价,不是看学术水平,而是看他在政府中的官阶。因为老师有地位,学生毕业后才有靠山。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预科毕业后,愿入法科,而不愿入文科。教员在这里也多是敷衍塞责,上课时照读一遍第一次的讲义,不管学生听与不听;考试时把题目和范围告诉学生,以避免学生的怀恨和顾全自己的体面。教员中很少有研究学问的习惯。
蔡元培到校后,首先针对这些陋习加以改革。他在就任的演说中,便对学生以“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事相勉。他在解释“抱定宗旨”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
2.展开百家争鸣
为了造成学术空气,必须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蔡元培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教育家,他对教员的选择,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下,《新青年》的编者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等,均被请来任教;同时,“拖长辫而持复辟论”的辜鸿铭,“筹安会之发起人”刘师培,也被请来任教;蔡元培虽在北大组织进德会,戒嫖、戒赌、戒娶妾,但教员中如有违反这些戒条的,也不过苛责备,因为他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来蔡元培是很懂得这一道理的。
对于各种学派,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自由争鸣,让学生自由选取。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又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3.对学生的政治活动,不予严格干涉
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虽不很赞成,但也不采取严格的干涉,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态度。他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4.中外教员,一视同仁
当时北京大学各科都聘有几个外国教员,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经过试用之后,发现学问并不都是很好,而且有的外国教员向不好的中国教员学,消极怠工。因此,蔡元培就按合同将这样的人辞退。有一个被辞退的法国教员声言,要控告蔡。一个被辞退的英国教员竟上朱尔典(英国驻北京公使)那里去要其和蔡谈判。朱尔典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竟摆出太上皇的姿态,放出口气说:“蔡元培是不想当校长了。”对于这些,蔡都置之不理,一笑了之。
蔡元培为了贯彻他的教育方针,在帝国主义分子威胁面前,没有屈服、退缩,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北京大学的改革,特别是文科的改革,使新文化运动获得一个有力的据点,使《新青年》团聚了更多的新文化人,使学生有了接受新思潮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同时,古老的北京,又是新旧思潮交锋的最前线。因此,这一改革,在五四运动史上是有意义的。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方针,尽管在主观上还反映了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性,但在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北大成为运动的中心,不是偶然的。
第四节 新世纪的曙光:一声炮响传革命
正是落叶惊秋的季节,俄罗斯传来一声炮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
革命导师列宁挥舞着他那强劲的巨掌,宣告了历史新纪元的到来。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汇合成一股汹涌壮阔的巨流,形成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世界革命的高潮。
孙中山说:“有了十月革命,便使人类产生了一个大希望。”
李大钊很形象地比喻道:“俄国的革命,不过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
1918年1月,日本巡洋舰驶进了海参崴,英国巡洋舰跟着也进来了。
一学生曾断左手中指血书:“案件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
李大钊是应永远怀念的,红楼也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划时代的炮声
1917年11月7日,北京香山的红叶已纷纷落地了。正是落叶惊秋的季节,北方的邻国――俄罗斯,传来一声炮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革命导师列宁挥舞着他那强劲的巨掌,宣告了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当日上午10时,列宁在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中写道: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立即提出民主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有了保证。
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
同日晚,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了。11月8日晨5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批准了由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宣布:“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同日晚,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列宁宣读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些法令。
大会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大会推举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11月9日,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
彼得格勒的起义发动后,莫斯科在11月7日晚也发动了起义,经过数天的战斗,反革命军队于11月15日投降。
彼得格勒、莫斯科起义胜利后,反革命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纷纷组织各种反革命的中心,和外国反动派相勾结并在其唆使下,阴谋发动叛乱。这种情况说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和巩固,还需要一个艰苦的战斗过程。
但是,十月起义终于胜利了,工人阶级已划时代地成为俄国的统治阶级。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其他一切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相同。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把人民从封建主义的剥削和枷锁下解放出来,但又给人民带来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把人民从一切形式的剥削和枷锁下解放出来。
为了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剥削阶级的一切反抗。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
1917年底和1918年初,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对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使军队中的全部权力转移到士兵苏维埃和委员会手中,并确定了建立工农红军的制度。
根据1917年底苏维埃政权颁布的法令,旧的司法制度被废止了,新的人民法庭成立了。
旧的警察队伍,还在二月革命的日子里,就被工人阶级摧毁了。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虽然组织过民团,但不是由劳动人民组成的。十月革命后,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民团,帮助苏维埃维持革命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