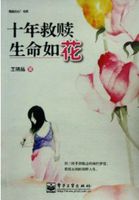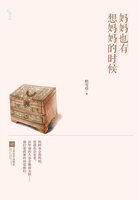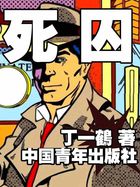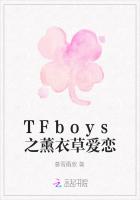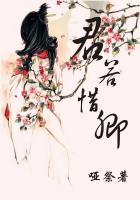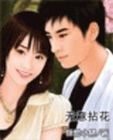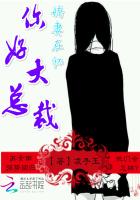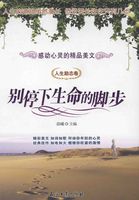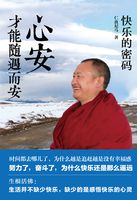曹禺写完《雷雨》,是在1933年。就在这一年,他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了。
他曾留在清华园里当研究生继续深造。但是,生活并没有使他滞留在高等学府宁静的书斋里;很快他就不得不在人生的道路上奔波流荡了。1934年,他到了河北省的一座古城——保定去谋生计,在一个中学教外语。不久,他又回到了故乡天津,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这种急速辗转的生活,使他对社会观察的视野扩大了,对社会的罪恶感受得更加深切而焦灼不安了。“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曹禺:《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
曹禺本来对天津的都市社会就比较熟悉。这个畸形的现代化城市,到处都是官商、流氓、妓女、烟馆、舞厅,还有大批失业人群。这个“东方的巴黎”,还充满了洋商、豪贾、买办、外国人。这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吃人社会。在天津,曹禺曾经有机会住过惠中饭店,得以深入观察那豪华大饭店里活动的人群。在这个饭店里,就有着像陈白露的交际花。在她周围吸引着一批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就有潘月亭那样的“大人物”。自然,作家也和福升那种人物打过交道。上海、天津都有金八式的人物,像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天津的高勃海等。天津人把高勃海这类人物称作“杂八地”。意思是说,他们在地方上有钱有势,称霸作恶。他们既是资本家,又是青红帮的大头目,手下有一批黑三式的流氓打手,同当地政府有较深的勾结。作家还亲自深入到天津三等妓院所在地——富贵胡同等地方,亲眼看到那些“可怜的动物最惨的悲剧”。这些,都化成种种的社会问题,使这个年青的剧作家原是按捺不住的习性更加愤懑了:“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的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同时他对这些问题追索答案的心情更加迫切了。“问题临在头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流着汗,急躁地捶击着自己,如同肚内错投了一副致命的药剂。”曹禺:《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
对万恶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恨,对劳苦群众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是作家进行创作的原动力。在年青剧作家的心胸中鼓荡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要“宣泄一腔的愤懑”。正是在这样的一股强烈的创作激情之下,《日出》终于在1935年末以其崭新的战斗姿态诞生了。1936年6月,开始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第一期上刊登,直到第四期连载完毕。
《日出》一经发表便轰动了文坛,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和讨论。最早是1936年到1937年之交,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组织的笔谈讨论。先后以两个整版发表了茅盾、巴金、叶圣陶、朱光潜、靳以、沈从文、黎烈文、李广田、荒煤、李蕤等人的文章,给《日出》以热情洋溢的肯定评价,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大公报·文艺》第273期,1936年12月27日;第276期,1937年1月1日。其中有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教授写的《一个异邦人士的意见》,该文指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我很愿知道作者由这些西洋戏剧家究竟有意识地承受了多少影响。作者心灵里实有一个预言者的激动,他看到了当前社会机构整个的腐烂,人类的贪婪,……残酷,……虚伪,……忌恨,……不公。这剧是对着藉投机和剥削而存在的整个寄生的社会机构一个严厉的攻击。……衬着并且存在这黑暗世界里还有光明的力量。”谢迪克:《一个异邦人士的意见》,1936年12月27日《大公报》。这位异邦人士对《日出》的评价并不过分。《日出》同那些世界上著名的戏剧作品并列是当之无愧的,而历史却埋没了这位异邦人士的声音。继之,便是在《光明》、《文学》等刊物上的讨论。黄芝冈发表了《从〈雷雨〉到〈日出〉》。他认为《雷雨》、《日出》“主要都只是‘正式结婚至上主义’和青年人都死定了留老年人撑持世界的可笑的收束”黄芝冈:《从〈雷雨〉到〈日出〉》,《光明》第2卷第5期。。周扬针对这种粗暴的批评写了《论〈雷雨〉和〈日出〉》,全面地论述了这两部作品的成就和不足。周扬:《论〈雷雨〉和〈日出〉》,《光明》第2卷第8期。欧阳凡海、张庚等也撰文参加了讨论。就一部剧作引起文艺界这样强烈的反响和讨论,这在话剧史上还是罕见的。从中也反映了《日出》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日出》发表的年代,被称作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第三次中兴”时期。当时,左翼戏剧运动发展较快,并创作了一批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的作品,而且在城市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职业剧团。但就创作来说,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剧目并不是很多的,一些剧团竞相演出的是历史剧和经过改编的外国剧。以1937年初轰动上海的春季联合公演为例,五大话剧剧团演出的剧目除阿英的《春风秋雨》外,均系外国作品。这种状况,竟然使一位美国戏剧家亚历山大·迪安(AlexanderDean)感到:“在上海的近代剧院,已达到戏剧历史最紧张的时期,而其成功乃优美的表演及导演者努力的结果”,“但此类剧院,严格地说,已失去中国剧场的面目,因所排演者均为西洋戏剧,……余甚希望数年之后当余重来此地时,得见一完全具有中国性质的剧院”亚历山大·迪安:《我所见的中国话剧》,《戏剧时代》创刊号。。当时,张庚曾指出了话剧创作把精力放到“外国剧本的改编”和“写历史剧”而忽视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倾向参看张庚:《目前剧运的几个当面问题》,《光明》第2卷第12期。。郑伯奇提出,新的观众迫切要求反映“跟自己生活有关系”的话剧。参看郑伯奇:《关于戏剧的通俗化》,《光明》第2卷第12期。他们在文章中肯定了《雷雨》、《日出》这样反映社会现实的剧目。因此,《日出》在当时的剧坛上出现,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并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了。
从演出效果来看,《日出》是深受广大观众热烈欢迎的。1937年2月,《日出》由欧阳予倩导演,上海戏剧工作社作了首次公演,引起观众的热烈欢迎。中国旅行剧团连续演出《日出》三四十场,观众始终保持满座。其后,南京、天津、汉口、昆明、重庆、成都、桂林以及革命圣地延安都相继上演过。《日出》还曾经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该报由叶圣陶、朱自清、杨振声、巴金、靳以等人组成的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对《日出》作者的评语是:“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责贬继之以抚爱,真像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够透视舞台效果。”1937年5月15日《大公报》。由《雷雨》到《日出》,终于使年青的剧作家坚实地站在话剧战线的战斗岗位上,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历史地位。
一“试探一次新路”
从《雷雨》、《日出》到《原野》(大约从1933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曹禺创作道路的前期。这段时间,正是曹禺的戏剧创作处于大胆探索、蓬勃发展的阶段,《日出》是他这个时期现实主义剧作发展的峰巅。
《雷雨》的创作已经表明了曹禺是一个思想和艺术都勇于探索的作家,《日出》更突出地显示了这样一个特点。如果说《雷雨》是作家以带有神秘色彩的哲学对现实作着窥视和探索;那么,《日出》则是作家以他达到的对现实的比较明确的认识,力求作出自己的答案。这样,就具有自觉的性质和特点。这种自觉性质的探索,使他在创作上提出要“试探一次新路”。
但是,对于作家“试探一次新路”的要求,虽然在历史上有过争论,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连作家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它的意义。批评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日出》的真实性上。如说:“剧中人虽都像活生生的,但就他们的真实性加以剖析,他们的影子便不免渐渐淡了。”有的说:“但这《日出》凡了解上海都市生活的人都认为它不真实,许多地方近于幻想。”因之,《日出》不如《雷雨》之说也就产生了。而有的评论直接对作家“试探一次新路”提出质疑,把它仅仅看做是个结构问题,于是说:“所以他现在还只能用片段的方法,人生零碎去阐明一个观念,而这个方法决不是艺术的大路”,“我疑心这是一条新路”。直到全国解放后,有些评论仍然从结构上来看“新路”,而没有联系时代的政治的文学的背景,从作家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变化上给予全面的深入的历史考察。“试探一次新路”之所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是因为它不但是作家在时代风雷激发下产生新的觉醒的体现,而且意味着作家在创作上朝着新的目标进行突破。当他决定去追求一条新路时,便不能不影响和决定着《日出》的整个创作面貌。现在,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作家是怎样提出“试探一次新路”这一课题的。他在《日出·跋》中说:
我想脱开了Lapiècebienfaite(即凑巧剧——引者)一类戏所笼罩的范围,试探一次新路,哪怕仅仅是一次呢。于是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起《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如若中间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结构”,那“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即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谓“结构的统一”也就藏在这一句话里。
的确,曹禺自己也把提出试探新路看做是个结构问题。但是,一个作家在艺术上探索新路,探求新的表现形式,总是由于他对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主题的探索而引起的。结构的创新归根结底是作家思想探索的艺术产儿。特别是戏剧的结构,不管作家是否自觉到这一点,当他结构他的戏剧大厦时,总是有一个思想出发点,或者说有着思想的支柱,才能把他的人物和事件组织在一个统一体之内。高尔斯华绥说:“完美的剧作家将他的人物和事实,围置在一个能够满足他的精神渴望的主导思想的圈子内。”转引自《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页239。《日出》的结构正体现着作家新的“精神渴望的主导思想”。这点,作家也没有规避。
他用“损不足以奉有余”来概括他对社会的认识。诚如一些评论指出,这个“基本观念”还是不科学的。但是,对于曹禺的思想发展来说却是一次飞跃。写作《雷雨》时,作家的“自己的哲学”主导方面是唯物的,可是却蒙上一层神秘的纱幔。对于充满斗争的冷酷和残忍的现实,他还“没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实相”。特别是在“主宰”问题上,使他陷入困惑之中。写作《日出》时,情况就不同了。尽管他还没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社会的认识也还缺少科学的阶阶分析;但是,他却借用老子《道德经》中的语言,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哲学”,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宇宙里的斗争”,而是对人吃人社会的“真实相”的粗略的概括。这正如周扬所说的:“写《日出》时,作者对于客观社会已有进一步的认识,他认清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人剥削人的制度。他已开始意识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对荒淫无耻的人们泄着愤懑,把希望寄托在象征光明的人们身上,而不再有对于隐秘不可知的事物的憧憬和恐惧,那种悲天悯人的思想了。他的创作的视线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他企图把一个半殖民地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脓疮社会描绘在他的画布上。所以《日出》无论是在作者的企图上,在题材的范围上,都是一个进步。”周扬:《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光明》第2卷第8期。还应该指出,作家对社会的新的认识,并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概念,而是从“包罗万象的人生”中,经过“静静地深思体会”,“参悟出来个中的道理”。所以它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着丰富的血肉和生动的内容的真理性的结晶。当然作家也读了“多少那被认为洪水猛兽的书籍”,提高了作家对社会的认识。参看曹禺:《日出·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当他自觉地运用这些认识来从事创作,唯物地思索着考察着社会现实时,这就使得《日出》的现实主义产生了新的特色。
作家提出“试探一次新路”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的文学的背景的影响。30年代中期日益加深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作家对黑暗社会的仇恨更加强烈,同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感受也更加广大和深邃了。革命的力量,反军事“围剿”和反文化“围剿”的力量,像汹涌的怒潮震撼着这黑暗社会的基础,给作家带来光明和希望。他说:“我感觉到大地震来临前那种‘烦躁不安’”,“萦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同上。显然,这是时代现实中光明和黑暗激烈搏斗的声音在作家心灵上引起的强烈反响。正是在这深刻的背景下,增强了他对黑暗社会进行彻底批判的战斗立场,以至于他要整个地推翻那个吃人的社会:“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蟠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他再不能容忍这个黑暗制度继续统治下去。因此,他写出《日出》也正是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果若读完了《日出》,有人肯愤然地疑问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要过这种‘鬼’似的生活呢?难道这世界必须这样维持下去么?什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的有人肯这样问两次,那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作者的奢望了。”曹禺:《〈日出·跋〉附注》,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反对压迫剥削群众,要求“根本推翻”那个不公平的世界,绝不是一般民主主义所能概括的,而有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某些特点。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火光所照耀,它体现的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这些,是同鲁迅、郭沫若等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