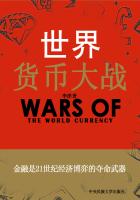中唐以前,土地的分配是按权力和等级进行的,大部分土地被官僚、地主控制,而农民控制的土地很少,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政府可以通过限田制、王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屯田等方式,通过各种手段直接配置土地资源。唐前期政府把长期战乱后遗留下来的无主荒地,产权不确定或发生争议的农地以及部分有主但无力耕种的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然后计口分配给有劳动能力的人去耕种。均田制基本宗旨就要做到耕地与人口的合理配置,使人口与耕地相适应,即李安世说的“力业相称”。其基本目的是限制兼并,缓和日益紧张的阶级矛盾,即所谓“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 使“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卑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
2.1.1 唐前期的均田制的推行
北魏以后,北齐、北周、隋等各朝政府,均沿袭均田制,并根据时代特点,不断加以完善和充实。尤其是隋统一全国以后,才真正地具备了“均给天下之田”的条件,均田制不仅在畿内得到实行,而且有条件推广到了江南以及权力所达之处。唐代的均田制继承了前代的规格形式,同时又根据唐代的特点有所变革和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凡天下之田……度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给田之制有差。” 敦煌和吐鲁番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户籍及土地登记残卷,就证明了唐代均田制实行的范围之广泛。这些地方档案大多数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其中有详尽的土地还授记录及每块地段的大小及四至,其中的精神与唐代的均田制完全吻合。
关于唐前期(618~755年)均田制的实施问题,是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讨论的焦点,在讨论中除少数学者对唐代均田制的实施提出怀疑外,大部分的史学家都持肯定的态度。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曾了若、森庆来、铃木俊等人,就已经肯定了唐代均田制的实施。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乌廷玉、李必忠、唐长孺、胡如雷、徐德嶙、韩国磐、田野等人的论文也对唐代前期实行均田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对唐代的均田制继续展开讨论,杨志玖、韩国磐、韦振江、唐耕耦等人的大批论文再度论证了唐代前期是实行了均田制的。至20世纪70年代,金宝祥的文章又对唐代的均田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证明唐前期实行均田制这一事实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后,武建国对均田制的四种土地授权方式展开系统研究,较全面地反映和证实了均田制在唐前期的全面实施。所以,唐前期实行均田制已是史学界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此处重申,无须论证。
2.1.2 唐前期土地分配政策的基本内容
作为唐前期基本土地制度的均田制,其宗旨就是均平占田、抑制兼并,反映在律、令、格、式的法律条文和皇帝有关诏敕中,这些条文相互联系补充,共同构成了唐前期较为周密、详细、可操作的土地分配政策。
以往学界研究唐代土地问题,多征引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唐六典》、《通典》等传世文献。其中《通典》卷二《田制》记唐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最为详细,但也未全文引录唐田令全文。
1999年,戴建国先生在宁波天一阁发现了明抄本宋《天圣令》后10卷,其中第21卷《田令》共56条,前7条据《唐令·田令》旧文参考宋制修订,后49条为宋代已不行用的《唐令·田令》原文,戴先生据以对《唐令·田令》进行了考证复原。 杨际平先生进一步将《唐令·田令》56条的条文逐条排出,成为研究唐代土地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杨先生还指出,《唐令·田令》为“有唐一代之法,而不仅适用于某一时期”,其他传世文献对《田令》的征引记载,“总体而言,《通典·田制》所记最详,最接近唐田令原貌。《唐六典》次之,亦较接近唐田令原貌。其他各书(《唐会要》、《资治通鉴》、两《唐书》、《册府元龟》等)所记与唐田令原貌皆有较大差距,有的还相差甚远”。本文征引《唐令·田令》即据杨先生所排出的条文。
经过复原后的《唐令·田令》共56条,其中44条(亦即从第1~44条)与官民“授田”有关,12条(第45~56条)与屯田有关。复原的《唐令·田令》比通典记载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多了14条(第14、17、25、26条,第28~36条,第44条),此外,还有4条(第2、6、22、27条)可订正或补齐《通典·田制》的令文,涉及到“授田”、土地还授的具体做法,对于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实施是一重要佐证。
2.1.3 唐前期土地分配的具体政策措施
唐前期的土地分配政策与北朝隋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武建国先生系统研究均田制的演变,提出了唐代均田制与前代相比较,有六个方面的变化,即成丁入老年龄,民户受田类别、数额,土地还受时间,授田对象,土地买卖规定,官吏的永业田、分田及官府的公廨田等方面。下文从土地政策的角度,以武建国先生的研究为线索分析唐前期土地分配政策的具体举措。
1.将原有私有土地和一部分国有可耕荒地一同纳入国家土地政策实施框架,并由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
对于隋末大乱之后所有权仍然明确的私有的耕地和可耕荒地,唐初高祖颁布《隋代公卿不预义军者田宅并勿追收诏》,规定“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预义军者,所有宅田,并勿追收”, 对唐初现实的土地所有状况以诏令形式予以确认,但必须将这一部分私有土地按照均田制的规定登记人户户籍之中,这一政策举措,是在不触动人户原有土地的前提下,将其纳入到国家土地政策框架范围内,以最小的政策变革成本,实施了国家授受土地,确保了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控制。武建国先生把这种土地授受方式,总结为簿籍授受,指出“簿籍授受是推行均田制中运用最多和最广泛的方式”。
不触动各户原有土地的规定更为明确。北魏太和九年令第3条规定“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虽然也是将各户原有土地计为各户的已受田,但语义仍较含糊。《唐令·田令》第2条就非常明确:“(民户)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此外,第6条又规定官吏:“若当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狭乡者,并即回受”;第11条规定:被解免官者,“若当家之内有官爵及少口分应受者,并听回给”;第27条规定:“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第30条规定:寺观因僧尼、道士、女冠身死、还俗等等原因而应退田时,“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受”等等也无一不是田土不出户。由此而知,将各应授田对象的原有土地通充各应授田对象的“已受田”,是《唐令·田令》处理土地分配的惯例。另外,《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三《给授田十六》引授田令所云“先有永业者,则通其众口分数也”,已证实簿籍授受是唐政府推行土地分配政策的主要方式之一。
唐初推行的均田制,将国家掌握荒闲土地授受无地少地农民,并依均田制规定登记于户籍上。高祖、太宗时期,因隋末丧乱,民多流徙;为招徕流民,分授官田,安辑流散,因此“流散者咸归乡里”。 这一推行均田制的政策措施,至少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稳定小农于土地之上,使劳动力与荒闲土地相结合。既可减少无地流民的管理成本,获得更多小农的政治支持,又调动小农生产积极性,实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目标。二是扩大国家赋役政策的实施对象范围,使政府在实施轻徭薄赋的赋役政策时不至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综上分析可知,均田制是在承认人户原有私有土地的基础上,将部分国有可耕荒闲土地用于授受,从而把人户原有私有土地和一部分国有可耕荒地纳入国家土地政策框架,确保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均田制并非是均分天下之田地,更非是劫富济贫,而是国家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方式。唐代推行的以授田与限田相结合的土地分配政策,主要是依靠单一的、直接的、行政手段,通过构建国家行政组织体系,执行和落实政府的土地分配政策。唐初政府在最基层设置里正岗位,作为推行均田制的措施。《唐律疏议》规定里正的主要职责之一是:“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授而不授,应还而不还,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 通过明确里正的责任和权利,并形成制度化的法律条文等具体措施,执行和落实国家土地政策。这是一种典型的采取行政措施配置土地资源的方式。里正的职责不仅局限于授田(国有荒闲土地授给缺田少地农民)和收田(占有土地人户中的漏剩土地和户绝田等受还于公),还要勘地造簿,对人户已经占有的土地的实际状况进行勘查和核实,汇总成簿牒呈报于乡、县。使政府能掌握土地占有状况的动态信息,根据土地占有状况调整土地政策,减少决策者信息不对称对政策的影响。当然,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特别是将土地资源配置的权力赋予最基层的里正,存在极大的政策风险,里正的履职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土地资源的调控以及赋役的征收。一旦对里正疏于监管或监管不力,就会动摇国家的财政基础。
2.沿袭按等级对官吏授田的规定,授田与限田政策措施并举,提出授田顺序,体现了通过扶持、保护小农并保证赋役收入的政策目的
北魏隋代以来,收授土地是按照等级(身份等级、地位等级、权利等级)来执行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均田制是一种典型的等级授田制。唐代的土地政策沿袭了按等级授田的惯例,对官吏和民户授田存在较大的差异。
(1)官吏依品级授永业田。
从亲王、一品至九品,“凡官人及勋,授永业田”。 具体授田标准(最高授给数额)见《唐令·田令》第6、7、9、11、12、13、17及23条。自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到云骑尉、武尉个六十亩,按品级授给。官吏永业田职分田的数额,普遍高于隋代,并且规定官吏的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授之限。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质者,不在禁限”。官吏所授之田,是具有完整意义的土地私有权,既可永久继承,也可买卖抵押等参与土地的市场流转。唐代对官吏授田的政策体现了统治者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从政策上保证了统治集团广占土地的特权。唐初官吏授田数额普遍增加,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掌握的土地数额有所增加;二是唐初统治者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以多予授田获取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大政治支持,以缓解高祖太宗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2)从均田制的性质来理解对官吏的授田,名曰授田,实则是对官吏占有土地的最高数量限制。
对超额土地“有剩追收”的实证材料迄今未见于有关文献和出土文书资料中。学术界一般认为对官吏限田规定实同具文,很难认真执行。
为了避免官吏占有过多狭乡之田。唐田令第9条明确规定,官吏应授永业田,五品以上,“皆不得狭乡受”,六品以下,“可以狭乡受”;官吏“当家口分之外,先有地”者,狭乡不可回授,宽乡则可;赐田场合,指的狭乡者,可于狭乡给;“非指的处所者,不得于狭乡给”。这些政策意图主要是进一步限制土地兼并,五品以上的官吏便不得在狭乡占田,抑制豪强大地主的膨胀,确保狭乡小农占有一定量土地以稳定统治和保证赋税收入。
唐代对官吏授田巨细无遗的规定,也反映出政府限制官吏利用权力占田的政策意图。《唐令·田令》有关官吏给授永业田、职分田,给各官府衙门配给公廨田的规定就达7条之多。唐代,官吏官爵的变动十分频繁,为此,《唐令·田令》规定:官吏犯除名,追夺其品官应受的永业田,并追夺赐田,然后按贫民百姓标准授田;官爵解免不尽者,按所降品级追收。倘若其户内另有官爵人应授品官永业田而未授,或有其他应授田口而未授,所追夺之地就先“回给”这些应授田者,有剩追收,不足更给。官吏因官爵应得永业田,未请或请未足而身亡者,子孙不得追请;承袭父祖爵位者,只得承袭父祖永业,不得另请,若父祖未请及请未足而身亡者,袭爵者只能请始受封者应得之半数。关于官吏隔越请田手续,《唐令·田令》规定:官吏隔越请田时,先要在本籍(本贯)陈牒,经本地官府勘验告身、检籍知欠(检核籍书已受田与欠田情况)后,录牒管地州,在经管地州勘验后给天,然后具录顷姆四至,报本贯上籍,同时又由本贯与管地州同时向尚书户部申报,计会附籍。
从以上三个方面限制官吏占田的分析可知,唐初政府制定土地分配政策时对官吏进行授田的同时,限田措施制定如此周密、细致,其宗旨还是力图禁止限外占田。正所谓名曰授田,实则限田。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分配政策限制官吏逾制占田,将有限土地授予无地少地小农以解决维护政治稳定和保证赋税收入两大难题。如此缜密限制官吏过多侵占土地的政策措施,可谓用心良苦!
(3)提出“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的授田顺序,反映出土地分配政策的财政实质。
唐代以均田制为主体框架的土地分配政策规定了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的授田顺序。第一优先的是承担课役的课丁。课丁之中,再按“无”、“少”、“富”顺序排列。不课户之中亦按“无”、“少”、“富”顺序排列。将课丁摆在第一优先授田位置,突出反映了以均田制为主体框架的土地分配政策的财政实质。
3.对民户授田的分配政策调整较大,具体措施趋于细化复杂
对于民户的授田则复杂细致得多,具体授给规定见《唐令·田令》第2~5条以及第21~36条。分析起来,又区分为以下几种具体情况:
(1)对民户的主体——个体小农以及工商业户,授田区分为“永业田”和“口分田”两类。
规定:“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分田三十亩”;“诸黄、小、中男女及老南、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诸给田,宽乡井依前条。若狭乡新授者,减宽乡口分之半”;“诸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宽乡三易以上者,仍依乡法易给”。“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授给广大个体农户及工商业户的“永业田”和“口分田”在性质上有明显区别:他们的“永业田”同贵族、官僚户的“永业田”一样,“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同样有明确的私有权。《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也记载个体农户及工商业户的“世业之田(永业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他们的“口分田”,在非“卖充(住)宅及碾硙、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情况下,“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在入老、身死之后要归还政府,另行他授,即“口分(田),则收入官,更以给人”,“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广大个体农户及工商业者仅有法定时间内的占有权、经营权而无所有权,所有权属于国家。
(2)对僧尼、道士、女冠等的授田。
规定“诸道士、女冠受老子《道德经》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受具戒者,各准此。”没有“永业田”和“口分田”的区分,实际上这类授田“不是授给僧尼、道士、女冠本身或其家庭,而是授给寺观”。 授田虽按僧尼、道士、女冠的人数授给,但僧尼、道士、女冠们并不拥有对所授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其所有权和占有权是属于寺观的,是寺观私有的土地。
(3)唐田令取消了妇女、奴婢、丁牛的受田规定,新增的僧尼、道士、女冠、工商户、官户、杂户等授田对象。
唐代,在法律上再次确认隋朝定制,除妇人、奴婢、部曲之课,妇人可能就不再是应授田口,因妇人不授田,一夫一妇无其他应授田口之户就只能“授田”100亩。 除了在牧与配城镇的官户奴外,奴婢不再是应授田口。在牧官户奴“于牧所各给田十亩”即当为维持其日常生活之用,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奴婢、部曲不再计为应授田口,一方面是由于隋唐时期奴婢、部曲的数量已较过去大为减少,奴婢虽仍用于生产,但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有限制地主兼并之意。
唐田令新增的应授田对象是僧尼、道士、女冠、工商户、官户、杂户。一般民户中,又新增老男作为应授田口。僧尼、道士、女冠之成为应授田对象,主要原因是隋文帝提倡佛、道,佛教势力又盛。至唐初,寺院“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已成积习。唐初,寺院广占田已是既成的事实,于是,唐田令便予以确认。僧尼、道士、女冠的应受田数远低于白丁,授田的本意只是在于维持寺观众僧道的基本生活,同时也有限制寺观大量兼并民田之意。
对官户、官奴等贱户的授田规定:“诸官户授田,随乡宽狭,各减百姓口分之半。其在牧官、奴,并于牧所各给四十亩。既配城镇者,亦于配所准在牧官户、奴例。”这其中又有区别,对一般官户只授予“口分田”,而且要减半;对在国有牧场和城镇服役的官户、官奴,只给予耕田十亩。由于官户、官奴是因犯谋反和谋大逆之罪而被籍没入官的政府奴隶,所以对他们的任何“授田”只是为了使他们能从事耕织以维持基本的衣食需要,来保障他们能够为政府服役。
4.为解决人地紧张矛盾,实行宽乡、狭乡的差别授田,旨在进一步限制土地兼并
唐田令对于宽乡、狭乡差别授田十分明确:诸民户给田,“宽乡并依前条,若狭乡新受者,减宽乡口之半”;官吏应授永业田,五品以上,“皆不得狭乡受”,六品以下,“可于狭乡受”,官吏“当家口分之外,先有地”者,狭乡不可回授,宽乡则可;先于宽乡借得无主荒地者,可以回给,狭乡则否;赐田场合,指的狭乡者,可于狭乡给,“非指的处所者,不得于狭乡给”;工商户给授田,宽乡永业、口分减半,狭乡则并不给;卖田场合,狭乡乐迁宽乡者,听卖口分田,狭乡迁狭乡,宽乡迁宽乡,不可卖口分田。
上述规定的政策立意旨在进一步限制土地兼并。照此规定,五品以上官便不得在狭乡占田,工商户也不得在狭乡占田,狭乡民户占田的限额也较前大幅度降低。
2.1.4 唐前期土地分配政策的效应
1.粮食产量及人口数量等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指标的持续好转是唐前期土地分配政策实施效应的集中体现
唐初,统治者以民本、农本思想为土地政策的指导思想,将土地政策的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协调统一,推行国家主导土地分配、以行政手段分配土地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无地或少地的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唐前期大量荒地在土地政策的引导下被开垦出来,粮食增产,粮价下跌。玄宗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 开元初建成的清河(今河北南部)“天下北库”储有巨额粮食……中经50年的耗用,到安史之乱时,尚存粮30万石。据记载,天宝八年(749年),官仓的存粮共有粟米9600万石。 近年考古发现洛阳含嘉仓,天宝八载,储粮就达5833400石。而这个粮仓的总面积达42万平方米,地下式的圆形窖穴295座,大窖能储粮2万多石,小的可储粮数千石。其中有一窖还存有已变质炭化的谷子,据推算这窖谷子当年储粮达50万斤之多。农业生产发展的直接结果是物价下跌,隋末一斗米值数百钱,贞观初斗米三四钱,开元十三年,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才三钱。”百余年间,在传统社会影响物价稳定的粮价基本无涨落,足见唐前期农业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唐代前期,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社会安定,加之国家鼓励生育的人口增殖政策,人口也不断增长。高宗武德年间,全国有户二百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三百万。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上升到380万户。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发展到615万户,人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全国有9619254户,人口有52880488人。
通过以上粮食增产、人口增殖可以窥见唐前期农业经济确有长足发展,国家财力充足,国势强盛,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自贞观三年,关中熟,……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至丰稔,米斗三四钱,……此皆古昔未有也。” 太宗贞观四年,“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三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年间是唐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史载:“四方丰稔,百姓殷富”,“人情欣欣然”。“人家粮储,皆及数月”,国家粮仓积满,甚至“陈腐不可较量。”唐代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些文献资料和诗人的描写虽有些夸张,但大体反映出了开元盛世的情景。
2.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维护抑制土地兼并的土地制度仍是土地分配政策的主流
《唐令·田令》第34条规定:官田荒废三年以上,允许民户申请借耕,九年以后“还官”,或授给借耕者充口分田。私荒废田同样可以借耕,限满只能“还主”,不得充借耕者的口分田。换言之,官荒地纳入均田制的政策体系,有主的私荒废地不纳入均田制实施范围。客观上承认民户对“私田”的土地占有权。诚如马端临所言,均田制“因非尽夺富之田以与贫人也”, 其目的只是在于使土地私有制运动在不致产生社会运动动荡的过程中有序地进行。
在均田制的制度框架下,国家力图将战后遗留下来的大片荒地收归国有,分给无地农民耕种。因此,北魏的均田法令中,对还田规定得细密而严格,“老免”、“身没”皆须还田;奴婢耕牛受的田,如果买卖或死亡发生了改变,必须“随有无以还受”;露田与麻田也须还受;定额之内的桑榆田也不许买卖。惟一能够买卖的,只有桑榆田超额者与不足额者之间。到了唐代,土地买卖的限制放松了,不但永业田可以买卖,甚至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出卖。如“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地亦并听卖”;在家贫需要葬费及流移的情况之下皆可出卖永业田;而口分田在狭乡迁宽乡,卖充住宅、邸店、碾硙时,也可出卖。尽管唐前期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无论在律令上抑或在实践中,都还受到国家的限定和控制,土地买卖是有条件的,是不自由的,土地的占有者还不具有“土地所有者可以象每个商品所有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的权利,还没有独立的专有权,没有“土地自由私有权”。这说明唐代前期均田制下的土地还没有完全私有化,土地占有者还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国家对于土地仍然具有很大的支配权力,仍是土地的最终所有者。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种种抑制土地兼并的方案虽然能暂时缓和一下土地兼并的势头,但根本上无力扭转土地私有的发展趋向。
3.客观上促使租佃关系的深化发展
唐代的田制,贵族官僚的受田,普及到品官中一切官吏,不论是职官、官爵、散官、勋官都可以授永业田,还有大量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这些官僚贵族分得的大量土地,自己无力耕种,必须借民力以佃耕。那些拥有众多部曲的地主阶级,在均田制下占有大量的土地。他们将土地分配给部曲及其他客户耕种而坐收地租。至于寺观中的僧徒、道士、尼姑等,也能分得土地。他们将土地租佃出去,坐收地租。即使是均田小农,在政策许可的条件下,也可以把土地自由出佃。可见,租佃关系成了唐代农业生产关系中得到政策、法律正式肯定的占支配地位的形式。租佃关系成为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关系。
4.对授田对象的调整是社会经济环境对土地分配政策影响的表现
废止了北魏以来奴婢分配土地的规定,反映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松弛的社会现实。这实际上是以政策、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北魏以来使用奴婢劳动的合法性。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奴婢逐渐取得了半自由人的身份,“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同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 奴婢演变成了部曲和客女。唐初时,部曲和客女与良人一样,法律允许其拥有资产的权利。唐初的土地分配政策,适应这一客观发展,废除北魏均田制中奴婢受田的规定,规定奴婢不能受田,并从法律的形式上给予肯定。这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
新增了僧尼和工商业者授田的规定,僧尼和工商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提高,反映了唐代封建地主制经济趋于成熟。唐以前的均田法令中,均没有工商业者及僧道授田的规定。唐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寺观的增多、僧道势力的增强,工商业者和僧道都被纳入了均田对象的范围,均田法令中规定了僧尼和工商业者都可以授田。虽然他们的授田数较农民常年成丁者少些,或者只能在宽乡授田,但这毕竟是以法律的形式正式承认僧尼和工商业者占有土地的权利。这一正式规定,一方面表明工商业者和僧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把工商地主及寺院地主的土地全部纳入均田土地编制之中,由国家统一分配。尽管在法令上承认工商业者和僧道的授田数,事实上只不过是对他们所实际占有的土地做出规定罢了,并不一定按人丁划分土地给他们。但这本质上多少带有了土地所有权性质。唐代授田范围的扩大,反映了封建地主经济更加成熟。同时,也为寺院和工商业兼并土地网开一面。因此,唐代的寺院经济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寺院占地附户日增,形成了“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 唐代工商业者在法律的范围内获得了占有土地的权利,这也表明了工商业资本更有条件投向对土地买卖,土地市场的发育也为抑制土地兼并的制度瓦解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