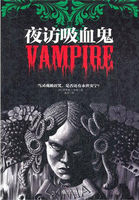这次回老家去,母亲说又有几户人家搬到吊庄去了。
吊庄有不少,在银川周边的陶乐、月牙湖、南梁一带。说是我们这里不适于人类居住,要把我们这里的人陆续迁去吊庄生活。已有不少人家迁去了。就像一个被搬走了许多坛坛罐罐的屋子那样,我们村子在走了许多人家后,显出一种难以言述的古怪与空洞来。
整个村子会被迁空么?
想到将后自己若真无这样一个村子可以惦念和回归,会是很寂寞很怅然的。
我也时或玩味着吊庄这样的说法,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叫,让人总有一种悬而未决的不踏实感。
别的事管不了。就问母亲又走了哪些人家。母亲一一说出来,这其中就包括那女人家。母亲说到这一家时,我心里一动,警觉地看了看母亲,但没有从她脸上看出什么来。
虽然离开还不足半年,但母亲脸上的皱纹似乎又多了一些。
夜里躺在炕上睡不着,透窗看着天上的星星,密密实实地挤挨着,像一树嘈杂不已的麻雀,就想,星星是无需迁到哪里去的吧。想着刚刚迁走的几家人,想着已经迁走的每一个人,曾经都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劳苦过,指望过,但是,突然地,像被惊散的麻雀一样,飞到别处去了。他们会怎么样呢?能真的过上一份好日子么?
我知道无论迁到什么地方,老百姓要过到一份好日子都是很不易的。
夜深了,重甸甸的星空似乎要携带着整个奥深的天空,哗啦一声扑落下来,又似乎要悄然地飞升到一个与我们不相关的高处去。我有着一种久违的露宿感。
在这样一个迷蒙却又透彻的夜晚,那女人的身影总是在我四近缭绕不散,就像一只缠磨人的蜂子那样。实际上从母亲说到她家也迁走的那一刻起,就这样了。
我惊异于母亲说到她时,那份近于木然的平静。
这样一个女人走了,一下子走得那么远,到千里之外去了,母亲难道就没有丝毫的轻松么?
不要说母亲,连我也恨恶过她的。
夜静如终古。我想着那女人的一些眼神,一些笑,一些心思和手段。作为一个成年的男子想这些,心思与小时候相比自是大有不同。那么,此刻,如此静安又荒寂的夜,她睡在怎样的一片土地上,怎样的一间屋子里呢?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她不是个好女人。她的家就好比一个店房,常常是很热闹的,常常有许多男人在她家里,拉闲话呀,打扑克呀,或者掰手腕什么的。黄昏时候,各家的饭都做熟了,女人偏头见自己男人不在,就使孩子站到街门上去喊。孩子们立在不同的门口喊着,方向却都是朝着她家的。果然不久,像打开了蜂箱那样,看见男人们从她家里三三两两地出来了。她慵懒地跟在后面送着,抿着嘴笑,指着一个男人的脚后跟,让他把踏入鞋里的裤脚抽出来。她的男人依布拉也伴在她一旁送着,肩胛耸起来,头似乎陷下去。依布拉的一只眼里,有着一叶萝卜花。这就使他的走路略带一些摸索的意思。偶尔女人的一句什么话,引起男人们一片雄野的笑声了。依布拉像是并没有听清女人说什么。然而在男人们的笑声里,他腮边的肉会动一动,终于也就凑合成盲人似的一个笑了。门上走空了,他们两口子还要在门口立片时,然后是女人打一个哈欠,回去了。依布拉低头,在自己身上找了找什么,像他记得自己身上曾经落过一个虫子似的。他找寻的时候动作于灵活中有些迟钝,然后就也回去了。先关上一扇门,将另一扇门总是带些犹豫地关到半开。
不久果然会有吃完饭的男人摸着嘴巴又出现在门上,斜着身子从那半开的门里进去了。
有时候这半开的门要到很晚才能完全地关上。
我有一个很深的记忆,母亲和她的好朋友舍巴妈那时节常常骂那个女人,在锄草的时候,在磨坊里各抱一根棍子磨面的时候,坐在门前的矮凳上做针线的时候,都骂。骂的什么忘记了。但记得确然是在骂她。母亲和舍巴妈骂她时的表情只要垂念一想,至今还可以历历目前。那表情真是再特别不过,轻蔑、厌恶、愤恨,还有委屈及无能为力等等都在里面的。总之是只有那样的时候,她们才有着那样的表情,别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的。那样一种别具的眉来眼去,那样一种别具的咬牙咧嘴,似乎只要一说到这个女人,她们的脸就必得有无穷变化,难以正常似的。记得一次舍巴妈的手上扎了一根刺,来寻母亲挑。很快两人就一拍即合眉来眼去地说起那女人了。其实一根刺,舍巴妈在自己家里就可以解决的,用不着来我家的,来无非是要和母亲眉来眼去一通。这一次说得似乎格外投机也格外解气,刺早就弄出来扔得不见了,话还汩汩滔滔地有许多没有说完,结果就搞得日头沉下山去,舍巴大脸色难看地寻上门来了。仗着母亲在旁边,舍巴妈大着胆子抢白了男人几句,说我们女人串门子,不过就是这样子串串,你们男人呢,你们咋串门子呢,你们总是一动弹就把门串错。然后抢在男人前面小跑着一样回去了。
母亲原本不过是表达着一腔义愤,也可以说完全只是帮着姐妹们骂骂,出出闲气罢了,担心在母亲也是有一些的,但侥幸心一定是更重些。母亲待父亲真是再好没有了。但是,忽然的,不知怎么了一下,父亲也开始往依布拉家跑了。
你要学别的男人,往那个娼妇家跑,我就死。先前,相安无事的时候,母亲曾多次这样对父亲说过。
但父亲的脚还是向那里去了。
这使得母亲和舍巴妈之间的眉来眼去少起来,话也很少的了,两人簇在一起,沉默的时候还是居多,偶尔是一声气短的咳嗽,偶尔是一声无助的叹息。让我们这些孩子也觉到一种莫名的压抑。
饭熟的时候,我也开始立在门外矮矮的院墙上,向着那女人家的方向,唤父亲来吃饭了。妹妹站在矮墙下,要求我声音再大一些。
父亲似乎连饭也不愿回来吃了。母亲就让我到她家里去喊。
她家窑洞的炕上,坐着几个男人,在说笑什么。父亲也在其中。一见我,先把脸上的笑收起来,接着是一声故意的咳嗽。那女人或是在刷啦刷啦洗锅,手臂上的镯子碰到碗碟上发出声音来;或是坐在灶前的一只矮凳上补缀什么;或是远远地坐在门槛上搛菜、捣辣面子。倒好像炕上的一伙男人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炕上的男人们说出一句什么,都要向她这里投一眼的,似乎这话实际上只是说与她的,似乎话一出口,紧跟着的一个程序就是要看看她的反应如何。
唉哟,叫你来了,叫你吃饭去呢。快快快,饭冰咧。
每当我去叫父亲吃饭,旁边的人就会这样说。那表情也是怪怪的。说着,也会不断地去看那女人,似乎女人身上有着一个什么答案似的。
女人全然不顾炕上的调笑。她向我笑笑,搁下手里的活计,从锅灶上摸出一个什么给我吃,有时是一只蒸得开花的土豆,有时是一只生胡萝卜。
我们干坐了这半天,也不给我们吃。炕上有抱怨声。我还不吃呢。我背了手站着,不看她手里。
这时候我父亲不高兴了,严厉地命令我拿上,似乎我不拿他就会跳下来揍我的。
我就拿上,装入口袋里去。觉得头上被女人轻轻摸了一把,头皮痒酥酥的,但是很快一下就摸过去了。女人又去接着干她的活计。
父亲不回去,我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然而没叫到父亲,我也就不便回去。我就在地上候着。
虽然不过是普通的窑洞,但这窑洞却是糊了顶棚的,就显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洋气来。墙上贴得花花绿绿的,细看看,竟是把各种颜色的香袋儿小心地拆开来,贴在了墙上。一只香袋儿舒开来不足一寸宽,糊妥这窑洞得用去多少香袋儿。也许是看见了香袋儿的原因,总觉得这屋里始终有着淡淡的一抹清香。前壁上的百叶窗很小,糊的白纸也泛黄了,但依然很干净。窗纸上贴着一些窗花,像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我发现这女人倒是很少参与到男人们的说笑中来,也没有一次上炕来和男人们坐在一起。她始终坐在两个地方,一处是门槛,一处就是灶前的矮凳上。有时候她也会斜倚着窑壁,用女人特有的样子虚立着做针线,一针一线做得仔细,眼神专注而清亮,像她的怀里始终有着一个熟睡或吃奶的婴儿,但这样的时候是不多的。有时她会显得超越于男人们的说笑,把手里做着的活计停下来,有些出神地望着一边,但很快就会否定什么似的,不易察觉地摇摇头,重新做起手边的活计来。她出神的时候,会使男人们显得不安,虽然还是说着话,一两声干干的笑或者也有的,但大家无疑都关注着她这里,时时被她这里牵制着,因此炕上就隐隐给人一种涣散感游离感,似乎是主角还没有到场或者已经离开了那样,使大家的谈话没有主心骨,寡寡的无趣味。直到她重新做起活计,炕上也才会重新热闹有趣起来,似有了某种接续与修复。有时她会为某句话莞儿一笑,像微风掠过时叶子动了那样。这就使说话的人始料不及地得意起来,眼睛频频地眨动着,嘴唇一跳一跳的,似乎有比这更为精彩的话将要从他那按捺不住的唇里出来。有人原本觉得他这话并无多少意思的,但是女人的一笑却使他们愣怔了,重新捞起那话掂量起来。偶尔一些特别的话还会使女人格外地笑起来,笑出声音来,笑得手按在肚子上,笑得捂自己的嘴。这就使说这话的人简直是兴奋到无以复加,怎么说呢?脸就像刚刚下完蛋,一路招摇不已的鸡屁股了。大家也都妒忌起来,似乎他已沾了什么大便宜,自己吃了什么大亏,但还是掩饰地拍打着他,鼓励他再说,说下去,多多的再说上些。坐得久了,他们还会拿坐在一边昏昏欲睡的依布拉说事。只要男人们一来,依布拉的话就是很少的,谁说话他就看谁的嘴,像在比较着说话的嘴们有什么不同,但他很快就昏昏欲睡了,上眼皮总是重得让他驮不住。于是就被旁边的人拍醒来。他立即就用双手帮忙,使自己坐得直一些,而且晃头令自己清醒,像真的由一个梦里回来似的。大家就让他也说说。他说你们说你们说。我们说你就不要睡觉,你睡觉我们说给谁听嘛。他听了这话就更加的往直里坐坐,表示这番他是不睡觉的了。于是有人就掇唆他给女人下一道命令,炒一锅麻麦子大家吃。依布拉把自己脸藏在阴影里,头仰在墙上不出声,而且把眼睛用着力闭上了。他这样子使大家略略地觉到一些尴尬了,暗暗交换着眼神问怎么办?是不是走?这时候女人却从门槛边站起来,把麻绳儿缠绕到鞋底儿上,说,坐心慌了?想吃麻麦?好。她就往锅里滴清油,生火,开始炒麻麦。很快就炒好了。一大拼盘端上炕去,七八张嘴吃得叭叭叭响。她也端一小碗儿麻麦,端到门槛边去,却不吃,重新纳起鞋底来。有人递一把麻麦到依布拉手跟前,依布拉眼睛被割裂那样睁开来看,接了,捏在手里,也不吃。
也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些情景。
后来母亲问个中细微,我如实道来,但母亲总像不能相信,翻覆问过之后,难散尽眼里的猜想与疑惑。
要是炒了麻麦,她会装我满满的两口袋。一手端一大碗麻麦,一手往我的口袋里装。轻声地说着让我撑开口袋来。我就撑开着。看见我口袋里的麻麦在暗影里渐渐地浮升上来,看见她的手镯一次次滑到她的手背上去。她的手就像一个精巧的漏斗,麻麦就从下面徐徐地漏出来,漏入我的口袋里去。因为离得太近,就觉得她的脸要比我的暖热一些。我从余光里看到了她脸上的汗毛,像是汗津津的。
我出师不利,只好害得母亲自己来喊父亲。母亲绝不到屋里来的。连大门也不进。她立在街门外喊。也不喊父亲,喊我。大家就都看父亲的脸。这使父亲难堪起来。下炕来,也不管我,向那女人古怪地笑一笑,就出去了。
女人没听到什么似的照旧做她的活计,我发现她的脸一时有着一种近于冷漠的安静。
顾不了许多,我也抢出门去。见父亲已走得不见了影踪,母亲还在街门外等我。
我赶紧辩白。
但母亲像是不用听似的,默默走到前面的夜幕里去了。
后来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一度很僵。
记得依布拉家打院墙了,很多男人都去帮忙,父亲也去了。母亲领着我和妹妹给羊铲草,母亲总是哭个不住。母亲的背斗很大,我和妹妹两个人帮,母亲都背不起那一背斗草来。后来弄到一个地埂儿上,母亲一腿跪在地上,我和妹妹在后面帮,才背起来。背斗把母亲的大半个身子都占没了。
山里有很多洞穴,有羊把式掘了避雨的,有看瓜人挖了住在里面守瓜的。这些洞穴,到里面并不很小,远处看去却似一个个乌鸦洞,阴森森的,使我觉到莫名的神秘和恐惧。我总是觉得有狐狸变成的老女人在那里面。正走着,母亲突然停下来,一边喘气,一边望着山坡上的一个乌鸦洞。望得我们怕起来,催母亲快走。母亲忽然说,她不回去了,她要到那个洞里去,她不想活了。吓得我和妹妹抱住她哭作一堆。
从此我就恨起那女人了。
再去喊父亲,我也不到她屋里去了。学母亲的样儿立在街门外喊,而且声音很不友好的。
但母亲却从暗里摸来,领我回去了。是我自作主张来喊父亲的,母亲已不让我再去喊父亲了。她原本做了饭,父亲要不在,她就放在锅里给他温着,如今丢在案板上,叫父亲回来吃冷饭。但吃冷饭的父亲也似乎并无什么怨言。
终于等到依布拉打这个女人的一天了。
没想到依布拉也会打女人。实际村里的女人们对依布拉的意见也很大的,甚而比对那女人还要大,她们觉得那女人之所以那么嚣张,与她有这么个男人不无干系的。是啊,这样子的一个女人,做男人的,怎么不好好地拾掇拾掇她呢?只有他依布拉是最为合适的拾掇她的人嘛。
好在依布拉终于是出手了。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极为异样的一天,记忆也尤其深牢,但想起来倒似一个梦境。
当时有许多孩子围拥在她家门口看,有的竟骑在墙头上。但不知为什么,没见一个大人来看,男人没有,女人也是没有。但在角角落落里能看到一些女人,交头接耳着,眉来眼去着,鬼祟着神情指天划地。
依布拉不打则已,一打原来是很歹毒的。这又是一个人没有想到的。他把女人的帽子都打掉了,把她的头发很多的缠绕在自己手上,使她离他很近,而且挣脱不开去,一边就操了一只鞋底往她身上乱打。女人只是用双手紧紧地蒙住面目,似乎并不很躲闪疯了似的抡向自己的鞋底。依布拉的弟弟哲麻高高地立在自家的窑顶上,赤着脚走来走去,不时地挥舞一下手臂,算是给哥哥助威。听他的口气,是鼓励哥哥把女人不打不说,要打就打死,然后他可以代哥哥去抵命。
我们挤挤搡搡在门洞里,呆了一样看着。
这时哲麻忽然作势在窑顶上找什么,明显是要对付我们的样子,我们就一下子从门洞下跑散了。等我们回过头时,门已由里面关上了。看不见,只好远远地听着。忽然就听到哭声,以为是那女人,很快就听出不是,是依布拉在哭,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老鞋底,在泥水里深一下浅一下没头没脑地走着。
那天夜里,我家里的气氛很有些异样。实际上整个村子里都有些异样。母亲做了父亲最喜欢吃的黄米饭就炒刷子菜。刷子菜是我们这里一种特别的腌菜,长长的,形似刷子,可生吃,也可炒来吃。当然炒了吃更香的。父亲一直嫌我家的刷子菜不好吃。母亲说谁家的刷子菜好吃了你吃去呀。但那天母亲却借了一碗好刷子菜来给父亲炒了吃,米饭里还和了大块的土豆。果然使父亲连吃了三碗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但父亲一直阴着脸吃饭,而且吃完后就早早地睡了,很快就放鼾声出来。然而不时伸伸腿搔搔头什么的,让人很容易就看出破绽来。母亲就着窗前的油灯补父亲的破袜子,不时指指父亲的后脑勺,幸灾乐祸地对着我们兄妹俩笑。父亲的后脑勺那天晚上是有些说不清的古怪的。我和妹妹在母亲的感召下,一次次看在眼里,一次次缩紧着身子偷笑着。
整个童年期间,我们很少这样齐心地快乐过。
我考上初中的时候,父亲下大工夫极为认真地给我理过一次发。我考了全县第七名,父亲高兴得不知给谁说说才好。就决定好好给我理一次发。至今也不明白理发的地点为什么不在我家,不在别处,而是在那个女人家。
记得当时院子里人是不少的,不知谁的一只小收音机还呜哩呜啦地响着。女人手里拿着一面镜子,用一种很女性化的样子闭紧着双腿蹲在前面,看父亲给我理发。我被看得不好意思,脸上露出不悦来。她便向后挪挪。一俟理完,她马上就拿镜子给我看,并连声说好看一类的话。我一看,实在谈不上好的。我已经很不喜欢父亲给我理的发型了。觉得委屈又不便诉说。但父亲看来是非常满意的,从各个角度欣慰地端详了半天才休。在父亲给别人理发时,她小心地扫拢了我的头发,嘱我走的时候带上,塞入墙缝里去。
但是没想到她会忽然地鼓动我刷牙,说我是中学生了,要到城里去了,不刷刷牙说不过去的。
说话间拿了牙膏牙刷来。
蹲在院里和墙根下的人们望着我开心地笑着,看我如何举措。我坚决不刷。
这似乎让她始料不及。她把牙刷翻来覆去拿给我看,一再解释说,牙刷才买来不多几天,她也只用过一两次,基本上还可以算是新的。
过多的解释使她红了脸,拿着牙膏牙刷,手足无措起来,倒似乎她真的在做着一个很不光彩的事。
父亲以命令的口吻让我刷牙。人家好心借给你,你还这样子。父亲愤愤地说。
我就一探手把牙刷接在手里。
很快看见她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唉呀,挤那么多。有人惊呼着。
好好刷一刷,要当中学生了嘛。她松了一口气似的说。但是我看着牙刷上的牙膏迟迟不刷。
父亲就在我刚刚推得干净的后脑勺上,响响地来了一巴掌。
那女人惊慌失措地将我揽入怀里,一遍遍摸着我的后脑勺,一遍遍叹着气说,这弄了个啥你看这弄了个啥。我狠狠推开她跑出去了,边跑边把牙刷扔在了院子里。
我记得很清楚,我一下子推在了她的肚子上,推得她倒抽了一口气。她的肚子软软的,我跑了很远,还觉得一些什么在我手上。
后来,许多年过去了,我已上完大学,参加了工作。自是有了天天将牙刷刷,将脚洗洗的习惯。那女人的事,已听得不再多。忽然一天,也不知为着个什么由头,听母亲又说起她来。母亲说,你不知道吧,人家跟你一样,如今也到城里上班了。这使我吃了一惊。问在哪里工作啊。说在县一中。原来她的工作不过是给教师们做饭。但即使这样一份工作,也是很不易搞到手里的啊。我们村里没有任何人能帮上她这个忙的。我在县一中教过书,知道那里的厨师都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子来头的。我竟有一种冲动,想了解一下她是怎么才谋到这份工作的,只要我打探,是可以探得个中消息的。
母亲说,她自从做了县一中的厨师,就常常能拿一些东西回来。问都是什么呀。
就说到旧三角板、粉笔以及旧桌子旧椅子一类,还有电棒,母亲说不说别的,光电棒就有好几十根。我们这里把日光灯叫电棒。母亲说当然都坏了的,用来照亮是不能的了,她就把它们擦得干干净净地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别人要也不很舍得给。有几根在屋子里做着晾杆儿,上面搭搭毛巾衣裳啥的。
听母亲说着这些埋怨里也含有一些歆羡的话,我心里却突然地觉到一酸楚。
人们迁去吊庄后,老院子一时就无人料理,空置下来。大多托亲戚邻里帮忙照看着,允许照看者在自家的老院里种种菜什么的,也可以把树上的果子收归己有。一走就真的很少回来了,不知将这院子留着还要干什么,不知是还给谁留着。然而出售嘛也实在卖不了几个钱的。几乎是等于白送,要白送还落得一个人情,却又舍不得的,就说说不定自己还要回来的,回来了就还是个窝嘛。于是就那么空放着。无人住,院子很容易就破败下去,长许多荒草出来。村里这样的院子一多,就使村子很有些异样的。好像影响得还有人住的院子也要跟着破败下去。我家正好在这样的几家空院中间,如同一个活人睡在几个死人中间似的,让人觉得不大舒服。有时候落一场大雪,凡是空空无人的院子里,积雪总是要过上很久才能化尽。但父亲上了年龄的缘故吧,倒觉得这是一份难得的清静。是的,住久了也便觉不出什么了。
我这次想在老家多呆一些时日。
一天,出门去闲望着,就看到了那女人的家。一下子想起小时候望着那里喊父亲吃饭的事来。禁不住心里一动,就向那里去了。到门上,还没进去,便能觉得出这里面是一个荒院。我想着这门上曾有的热闹。门用一把小到微不足道的锁子锁着。我轻轻动了一下,它就打开来。像吹口气它也能开来似的。锁环和锁孔都已生锈了。我把锁子捏在手里走进去。
院子里倒没有想象得那么荒败。野草是有一些的,沿墙根一路长过去。当院晒着一小坨干牛粪。果然有两头牛在西边的墙角下卧了,眯了眼晒日头,不断地伸出长舌头来,轮番舔向两边油腻腻的鼻孔。哲麻没有搬走,这一定是他家的牛吧。
但那两孔窑洞却年迈的人一样苍老了许多。而且像放久了的果子显得像果核那样,它们在枯寂的岁月中也明显萎缩了不少。和记忆中的已完全不同。简直不能相信这里面曾有人住过,有那样的一个女人住过,住过那么多年。两孔窑洞连体人一样在一起的。一孔的门已没了踪影,里面隐隐约约装了许多东西,草啊破自行车啊没有了盖子的老木箱啊什么的。另一孔门却在的,而且用一把大锁子结结实实地锁着,像是没有任何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它了。我故伎重演,又握住它拉了几拉,果然用了不小的力气也奈何它不得。实际用不着拉开它的,透过窗子就能将里面看得清楚。窗子曾有的那些静静的窗花一个也不见了,连窗纸也没有了,只有窗棂横在那里,像一副骨架。我透过窗棂向里看去,窑壁上像被烟蚀雨淋过,仔细看才能看出香袋儿来,如一种行将磨灭的痕迹。顶棚也这里那里的掉下来,让人惊骇地发现,一纸之隔的上面原来竟是这样子的。锅啊案板啊一类都不见了,被它们空出来的地方显得触目惊心。里面看来是被搬得空空的了,连墙上的钉子也似乎一一拔去了。但这时候我的心却跳了一跳,在一个相对隐蔽的角落里,有两个钉子还很显结实地钉在两边的墙上,那是两个不小的钉子,顶端被弄得弯向上面,以便把它们上面的那根电棒稳稳地驮住。电棒的中间部分已朽坏似的破裂了,裂片就掉在它下面的地上,如果看得稍久些,就能在浮游不定的阴影里看到它们,像经过了文火的一些纸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