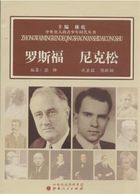三、著述
张岱一生“著作等身”(佚名《西湖梦忆》序中语。此序从语气看,疑为张岱自作。),其69岁时所作《自为墓志铭》,即称:“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古今义烈传》、《张子文秕》、《明〈易〉》、《〈大易〉用》、《昌谷解》、《快园道古》、《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张子文秕》)其未著录者尚有《四书遇》、《张子诗秕》、《茶史》、《陶庵肘后方》、《石匮书后集》等。69岁以后,又先后完成了《夜航船》、《西湖梦忆》、《史阙》、《明纪史阙》、《朗乞巧录》、《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等,另外,还参与编写了《明史纪事本末》、《会稽县志》等,计所著述,达近三十种。
张氏以史学、文学名家,然著作范围,遍涉四部。兹依经史子集为序,略加绍介,叙录版本、存佚情况等;又,张氏著作,大多存有自序,述义例、明作意,除部分史著在本文第三章中要另详加评介外,其书较罕见者之序、跋亦尽量据稿本或最早抄本或本摘录,俾能对读者有所助益。
四书遇六册
此书不分卷,稿本六册,黑格精妙,每面八行,行二十字。上有张岱眉批及补充、修改手迹,殆末完全定稿之钞稿本。(内夹《寿王白岳八十》七古诗手稿二纸。此书现藏浙江图书馆,有马一浮题识见《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编》。)。
此书始作于何时,不详。然结集时间当不迟于清顺治丙戌(1646)(详本文第二章第二节)。是年所作自序云:
六经、四子,自有注脚,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诠解,而去其八九矣。故先辈有言:六经有解不如无解。完完全全几句好白文,却被训诂讲章说得零星破碎,岂不可惜哉!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馀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书遇》。盖“遇”之云者,谓不于其家,不于其寓,直于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古人见道旁蛇斗而悟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笔法大进,盖真有以遇之也。古人精思静悟,钻研已久,而石火电光,忽然灼露,其机神摄合,政不知从何处着想也。举子十年攻苦,于风寸晷之中构成七艺,而主司以醉梦之馀,忽然相投,如磁引铁,如珀摄刍,相悦以解,直欲以全副精神注之。其所遇之奥窍,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推而究之,色声香味触发中间,无不有遇之一窍,特留以待深心明眼之人,邂逅相遇,遂成莫逆耳。余遭乱离两载,东奔西走,身无长物,委弃无馀。独于此书,收之箧底,不遗只字。曾记苏长公儋耳渡海,遇飓风,舟几覆,自谓《易解》与《论语解》未行世,虽遇险必济。然则余书之遇知己,与不遇盗贼水火,均之一遇也。遇其可易言哉!
此书于1985年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将张岱于钞稿本上所加眉批、补记、浮笺,统列于各章正文之中。惟附录《四书》原文,悉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大失张氏本意。
《论语》解卷数未详
《大易》用四册
《嘉庆山阴县志》卷三十六“书籍”著录:“《大〈易〉用》(张岱撰),无卷数,写本,四册。”可见清嘉庆年间此书尚存于世,惟此“写本”不知指稿本或传钞本。今存佚情况不详。
《张子文秕》存有此书序全文,略谓:
夫《易》者,圣人用世之书也……今年已六十有六,复究心《易》理,始知天下之用,咸备于《易》。如“屯”如“蒙”如“讼”如“师”如“旅”如“遁”,一卦之用,圣人皆以全副精神注之,曲折细微,曾无罅漏,顺此者方为吉祥,悖此者即为患祸……故常就学《易》者而深究之。执之失二,谬也,杂也;变之失一,反也。谬者失时,杂者失势,反者失机。李膺、范滂处蒙而执同人,孔融处坎而执离,刁刘处小畜而执中孚:所谓谬也。苻坚处刚行柔,乾、坤紊矣;嵇康内文外污,离、遁乱矣;霍光当难忘安,否、泰暋矣:所谓杂也。宋武德在师,急于受命,变而为革;唐德宗志在震,三藩一决,变而为需:所谓友也。呜呼!成败之不可以论人也固矣!审夫《易》之为用又岂无说乎?能成天下之务者,愚不可也,智不可也;愚则不知其所操,而智者必亟亟乎屡更其道。夫《易》如药也,能生人,亦能杀人。不知其病,数易其方,几何而不死哉?
明《易》卷数未详
见《张子文秕·自为墓志铭》著录。刊刻及存佚情况无考。
《易解》卷数未详
《四书遇序》其书今未见
石匮书二二一卷
《石匮书》系明代开国至天启年间之纪传体通史,卷首系总目;卷一至卷十七本纪;卷十八至二十二世表;卷二三明兴以来直阁典铨年表;卷二四至卷三七志;卷三八至六四世家;卷六五至卷二二一列传(按,凤嬉堂抄本次序与此有异)。是书系张岱历三十馀年精心编撰之作。其书今所见版本有三:(一)八册手稿稿本,不分卷,藏浙江省图书馆。(二)南京图书馆藏凤嬉堂钞本,内题“《石匮书》(二百二十)卷”该馆《古籍版本题跋索引》著录为“风嬉堂稿本”,检原书,实为钞稿本。(又据《题跋索引》,该馆尚存“诸暨陈氏旧藏残稿本”一部,未见。),缺第十二至二十三卷。(三)上海图书馆藏配钞本,题“二二一卷”,原清钞本缺卷一至三、三十二、七十三至七十四、一百六十四至—百七十一,实存二O八卷,所缺者为近人补钞。是书自序云:
能为史者,能不为史者也,东坡是也。不能为史者,能为史者也,州是也。州高抬眼,阔开口,饱醮笔,眼前腕下,实实有非我作史更有谁作之见横据其胸中,史遂不能果作,而作不复能佳。是皆其能为史之一念有以误之也。太史公其得意诸传,皆以无意得之,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银钩铁勒,简练之手,出以生涩。至其论赞,则淡淡数语,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墨汁斗许,亦将安所用之也。后世得此意者,惟东坡一人,而无奈其持之坚,拒之峻。欧阳文忠、王荆公力劝之不为动,其真有见于史之不易作,与史之不可作也。嗟嗟!东坡且犹不肯作,则后之作者,亦难乎其人矣。
余之作史,尚不能万一州,敢言东坡?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余家自太仆公以下,留心三世,聚书极多。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则茂先家藏三十馀乘,亦且荡为冷烟,鞠为茂草矣。余自崇祯戊辰,遂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缺勿书。故今所成书者,上际洪武,下讫天启,后皆缺之,以俟论定。余故不能为史,而不得不为其所不能为,固无所辞罪。然能为史而能不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执简俟之矣。
石匮书后集六三卷
此书为《石匮书》(洪武至天启)之续编,原拟只续至崇祯末年(见《与周戬伯》)《张子文秕·与周戬伯》:“……弟向修《明书》(《石匮书》),止至天启。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章奏,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论定。今幸逢谷霖苍文示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朝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馀卷,悉送文几,祈著丹铅。弟盖以先令鼎升之时,遂为明亡之日,并不一定载及弘光,更无一言牵连昭代。”。后经修订,增南明五王及诸臣传。
南图藏凤嬉堂钞本,格式同《石匮书》。另有藏钞本为刘氏天尺楼旧物。南图藏本题“《石匮书》后集六十三卷,附录一卷”。
是书为康熙初年张岱于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时应邀参加修撰《明史纪事本末》时始作,尔后续修而成。第二十六卷(钱谦益、王铎列传)、二十七卷(洪承畴、冯铨列传)、三十卷(郑芝龙列传)、三十一卷(吴三桂列传)、四十三卷(张春列传)、五十四卷(张煌言列传)、五十五卷(甘辉列传)均有目无文,实存五十六卷。
按,是书之名,当为抄辑者据内容所拟,而非张岱手定,与《石匮书》互为叉者约占三分之一,其中《甘辉列传》等系漏辑。
古今义烈传八卷
此书现存版本有:(一)八卷钞本,四册。卷首有祁彪佳序(《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编》。),藏浙江图书馆。(二)崇祯戊辰刻本,首陈继儒序、刘荣嗣序,刘光斗序、祁彪佳序、马如蛟序(缺)(均作于1628~1632年间)、自序(1628年作);次凡例(藏北图)。南图藏该版覆刻崇祯本有“昆山吴氏四福读书堂”藏书印。自序略云:
天下有绝不相干之事,一念愤激,握拳攘臂,揽若同仇。虽在路人,遂欲与之同日死者。余见此辈,心甚壮之,故每涉览所至,凡见义士侠徙,感触时事,身丁患难,余惟恐杀之者下石不重,煎之者出薪不猛。何者?天下事不痛则不快,不痛极则不快极。强弩溃痈,利锥拔刺,鲠闷臃肿,横决无馀。立地一刀,郁积尽化,人间天上,何快如之!苏子瞻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尝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余为之酣适。”余于节义之士,窃亦为然。当其负气慷慨,肉视虎狼,冰顾汤镬,余读书至此,每为之颊赤耳热,眦裂发指,如羁人寒起,颤栗无措;如病夫酸嚏,泪汗交流,自谓与王处仲之歌“老骥”而击碎唾壶,苏子美之读《汉书》而满举大白……余自史乘旁及稗官,手自钞集,得四百余人,系以论赞,传之劂剞,使得同志如余者,快读一过,为之裂眦,犹余裂眦;为之抚掌,犹余抚掌。亦自附子瞻之蓄药酿酒,不以为人,专以自为意也。龙飞崇祯戊辰(1628)鞠月,会稽外史宗子张岱读书于寿芝楼,秉烛撰此。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刻本自序中有“手自钞集,得四百馀人”之语,卷末载《古今义烈名籍》,谓是书“始于周镐京,迄于明崇祯甲申得五百七十三人,四百七十三篇。”又,此序与道光三年刻本序文字颇有异文。殆此为最早成书时所写之序,光绪刻本《自序》则为明亡后增订本序。
序末镌两阳文印,一为“陶庵”,另一印不可辨认(似为“文孙”二字)。又有凡例十则(略)。
史阙十四卷
《嘉庆山阴县志·书籍》著录:“史阙,无卷数,写本六册”。此“写本”是否为手稿本,不得而知。
是书内容“上自伏羲,下逮金元,有明一代不与焉……”。其所叙述,有异正史事同而文异者,有与正史全异者。“辩证博洽,持论平允,尤非熟读百史而得洵者。”郑佶编十四卷跋。
此书手稿为今人黄裳先生所藏。据黄氏叙录:“此稿本不分卷,分订六帙而已。原稿竹纸黑格,每面八行,白口单边。笔迹用纸与(稿本)《张子文秕》无异。”“卷首有大字序四页,序末题‘古剑陶庵老人张岱撰’,下钤‘张岱之印’,‘天孙’二印,俱白文。每卷首大题下署‘古剑陶庵张岱’。”(《黄裳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页。)
清光绪年间吴兴郑佶编本亦为十四卷,亦题“古剑陶庵张岱”。据郑佶跋,前此已有钞本,“唯纸色甚旧,摺痕皆断裂,殆非近时所钞”(郑佶编十四卷跋。)。南京图书馆藏有此版本。目录如次:卷一,三皇五帝纪;卷二,夏商周纪;卷三,春秋战国纪;卷四,西汉纪;卷五,东汉纪;卷六。三国纪;卷七,晋纪;卷八,南北朝纪;卷九,隋纪;卷十,唐纪;卷十一,后五代记;卷十二,北宋纪;卷十三,南宋纪;卷十四,辽金元纪。
《史阙》作意,见《张子文秕》卷一:
《春秋》书“夏五”,阙文也,有所疑而阙之也。如疑,何不并“夏五”而阙之?阙矣而又书“夏五”者,何居?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书之义也,不书义也,不书而又书之,亦义也。故不书者,月之阙也;不书而书者,月之食也。月食而阙,其魄未始阙也,从魄而求之,则其全月见矣。
由唐言之,六月四日,语多隐微,月食而匿也。太宗令史官直书玄武门事,则月食而不匿也。食而匿,则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则更之道存。不匿,则人得而指之,指则鼓,鼓则驰,驰则走。走者救也,救者更也。使太宗异日而悔焉,则更之道也;太宗不自悔,而使后人知鉴焉,亦更之道也。此史之所以重且要也。虽然,玄武门事,应匿者也,此而不匿,更无可匿者矣。余读唐野史,太宗好王右军书,出奇吊诡,如萧翼赚《兰亭》一事,史反不之载焉,岂以此事为不佳,故为尊者讳乎?抑见之不得其真乎?
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古今,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余又尝读正史,太宗之敬礼魏征,备极形至。使后世之拙笔为之,累千百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怀中”四字尽之,则是千百言阙,而四字不阙也,读史者由此四字求之,则书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阙哉?
清光绪末年,又有十五卷刻本,系加入原单行之《明纪史阙》而成。
明纪史阙—册
题“古剑陶庵张岱□”,为《史阙》之续集。清钞本,四十一页,半页八行,行二十字,版心有“鹤轩日稽”四字。记事起洪武,迄洪熙年间,最后一节有“补永乐”三字标题,仅钞完一行,可见钞写有缺略。无序跋,殆据张岱未完成之稿本传钞。
此书影印本见巴蜀书社《中国野史集成》第十四册。
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一册
此书为张岱晚年与徐野公(名沁,徐渭之孙)合作,1689年秋付刻,未及半而岱已逝世。镌版后存朱文懿家,乾隆戊子朱秉直付印。有蒋士铨序、张岱自序,陈仲谋、余火亘跋。岱自序末署“岁在滩(案即1680年)仲秋古剑老人识”。又有民国八年排印本,前载蔡元培序,岱自序末易署“庚申(1680)八月明后学张岱敬书”。自序云:
在昔帝赍良弼,即以图像求贤,而汉桓帝征姜肱不至,遂命画公图其形状。古人以向慕之诚,致思一见其面而不可得,则像之使人瞻仰者,从未尚矣。是以后之瀛洲、麟阁、云台、凌烟,以至香山九老、西园雅集、兰亭修禊,无不珍重图形以传后世。使后之人一见其状遂无汉武帝不得与司马相如同时之恨,亦快事也。
余少好纂述国朝典故,见吾越大老之立德、立功、立言以三不朽垂世者,多有其人,追想仪容,不胜仰慕。遂与野公徐子沿门祈请,恳其遗像,汇成一集,以寿枣梨,供之塾堂,朝夕礼拜,开卷晤对。见理学诸公则自愧衾影,见忠孝诸公则自惭有愧忠孝,见清介诸公则自恨纠缠名利,见文学诸公则自悔枉读诗书,见勋业诸公则自惜空蝗梁黍,见文艺诸公则惟恐莫名寸长。以此愧厉久之,震慑精神,严惮丰采,寤寐之地如或遇之,其奋发兴起,必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予不幸遭时变,禀承家训,恪守师资,一时景仰前贤,谂知不朽者其名,而不可得而共睹者其像,乃与同志为登门求像之举。诸贤裔鉴其诚,而慨然许之,或千里而惠寄一像,或数载而未获一图,积月累时,送完斯帙,夫岂直一手足之烈哉?至若是书是像之垂示无穷,而终于不朽,则所望于后之读是书者。古剑老人识。
张氏家谱卷数不详
《张子文秕·自为墓志铭》著录。存佚情况不详。
〔附〕明史纪事本末
清顺治十三年(1656),谷应泰(1620~1690)以户部郎中提督浙江学政。莅位后,设“谷霖苍著书处”于杭州西湖畔,主持编写《明史纪事本末》,慕张岱名,力邀参加修撰(同与共事者,另有陆圻、徐倬、张子坛等)。岱因生后无着,更为收集崇祯朝史料完成《石匮书后集》,于1572年破例应聘至杭,将《石匮书》借与谷氏参考,共撰写了《本末》约近五分之一的篇章(笔者曾将《石匮书》及《后集》与《本末》细加比勘,《本末》中与岱两书文字全同或部分相同者近14万字,无疑出自张岱手笔)关于《明史纪事本未》,有所谓谷氏以五百金购公书而成的传说。邵廷采《思复堂文集》(绍兴先正遗书本)卷三《明遗氏所知传》:“山阴张岱……长于史学……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藏书》……顺治初,丰润谷应秦提学浙江,修《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其书,〔公〕慨然曰:‘是固当公之谷君,得其人焉。”邵氏此说出,附和者较多,如温睿临《南疆逸史》列传卷三九、陆以《冷庐杂识》卷九“窍人之书”条等。这个问题牵涉问题较多,兹从略。据笔者初步考察,《纪事本末》取材虽不止一家,但取自张岱《石匮书》者为最多,(详拙文《张岱与〈明史纪事本末〉》。)。岱在杭近一年,馀除参加集体修书外,另利用谷氏所藏史料,自成《石匮书后集》数十馀卷(全书未完成,后续有增补参见前文)。
〔附〕会稽县志
康熙壬子(1672),会稽续修县志,当局者礼请张岱主修,岱力辞不获允。《张子文秕·与张噩仍(名文成)》书云:“不肖以废弃陈人,株守泉石,并不与闻户外之事,而郡县不知何所见闻,乃以《会稽志》事相属。不肖辞让再三,不得俞允。正在踌躇,赖有宗肯毅然任事,不容糗粮,纤集多入,钞写誊录……不肖在局,亦仅可坐啸画诺,饮酒食肉而已。故于‘凡例’之外,不敢多赘一字,盖至慎也。卷首书名,自当以宗兄为首事纂修,不肖列名校阅,亦邀荣甚矣。不晓当事何意,又以贱名纂列兄前,而并不用兄原本,乃属董兄舜邻……”张岱因不满意董氏原稿“挂一漏九,留三增七”,体例杂乱,特向张噩仍倾吐衷曲,再次转托力辞,于全《志》仅起草了《凡例》十则。张氏为著名史学家,这十条“凡例”是研究张岱史志学思想的重要材料。
陶庵梦忆八卷
《陶庵梦忆》最早之凤嬉堂钞本,藏国家图书馆。其馀存世版主要有:
金忠淳刻《砚云甲编》本。首有一序,略云:“陶庵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匮》一书。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今已矣,三十年来,(老人)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间策杖入市,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遂更名曰蝶庵,又曰石公。其所著《石匮书》,埋之琅琊山中。所见(?)《陶庵梦忆》一书,为序而藏之。”按,此序无撰人名氏,从“三十年来,杜门谢客”等语看,序当作于甲申(1644)后三十年即1674年前后,其时张岱还在世;又云“为刻而藏之”而不曰“序而刻之”,显然非编刻者语。序为原钞本所有,或为张岱在世时其友人所作,或为岱晚年所作之又一序(张岱《梦忆·自序》作于1646年),此序从内容文字风格上看,当为张岱于1744年前后所作另一序。有编者金忠淳跋,谓原本得自“舅兄”胡学林。
王文语刻本。乾隆五十九年刻,大版;又有道光初王介臣刻巾箱本,书名仅题《梦忆》二字。
粤雅堂丛书本。有“咸丰壬子重阳日南海伍崇曜跋。此本刊刻精良,为流传较广之本。”
是书现当代刻本甚多,有俞平伯点校本(朴社民国八年版)、“美化文学丛刊”本等,以俞氏点校本影响最大。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马兴荣氏点校本(与《西湖梦寻》合刊;惜缺四条),校勘较精,堪称佳本。
《陶庵梦忆》为张岱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盖以国变之后,意绪苍凉,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寓于全书,“情真意挚,引人入胜”,确为明末小品文之极范。
西湖梦寻五卷
是书有康熙丁酉(1717)凤嬉堂原刊本,藏国家图书馆。首载“潞溪白岳王雨谦”、“弟祁豸佳”序(署“书于仙庐”)、“社弟查继佐”序、“武林道隐”(金堡)序、“古夔旧史”李长祥(研斋)序。诸序均作于1774年前后。有张岱自序,作于1671年七月十六日,序称: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歌楼舞榭,弱柳夭桃,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因想余梦与李供奉异。供奉之梦天姥也,如神女名姝,梦所未见,其梦也幻。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载,梦中犹在故居。旧役小厮,今已白头,梦中仍是总角。夙习未除,故态难脱。而今而后,余但向蝶庵岑寂,遽榻纡徐,惟吾旧梦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也。儿曹诘问,偶为言之,总是梦中说梦,非魇即呓也。第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犹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竟来共舐其眼。嗟嗟!金齑瑶柱,过舌即空,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岁辛亥七月既望,古剑蝶庵老人张岱题。
夜航船二十卷
此书为一分类知识性辞典,其写作宗旨见书前《自序》(《张子文秕》卷一亦载此文):
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盖村夫俗子,其学问皆预先备办,如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稍差其姓名,辄掩口笑之。彼盖不知十八学士、二十八将虽失记其姓名,实无害于学问文理,而反谓错落一人,则可耻孰甚。故道听途说,只办口头数十个名氏,便为博学才子矣。余因想吾越,惟馀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或曰:“信如此言,则古人姓名,总不必记忆矣。”余曰:“不然。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如八元、八恺、厨、俊、顾、及之类是也;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如四岳、三老、臧毂、徐夫人之类是也。”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说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人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极浅之事,吾辈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
陶庵对偶故事二册
“二册,稿本”(《黄裳书话》著录)。未见。案,此书殆后人集《快园道古》及《西湖梦寻》、《琅文集》等书中柱铭撮抄而成。《柱铭钞》序见《张子文秕》卷一。
陶庵肘后方四卷
未见著录,殆已佚。唯序见《张子文秕》卷一,略云:
曾记竹庭与余说:“一日,梦中喧嚷杂沓,说上帝宴天医。多人赴宴,竹庭与焉。及在席,衣冠者三四人,而内多缁衣黄冠,乞儿贫子,鹑衣百结、提囊负笈之辈。盖草泽医人,其以丹方草头药活人为多,故天宴亦多此辈也。余家向有大父所集方书二卷,葆生叔所集丹方一卷。”余闻竹庭言,遂有意丹方草头药。凡见父老长者、高僧羽士,辄卑心请问,及目击诸病人有服药得奇效者,辄登记之。积三十馀年,遂得四卷,收之箧囊,邂逅旅次,出以救人,抵掌称快。因忆欧阳文忠公语:人有乘船遇风,惊悸而得疾者,取多年拖牙为长年手汗所渍处,刮末服之而愈。良医用药,多以意造。若吴竹庭之疗吾先大夫,匠意而出,不拘古方,与草泽医人用草头药者,亦复何异?盖竹扇止汗,破盖断虐,此中实有至理,殆未易一二为俗人道也。
张子说铃
《张子文秕·自为墓志铭》著录,序载《张子文秕》卷一:
说何始乎?《论语》始也。说何止乎?《论语》止也。《论语》之后无《论语》,而象之者《法言》也。《论语》卒不可象,而止成其为《法言》者,亦《法言》也。何也?象者像也。方相氏虎目执戈以怖鬼,童子蒙虎皮以怖人,鬼与人卒不可怖,而方相氏、童子止自怖者,自怖然后谓可怖鬼,可怖人也。
余之为说也,则异于是。食龙肉,谓不若食猪肉之味为真也;貌鬼神,谓不若貌狗马之形为近也。余主何说哉?言天则天而巳矣,言人则人而已矣,言物则物而已矣。余主何说哉?尝片脔而定其为猪肉,则其味不能变也;见寸而呼其为狗马,则其形不能遁也。何论大小哉?亦得其真,得其近而已矣。大块风也,窍亦风也;又海水也,人之津液涎泪无不水也。
扬雄氏之言曰:“好说而不见诸仲尼,说铃也。”铃亦何害于说哉?秦始皇振铎驱山,而山如鹿走。铃,铎属也。
诗韵确
《张子文秕》著录,自序见《张子文秕》卷一。存佚情况不详。
奇字问
未见著录,亦未见有传本,殆其书已佚,自序尚存,载《张子文秕》卷一,明作书之旨:
夫《尔雅》不识字书不见字学之难穷也,自古记之矣。余内手扪心,胸中贮有几字,敢学扬子云乃来玄亭问字也?然余尝见人读书,及自读书,目数行下,奇字历落,不究训诂,混入眼中,若可解,若不可解,如人忙中吃饭,泥沙与沫饽同咽,骼与沫饽同啜者多矣。有旁观者,摘一二字诘之,始茫然不能置对。如或不问,则终身安之无忤也。余不能博闻洽记,近取《左》、《国》、《史记》、《两汉》、《文选》、《庄》、《列》、《韩》、《管》诸书,在人耳目前者,聊摘其一二奇字解释之,以自问问人,颇有奥义。犹之天台、雁宕、五泄、洞岩,近在鞋下,天下人裹粮宿舂,千里来游。问之山下里人、鲐背苍,多有不至者,咫尺松楸,茫然如云雾,亦是大可笑事。又有如越人食彭蜞桀步,稚子狎弄,而山东人见之,以为鲨虎,无不惊走。举以告越人,越人亦第笑之而已。余所辑字义,有如彭蜞桀步之类,人见之而惊者,存以待人之问。又有如天台、雁宕,人问及而余之不知者,存以自问,以待人之问。故名之曰《奇字问》焉。虽然,余以为奇,而人且耳而目之者久矣。渔者握,妇人拾蚕,则是其所见不同也,以此嘲余,余不任受。
朗乞巧录一册
未见著录。手稿本。藏国家图书馆特藏部。分类辑录古今哲人智士的隽言妙语。前有自序云:
余生来愚拙,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凡见人有智慧之事、智慧之言,心窃慕之,不能效法。曾闻人言:“牛女星旁,有一星名朗,男子于冬夜祀之,得好智慧。故作《乞巧》一编,朝夕弦诵,以祈朗。倘得邀惠慧星,启我愚蒙,稍窥万一,以济时艰,虽不能传灯钻锐以大展光明,囊萤映雪,藉彼微茫闪烁,以掩映读书,徼幸多多矣。”殆为作者临终前不久所书。
桃源历一卷
《张子文秕著录》,自序见《张子文秕》卷一。
老饕集卷数未详
书未见,殆亦已久佚。此书系据《饔史》订正增补而成。惟序尚存于《张子文秕》卷一,略谓:“余大父与武林涵所包先生、贞父黄先生为饮食社,讲求正味,著《饔史》四卷,然多取《尊生八笺》,犹不失椒姜葱,用大官炮法。余多不喜,因为搜辑订正之。穷措大亦何能有加先辈,第水辨渑、淄,鹅分苍、白,食鸡而知其栖恒半露,吸肉而识其炊有劳薪,一往深情,余何多让,遂取其书而拴次之。割归于正,味取其鲜,一切矫揉泡炙之制不存焉。虽无食史、食典之博洽精腆,精骑三千,亦足以胜彼赢师十万矣。鼎味一脔,则在尝之者之舌下讨取消息也。”
皇华考一卷
《张子文秕》著录,自序见《张子文秕》卷一。
博物志补十卷
周作人《知堂书话》著录:“宗子《和陶诗·和赠长河公》序云:‘博闻洽记,余慕吾家茂先因于读《礼》之暇,作《博物志》十卷,以续其韵。’”(《知堂书话》海南出版社,上册第678页。)
茶史卷数未详
见《陶庵梦忆·闵老子茶》录,未注明卷数。书今末见,仅存序文,载《张子文秕》:
周又新先生每啜茶,辄道白门闵文水,尝曰:“恨不令宗子见”。一日,文水至越,访又新先生,携茶具,急至予舍。余时在武陵,不值,后归,甚懊丧。戊寅,余至白门,甫登岸,即往桃叶渡访文水。时日晡矣。余至文水家,文水亦他出,余坐久。余意文水一少年好事者,及至,则瞿瞿一老子,与余叙款曲,愕愕如野鹿不可接。方欲纵谈,而老子忽起曰:“余杖忘某所,去取杖。”起席,竟去。余曰:“今日岂可空去?待其返,更定矣。”老子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尚在何为者?”余曰:“周又老尝道闵先生精饮事,愿借馀沥以解渴思。”文水喜,即自起当炉,茶旋煮,速如风雨。导至一室,幽窗净几,荆溪壶及成宣窑瓷瓯十馀具,皆精绝。余问老子曰:“此茶何产?”老子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老子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甚也。”老子吐舌曰:“奇!奇!”余问水曰:“何水?”老子曰:“惠水。”余又曰:“莫绐余,惠水至此千里,岂有水之圭角毫芒不动,生磊若是乎?”老子曰:“不复敢隐,舍间取水,必俟惠山人静,夜分涸其井,淘洗数次,至黎明,涓流初满,载以大,藉以文石。舟非风则勿行。水体不劳,水性不熟,故与他泉特异。”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老子自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也。向瀹者,的是秋采。”老子大笑曰:“余年七十,精饮事五十馀年,未尝见客之赏鉴若此之精也,五十年知己,无出客右。岂周又老谆谆向余道山阴有张宗老者,得非客乎?”余又大笑,遂相好如生平欢,饮啜虚无日。因出余《茶史》细细论定,以之以授好事者,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战也。
历书眼不分卷
《张子文秕》著录,自序见《张子文秕》卷一。
徐文长逸稿(辑)
是书为张岱搜辑之徐渭未刊稿,卷首有其祖父张汝霖序、王思任序,书成于张岱十九岁时(1615)。王序称:“……袁中郎从陶周望架上得其《朗篇》等集,一夜狂走,惊呼拜跪,业已梓播人间。而张文恭父子雅与文长游好,闻见既多,笔札饶办。其孙宗子箕裘博雅,又广搜之,得逸稿,分类若干卷。读其文,似厌薄五侯之镣,独存蔬笋之味。又如着短后之衣,缒险一路,杀讫而罢,读其诗,点法、倒法、脱法、藏法,漉趣织神,每在人意中,攘脆争可,巧进口头,必不能出者,而文长一语喝下,题事了然。读其四六,在黛眉淡骨之间。读其隐字、对偶诸技,以天成者佳,以人胜者逊,通方言者佳,以越语者逊。总之,灵异立成,爪发皆矗,予断以龙鬼精怪之文,起文长而署之,应以牍受,为我楚舞,饮八斗而醉二参也。是集也,经予谈阅者什三,予有博虎之思,止录其神光威渖,欲严文长以爱文长。而宗子有存羊之意,不遗其皮毛齿角,欲仍文长以还文长。谋不同而道自合,海内愿沽者众,其必有以处兹玉也矣。”(《王季重十种》,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是书有天启刊本(现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一卷冰雪文卷数未详
《张子文秕》,为张岱所自选之诗、文合集。书今未见。自序存《张子文秕》卷一:
余选《一卷冰雪文》,而何以附有诗也?余想诗自《毛诗》为经,古风为典,四字即是碑铭,长短无非训誓。摩诘佞佛,世谓诗禅;工部避兵,人传诗史。由是言之,诗在唐朝,用以取士,唐诗之妙,已登峰造极。而若论其旁引曲出,则唐虞之典谟、三王之诰训,汉魏之乐府,晋之清谈,宋之理学,元之词曲,明之八股,与夫战国之纵横,六朝之华赡,《史》、《汉》之博洽,诸子之荒唐,无不包于《诗》之下已。则《诗》也,而千古之文章备于是矣。至于余所选文,独取“冰雪”。而今复以“冰雪”选诗者,盖文之冰雪,在骨在神,故古人以玉喻骨,以秋水喻神,已尽其旨。若夫诗,则筋节脉络、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气沐浴其外,灌溉其中,则其诗必不佳。是以古人评诗,言老言灵,言隽言古,言浑言厚,言苍茜,言烟云,言芒角,皆是物也。特恨世无解人,其光华不得遽发耳。昔张公凤冀,刻《文选纂注》,一士夫诘之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张曰:“昭明太子所集,于仆何与?”曰:“昭明太子安在?”张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张曰:“便不死,亦难究。”曰:“何故?”张曰:“他读得书多。”余藉斯语,亦以解嘲,故仍题之日《一卷冰雪文》。
琅诗集五卷
此书未见张岱本人著录,然《自为墓志铭》著录有《琅文集》,殆诗文合刊而分刻之选本。《诗集》有张岱自序、张弘序。自序云:
余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诗,而并学喜文长之中郎诗。文长、中郎以前无学也。后喜钟、谭诗,复欲学钟、谭诗,而鹿鹿无暇,伯敬、友夏,虽好之而未及学也。张毅孺好钟、谭者也,以钟、谭手眼选明诗,遂以钟、谭手眼选余之好钟、谭而不及学钟、谭之明诗,其去取故有在也。张毅孺言余诗酷似文长,以其似文长者姑置之,而选及余之稍似钟、谭者。余乃始自悔,举向所为似文长者悉烧之,而涤骨刮肠,非钟、谭则一字不敢置笔。刻苦十年,乃问所为学钟、谭者,又复不似。盖语出胞胎,即略有改移亦不过头面,而求其骨格,则仍一文长也。余于是知人之诗文如天生草木花卉,其色之红黄、瓣之疏密,如印板一一印出,无纤毫稍错。世人即以他木接之,虽形状少异,其大致不能尽改也。余既取其似文长者而烧之矣,今又取其稍似钟、谭而终似文长者又烧之,则余诗无不当烧者矣。余今乃大悟,简余所欲烧而不及烧者悉存之,得若干首,钞付儿辈,使儿辈知其父少年亦曾学诗,亦曾学文长之诗,亦曾烧诗之似文长者,而今又复存其似文长之诗。存其似者,则存其似文长之宗子;存其似之者,则并存其宗子所似之文长矣。宗子存而文长不得存,宗子、文长存而烧文长,文长之毅孺,亦不得不存矣。向年余老友吴系曾梦文长,说余是其后身,此来专为收其佚稿。及余选《佚稿》,而其所刻诸诗,实不及文长以前所刻之诗,则是文长生前已遂不及文长矣。今日举不及文长之文长,乃欲以笼络不必学文长而似文长之宗子,则宗子肯复受哉?古人曰:“我与我周旋久,则宁学我。”甲午八月望日,陶庵老人张岱书于快园之渴旦庐。
按,张岱自序乃针对张弘(毅儒)序而发,张序云:
吾选宗子诗,不敢存宽严二字,但阿吾所好而已。杜工部,诗家集大成者。历下之选一工部,竟陵之选,又一工部,总以成工部之大,无所不有而已。吾越徐文长,昭代诗豪,其诗酷似工部。宗子咏物诸篇又酷似文长。吾疑宗子曩所刻《文长佚稿》,或多宗子拟作,即如米南宫伪造晋人书贴,使人不可复辨。若以宗子诸诗与文长并驱中原,便可谓吾越有两文长也。吾近选《诗存》,去取文长诸诗,不能存十一。曹公曰:“缚虎不得不急。”以文长、宗子诸诗雄视一代,气魄难训,假操觚者不别存手眼,狠着钳锤,便当死其一句一字之下,岂有丹铅复及馀子哉?宗子名下,屈第一指,著作已流传海内。吾与宗子总角交契三十年,相视莫逆如一日,即其诗篇,咄咄惊奇,连章累牍,便可高踞汉、唐之上,而犹不能买菜求添,强吾所不好,此亦曹公缚虎之意也。吾故于宗子诗选录若干入《明诗存》讫,而复笔其篇端云。己丑重九日小弟〔弘〕首题并书。
此书有作者手稿本,题《琅文集》,然有诗无文。有单页手稿粘贴书中,可见是未经完全编定之底稿。原为朱氏别有斋旧藏,现藏黄裳先生处。此本校通行本多《礼宗十章》、《孝陵磨剑歌丁亥七月十六日项里记梦》、《百丈泉(剡中灵院)》、《康衢篇赠陈子申》、《为陆子姑起病》、《姑苏张载之携琴访余,今年正七十大寿》、《野老哭十首》(缺八首)等近三十首。因系手稿,未经改篡,其中抒发反清复明之志的诗篇、均得完整以保存,十分珍贵。中有评语,与国家图书馆藏《张子诗秕》钞本评语字迹同,为王雨谦手迹。
张子诗秕五卷
此书国家图书馆藏凤嬉堂钞本,格式与《张子文秕》相同。合《张子文秕》十八卷,凡二十三卷,内《张子诗秕》五卷,题“陶庵张岱著,白岳王雨谦评,雪瓢祁君佳校”。有自序及王雨谦、祁豸佳序、张弘序。
藏清钞本编次同,文字与北图原抄本间有小异。此二种均妙本钞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与手稿本较,反清内容几删芟、修改净尽。惟诸家序文暨王雨谦评语(较稿本为多),为稿本所缺,独此本存,弥足珍贵。
王雨谦序《张宗子诗叙》为王氏手书。《叙》中不仅高度评价张岱诗作,且首次将《石匮书》与《史记》进行比较评论,十分珍贵兹全录如次(惜经虫蛀,已缺百馀字):
予读宗子诗,而忽慨然于司马子长也……吾固谓子长史才也,实诗才也,而不以诗显;千载之后,张宗子则起而兼有之……庙器宜不独以著书,乃以彼其才处祯朝,遇思庙尧舜主,而竟以文学者老之,且以甲申之变,穷愁著书,乃如渴司马与腐司马,一如无汉武之朝不可得,盖亦悲矣!然而三十年苦思,《石匮》告成,特与《史记》并有今古。即俾宗子不作诗,《石匮》中未尝无诗也。试读其诗,则于今昔之变,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其诗又特一史也,而非失世之诗也。磋乎,子长故言之:“诗三百篇大圣贤发愤所作也”,知诗哉!故使子长而与宗子遇,则子长未尝无诗,宗子正亦不必为诗也。两人之诗皆在史也。特以两人之遇主不同,而终处世又不同。孟子曰,颂其诗必论其世。则宗子之作史与子长之作史已自有异,是其所谓诗者即欲不作,亦安得不作乎?悲歌行国,泣数行下,如屈子《离骚》,不得其平则鸣。吾于宗子,曷怪哉?至若宗子之为人,豁达有大节,则海内鲜不闻之,其为诗则卓然张宗子之诗,非诸子之诗,而并非三百篇之诗也。非诸子之诗,而并非三百篇之诗也。此其说在伯乐之相马也,故不必扩之为世人与言耳。(北图藏凤嬉堂钞本《张子诗秕》页一a页二a,)此序末署“庚子(1660)夏五潞溪识字田夫王雨谦撰”。
案,张岱诗集自序作于清顺治甲午(1654),时年五十八,标明为《琅诗集自序》,而《张子诗秕》收诗至作者去世前一年(《己未元旦》,己未为1679年),显系选者从作者五十八岁以后诗中选钞,其书名殆亦系选者所加。而封面又总题曰《张子文秕》,曰“诗秕”云者,盖未为作者认可(王雨谦序未标集名,题为“张宗子诗”)。
琅文集六卷
是书有康熙凤嬉堂刻本,卷首有祁彪佳、王雨谦序。王序称:
有大文之人而文始传。文也者,人也。其人为天地所属,则凡天地之所焕不能郁,与郁而不克告之天下万世者,皆汇而委诸其人。由是而日星之蒸变,河岳之苞孕,勤勤焉提以成之也。然其所际有显晦,且有不即内之于显,而困苦拂乱,与以晦晦之遇,而别有以显之,则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如昔左氏《春秋》、龙门《史记》,皆不屑以爵禄荣之,而特荣以三曾之大也。吾故于陶庵张子之文,而知天地之成之显之者深且宏也。陶庵为雨若公之孙,而阳和公其曾祖父也。阳和公以文章大魁天下,雨若先生成进士,以理学推醇儒。陶庵尊人大涤公抱命世才,虽仕藉,竟不克大展其学,乃举累代清淑之气,尽以钟之陶庵。陶庵自束发为文,发藻儒林,以彼其才,使其立取一名,身都显要,自当复命造物,爽爽不怍,而以才大莫器。有识者成为裂眦问天,而陶庵怡然听之,遂潜名成《石匮》一书,上与《左》、《史》等鼎。甲申以后,屏弃浮云,益肆力于文章,自其策论、辞赋、传记、笺赞之类,旁及题额、柱铭,出其大力,为能登之重渊,而明诸日月,题日《琅文集》。盖其为文不主一家,而别以成其家,故能醇乎其醇,亦复出奇尽变,所谓文中之乌获,而后来之斗杓也。余与陶庵以气谊文章为世外交,每一篇出,无不披华食实,如李才江之范金呼岛佛,柳柳州之盥薰读《昌黎集》也。兹者百家争喙,俾斯集行之于世,则震风凌雨,应知夏屋之为也。陶庵其先蜀产也,其近则越产也,其人其文,几几各争有之。余则曰:“此非蜀之有,越之有,而天下之有也。张子,天下才也”。
祁序称:
越故多才,其所最著者,宋有陆放翁,元有杨铁崖,明有徐青藤。后来才士所生不少,以沉埋帖括,淹屈多人,间有进贤纱帽,游戏古作,视为绪馀。神宗朝,吾越中以古文名者三先生,一为陆景邺,一为王谑庵,一为倪鸿宝。陆长于武断,其蔽也敢;王长于撮巧,其蔽也狎;倪长于征僻,其蔽也鬼。较之前代,三贤尚难学步,而其所刻文集,又皆荣不择茅,金常夹砾。此虽作者之过,而选之者亦不得不任其责矣。钟伯敬曰:“选者之力,能使作者读者之精神心目为之顿易。故夫选而后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陶庵所作诗文,选题选意选句选字,少不惬意,不肯轻易下笔,凡有所作,皆其选而后作者也。其后汇所存稿,悉简其代作、应付诸篇什,尽付一炬,有所存贮,又皆其作而自选者也。今兹选刻稿尚盈笥,王白岳又为之痛芟雠校,在十去七。所定《琅》一集,譬之文豹留皮,但取其神光威沈;孔雀堕羽,只拾其翡翠金辉。淘汰簸扬,选择最核。以视前代,即放翁之《剑南》、《渭南》,铁崖之《乐府》、《史钺》,青藤之《樱桃馆》、《阙编》,何遂能过之也?盖陶庵先为蜀产,后生会稽,以嵯峨渫之奇,席万壑千岩之秀,其所脱胎结撰,自合磊坷韵秀,亮拔不群。此其生质使然,岂可与之争锋角胜乎?昔李研斋见《石匮书》,力争陶庵决非浙产,言及先世,始哗然大笑,自谓知人。其藻鉴之确,信有以也。
又有王介臣刻本,卷首有光绪三年黎培敬序、王惠跋及光绪丙子王介臣“书后”,文繁不录。民国二十四年“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刘大杰点校),即以王刻本为底本。
张子文秕十八卷
是书依文体分卷,内容与《琅文集》大致相同。凤嬉堂黑格钞稿本,藏国家图书馆,版心有“凤嬉堂”三字,题“陶庵张岱著,白岳王雨谦评,雪飘祁豸佳校”。篇中有王雨谦评语。卷着载手写之“曲辕社弟王雨谦撰并书”之序(与《琅文集序》同)及“同学弟雪飘祁豸佳序”。
昌谷集解
见《张子文秕·自为墓志铭》及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著录。其书成书于1638年《祁忠敏公日记·山居掘录(丁丑)》九月十日条:“得张宗子书,示以所注李长吉诗。”,今未见。自序则存于《张子文秕》卷一:
长吉诗自可解,有解长吉者,而长吉遂不可解矣。刘须溪以不解解之,所谓吴质懒态,月露无情,此深解长吉者也。吴西泉亦以不解解之,每一诗下,第笺注其字义出处,而随人之所造以自解,此亦深解长吉者也。有此二人,而余可不复置解矣。乃余之解长吉也,解解长吉者也。凡人有病则药之,药之不投,则更用药以解药,所谓救药也。药救药,药复救救药,至于不可救药,而病者真死矣。故余之解,非解病也,解药也。夫药亦有数等,庸医杀人,着手即死者无问矣。乃有以偏锋劫剂,活人什三,杀人十七者;有以大方脉、官料药,堂堂正正,而手到病除者;乃有草泽医人,名不出于里,而以丹方草头药起人于死者;乃有不用刀圭,不用针砭,而第吸其夜半沆瀣之气,而使其自愈者。疗之之法不同,而用以疗病则一。至病一愈,而药与不药等。等不一之药,皆可勿用矣,安用救药哉?故徐青藤、董日铸用劫药者也,吴西泉用官料药者也,刘须溪则不用药者也。若余则何居?余则远谢雷公,不问岐伯,服参术多,则用山药萝卜菔汁解之,服生熟多,则用大黄、芒硝解之。道听途说,为一日草泽医人,而病已霍然除矣。故曰:余之解,非解病也,解药也。
越绝诗
未见著录,自序则《张子文秕》卷一。
柱铭钞
未见著录,然《自序》尚存。自序云:
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传之自文长始。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自《逸稿》刻柱对,而越之文人竟作柱对。然越之文人之竟作柱对,未作时,先有一文长横据于其胸中,既作时,又有一文长遮盖于其面上。故用学问者多失之板实,用俚语者多失之轻佻,文人之学文长者,实多为文长所误。然学文长而全学文长之恶套者,则文长又为学文长者所误。余故学文长而不及文长,今又不敢复学文长,则伥伥乎其何适从耶?我越中崛强,断不学文长一字者,惟鸿宝倪太史,而倪太史之柱对有妙过文长者。而寥寥数对,惜其不及文长之多。则余之学文长而不及文长者,又何取乎?其多过文长耶?乃友人不以宗子为不及文长,而欲效宗子之刻文长,每取文长以夸称宗子。余自知地步远甚,其比拟故不得其伦,即使予果似文长,乃使人曰文长之后复有文长,则又何贵于有宗子也?余且无面目见鸿宝太史,何况后之文人!
蜀鹃舌血录
见《祁彪佳集》著录。其书今未见。
乔坐衙
杂剧。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剧品》著录。陈洪绶《宝纶堂集》有《张宗子乔坐衙剧题辞》:“吾友宗子,才大气刚,志远学博,不肯俯首牖下。天下有事,亦不得闲置。吾宗子不肯俯首,而今俯首;不得闲置,而今闲置之。宗子能无言田亩乎?《乔坐衙》所以作也。然吾则为宗子何必如是也?古圣先贤,怀其宝走四方,不遇则进学弥笃。即使宗子少年当事,未免学为气用,好事喜功。今日之阻,当进取圣贤,弗以才士能人自画,损下其志气,复温故书,深究时政,三年间可上书天子。吾不为宗子忧也。然吾窃观明天子在上,使宗子其人得闲而为声歌,得闲而为讥刺当局之语,新辞逸响,和媚心肠者,众人方连手而赞之美之,则为天下忧也。”
冰山记
传奇剧本。《陶庵梦忆》有《冰山记》一则,提及此书。此剧系张岱根据他本改成,演魏忠贤事,曾在绍兴、兖州等地演出。今存佚情况不详。
评东坡和陶诗(附张岱补和陶诗)一册
《知堂书话》:“《评东坡和陶诗》,汉阳朱氏抄本。署戊子冬,胤字缺笔,当是乾隆三十三年。后附补和二十四首,书眉亦有评语,或是王白岳等人手迹耶?”
“宗子对于东坡殊不客气,评渊明诗固多倾倒,但也有一两处,如《答鲍参军》批云:‘亦是应酬语’;又《和胡西曹》批云:‘陶诗亦复不佳。’语甚戆直,陶诗评中殆不多见,颇有意思。宗子《和陶诗》有小引云:‘子瞻喜彭泽诗,必欲和尽乃已,不知《荣木》几篇何以尚遗什之二。今余山居无事,借题追和,已尽其数。子瞻云:古人无追和古人者,追和古人自子由始。乃今五百年后,又有追和古人者为之拾遗补阙,子瞻见之,得不掀髯一笑乎?’”(《知堂书话》上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4、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