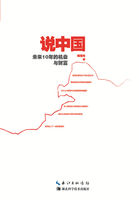王蔚
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早年的随笔集《学林漫步》,新版中增加了十余篇近年撰写的文章。[1]这本书中,讨论史学研究的《外国史研究》和《中国文史之学的危机与转机》,以及怀念周一良的《长使书生泪满襟》都提到了一位他在台湾大学就读时的老师,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史学博士的徐子明。[2]对这位师长最详尽的记述是书中收录的《怀念宜兴徐子明先生》,在这篇长文里,汪荣祖以敬仰的笔调回顾了徐子明的生平,一个忧心中国文化命运的博学大儒形象跃然纸上。遗憾的是,文中对徐氏求学、任职经历的记叙,对其道德学问的褒扬实际上充满虚构和夸饰,严重背离了史家应有的严谨。
学历之谜
据《怀念宜兴徐子明先生》所述,徐子明名徐光,1888年出生,江苏宜兴人,自幼通读四书五经,1902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与陈寅恪同学,十九岁即1907年时从南洋公学毕业。[3]汪荣祖早在1976年便出版了《史家陈寅恪传》,此后又数次修订重版,对陈氏的生平理应了如指掌。然而陈寅恪从未在南洋公学读书,他在上海只就读过复旦公学。[4]在《史家陈寅恪传》中,汪荣祖并没有弄错这一基本情况:“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陈寅恪)考入吴淞复旦公学,为插班生,同班同学中有后来留德获海德堡大学史学博士的徐子明。”[5]姑且认为汪氏在写《怀念宜兴徐子明先生》时不慎出现笔误,将复旦公学写成南洋公学,但两书中的时间又发生了明显的矛盾:陈寅恪1907年入学,徐子明1907年毕业,二人怎么会是同班同学呢?
根据复旦大学档案馆馆员孙瑾芝、杨家润在《陈寅恪入复旦公学年月及是否毕业考》中提供的资料,陈寅恪在该校档案馆所藏复旦公学1908年春季的学生名册中是备斋丁班生,入校的时间为1905年秋。[6]复旦公学当时有甲至庚共七级学生,其中甲、乙、丙为正斋生,丁、戊、己、庚为备斋生。复旦公学属高等学堂性质,正斋为“大学之预备”,备斋则是正斋的预备。[7]1930年编制的《复旦大学同学录》中,收有从复旦公学到复旦大学的历届毕业生名单。在1908年第一届高等正科(即正斋生)的8名毕业生里,有位名叫徐仁锖的人。[8]结合徐仁锖、徐子明这两个名字的留学和任教经历可以断定(详见后文),徐仁锖就是徐子明的原名。1908年,当陈寅恪还是一名备斋生时,徐仁锖已经从正斋毕业了,可见二人至多只是校友,并非同班,原不必硬拉陈氏充作徐氏的背景。
陈寅恪与南洋公学无关,徐仁锖却的确在南洋公学读过书。在1926年出版的《南洋大学卅周纪念校友录》中,历届学生名册里便有徐仁锖的名字,注为“号佩铣”,[9]但没有详细的个人信息,也没有记录在校时间。1902年,南洋公学中爆发风潮,部分学生愤而退学,后进入马相伯出资创办的震旦学院就读。1905年,由于与校中任教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发生冲突,马相伯率学生退出震旦,随后另组复旦公学。[10]从时间上看,徐仁锖当是先入南洋公学,后入复旦公学,且很可能经历了从南洋到震旦再到复旦的轨迹。
对于徐氏此后的求学生涯,汪荣祖的描述是:“宣统二年(1910年),徐先生考取首届庚款留美,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习西洋史,不到三年,于民国元年(1912年)获得学士学位(B。A。),因成绩优异,并通多种欧洲语文,又有一篇论文受到一位德籍教授赏识,遂由该教授推荐赴德,入著名的海德堡大学专修西洋中古史,在两年内《中世纪之特色》(Die Eigentümlichkeiten des Mittelalters)为题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Dr。Phil。)。”[11]在汪荣祖看来,“能以如此短速的时间内完成学业”,“足见其能力之高超以及学问之丰硕”,[12]可惜这段天才般的留学经历却丝毫经不起推敲。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多余部分,中美双方随后商定自1909年起每年派一定数量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3]1909年7月,游美学务处成立,9月举办第一次留学考试。汪荣祖将首届庚款留美的时间写成1910年,属于基本史实错误。这次留学考试录取47人,其中姓徐的学生有两位。[14]从籍贯和留美的学校、专业可以判断,他们显然都不是徐子明。而通过了初试进入复试的68人名单中,[15]也没有徐氏其人。
1910年7月,游美学务处举办了第二次庚款考试。初试考国文和英文两科,平均分数及格者均予以录取。共有272人进入初取名单,其中出现了徐仁锖这个名字。[16]初试放榜后,紧接着又进行了为期三天,包括多门科目的复试,最终录取70名考生获留美资格。复试内容偏重于理科,考生的排名也因此与初试有了很大变化,如初取名列榜首的傅骕在复试后便落到了第23名。[17]初试考了第10名的胡适复试时对“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几门理科自觉“很不得意”,结果名列第55.[18]徐仁锖虽然在初试中位列第25,复试后却落选了。
复试成绩不够,没能直接留美的这部分学生也有去处。“其各科学力深浅不齐,而根柢尚有可取,年龄亦属较轻之各生,亦经从宽选取一百四十三名,拟俟新建肄业馆落成,收入高等科,分班肄习,以资预备。”[19]徐仁锖便是被录取到游美肄业馆高等科的143名学生之一。[20]1911年2月,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4月正式开课。6月,留美考试再度举办,从清华学堂高等科学生中录取了61人(另有两名中等科学生)作为第三批庚款留美生,这次徐仁锖入选了。[21]1911年7月游美学务处上报的这份名单中,徐仁锖的年龄为21岁。汪荣祖文中称徐氏出生于1888年,则1911年时徐氏实际年龄应为23岁,按中国传统的计龄方式为24岁。1909年外务部制订庚款留美考试办法时,对考选学生的年纪做出了规定,分第一格和第二格。经考试直接派遣到美国大学学习的为第一格学生,年龄需在20岁以下。[22]官方登记在册的前两批庚款生的年纪确实都不超过20岁,第三批学生中由于有上一次考试的备取者,故部分人的年纪为21岁。[23]如果徐仁锖生于1888年,他在1910年参加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时便已超龄,当是为了符合规定而填报为20岁。
第三批庚款生于1911年8月启程赴美,而汪荣祖文中称徐氏在1912年获得威斯康辛大学的学士学位,这就不免使人心生疑窦:即使聪明过人,一名只有相当于大学预科学历的中国学生是否能够用一年时间完成美国大学的全部学业?而汪文还称,徐氏在从威斯康辛毕业后因为成绩突出赴德留学,在两年内,也就是1914年取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显得更加神奇。
1917年,清华学校的留美学生通讯处编辑了一本中英对照的《游美同学录》(Who’s Who of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ts),收集了一些从清末至1917年毕业回国的自费和官费留美学生的个人信息,但其中并没有徐氏。[24]1925年出版的《清华一览》里收有“游美毕业回国学生一览表”,包含了历届庚款留美生的完整名单。在“第三批 六十三名 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三日放洋”中,有这样一条记录:[25]
此处的名单里已经没有徐仁锖这个名字,而只有徐光,可见当时徐仁锖已经改名为徐光。1937年4月印行的《清华同学录》也辑录了历年清华留美学生的名单,在“一九一一考选留美同学”中,徐氏的资料为:[26]
两处统计材料都包含了通信地址这样的私人信息,说明编者在成书前与当事人应有过联系。但徐氏的学位却一下子从学士变成了博士,且获得学位的时间也大有蹊跷。在《清华同学录》的名单中,其他1911届留美学生最早获得学士学位的是威斯康辛大学的陆懋德和密歇根大学的史译宣二人,均为1913年。绝大部分学生获得学位的时间在1914至1917年。即使是前两批庚款生,能在1912年拿到学士学位的也寥寥无几,1909年第一届和1910年第二届学生中分别各有两人。两年从美国大学毕业,对于当时的那些中国学生来说已经很难实现,何况是一年呢?
而与徐仁锖同年考取庚款留美,并一同到威斯康辛就读的梅光迪在留学期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徐氏的为人,也可作为推翻其1912年本科毕业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梅光迪1908年从安徽高等学堂毕业后,到上海进入复旦公学继续学业。次年,他经安徽同乡介绍结识了也在上海求学的胡适,成为好友。1910年,二人一同北上参加了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27]胡适顺利考取,梅光迪则和徐仁锖一样成为备取生。胡适赴美后,梅光迪一直与其保持通信往来。此后梅氏经过在清华学堂的短暂学习,于1911年通过庚款考试。梅光迪没有选择胡适所在的大学,二人仍通过信件进行联系,对彼此的思想和生活动态都很了解。1912年4月30日,梅光迪满怀愤慨地致信胡适,讲述了在威斯康辛的两位室友徐氏和陆氏对他的欺凌:
徐在复旦毕业时,迪始进复旦为末班生,程度相差至七年之远,故徐向以前辈自居,而性尤傲僻。其视吾辈犹无知小儿耳,且非但视吾辈如此,其视天下人皆无知小儿耳。迪向未与之深交,彼此不相闻问,自至清华始稍稍与之周旋,以为其人虽不足交,然外貌酬应固无伤也。至此邦,渠本欲以复旦卒业文凭作为此邦B。A。文凭而直接进Graduate School,乃本校不许其请,置之Sophomore之班,渠恨极。适迪亦置此班,渠益恨,而忌迪之心遂甚。自此逢人辄骂迪。……迪始来此,适与其同舍,旦夕相见,渠视迪为眼中钉,刻刻不自安,日思设法中伤之。同住陆某亦老朽而怪僻者,陆又山东产,北方之强,一言不合,拔剑而起。陆之骂人忌人本领差堪敌徐,徐于是深接之,称为知己。徐陆二人读书本不多,然窃得明末人习气,又闻今世西人有言论自由之说,与夫所谓有强权无公理者,于是以骂人为真言论自由,以为个人交际亦须讲强权。而纵论当世人物,信口唾骂,亦吾国名士所乐许。陆徐两人受病之深全在于此故。[28]
对照庚款留美名单,经1910年考试录取到清华学堂,随后又在1911年留美的徐姓学生只有两位,一个是威斯康辛的徐仁锖,另一个是去了普渡大学的徐书,后者与梅光迪所指明显不符。1908年复旦毕业这一信息也进一步印证了梅氏笔下的那位室友就是徐仁锖。[29]而第三批庚款留美生中,在威斯康辛的山东籍陆姓同学,只有陆懋德符合条件。[30]
梅光迪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向胡适澄清当年2月与陆氏发生的一场冲突,并请胡适在留美中国学生中为其洗脱动手伤人的污名。据梅氏所述,威斯康辛的中国学生开会时,陆与梅发生争执。陆飞脚向梅踢去,梅起身闪避,陆收脚不及,摔倒时碰到椅子,撞破了头。在场众人中只有徐氏要求将陆送医治疗,并主动提出陪其前往。学生会会长等同学劝说梅当晚不要回宿舍,以免陆徐二人对其不利,梅当晚便到他处借宿。第二天,庚款留学生每月生活费的70元支票恰好寄到宿舍,陆便偷拆了梅的信件,到银行冒用梅的签名取出了钱,声称要从中扣除20元医药费,剩下的钱可以还给梅。梅和其他同学得知此举后非常气愤,商议后决定由梅写信给留学生监督黄氏(当时的驻美游学监督为黄鼎)报告事情经过,要求对陆做出处理,并称陆是“为人所愚(暗指徐)”,在场学生除徐外都签名表示支持。经过黄氏的调停,最后决定让梅赔偿陆10元,从此后月费中分五个月还清,陆将冒领的70元寄给黄监督,再由黄作为中间人寄还给梅。陆此前在学校中的表现很差,已有多门功课不及格,出了这件事之后,“数日后即往Ohio去矣”。[31]由此可见,《清华同学录》中称陆懋德1913年获得威斯康辛的学士学位并不准确。[32]更早的《游美同学录》中记载陆懋德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都是从俄亥俄大学取得,[33]当更为可靠。
陆转校后,梅也搬了家,原宿舍中只剩徐氏一人,但黄监督却将退款支票仍然寄到了那个地址。结果徐又重蹈了陆的覆辙,偷偷扣下支票,假冒梅的身份去银行把钱取走了。黄、梅沟通后察觉支票遗失,到银行查询,认出取款签名为徐之笔迹,打算去找徐对质。梅尽管生气,却也不想做得太绝,还在替对方考虑:“此事始终不能令银行知,以中人全体名誉攸关也。若令银行查办,则极易着手,徐不免受缧绁之辱也。”梅光迪写信给胡适时,此事尚未了结,梅相信黄氏会秉公处理,请胡“静候好消息”,并请胡适不要对外宣扬这桩窃案。[34]然而梅光迪致胡适的下一封信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并未收录,《胡适留学日记》中,1911年11月至1912年8月期间的“北田(Northfield)日记”又恰好遗失。梅光迪在这封信中留下的悬念,如今大概已无从揭晓。
梅光迪似乎没什么必要特意向胡适诬陷他的同学,在中国留学生的小圈子中,撒了谎也极易被拆穿,信中提及的留学监督和学生会长等人均可作为旁证。如果梅氏所言属实,徐氏的人品和学位都大有问题。徐仁锖1911年秋季到威斯康辛时是以“sophomore”(本科二年级学生)的身份开始学业,绝不可能1912年便拿到学士学位。
晚近出版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里,收有前三届庚款留美生的个人信息汇总。在1911年第三批派出学生中,徐氏的情况记载如下:[35]
据该书编者标注,这份“清华学校留学回国学生”名单是“案存教育部档案室”。因此这一资料当有很高可信度,也就是说,徐仁锖1914年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就回国了。1911年入本科二年级,1914年毕业,时间上也显得合理。但这样一来,徐氏的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又是何时获得的呢?姑且认为民国教育部掌握的资料不够全面,徐氏1914年结束本科学业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冒着欧战的炮火奔赴德国留学,且如《清华同学录》所载,1916年从海德堡博士毕业,如此则又与他后面的任教经历发生了冲突。
汪荣祖文中称,“徐先生自民国四年(1915年)起,就在北京大学执教,授希腊罗马文学史与德文,傅斯年恰为其德文班上学生。”[36]说徐氏1915年任教于北大是准确的。1918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列有北大现任和离任职教员的名单,前任教员里便有徐仁锖,在职时间记载为“民国四年九月”至“民国七年一月”。[37]北大却并不是徐氏归国任教的起点。根据徐悲鸿遗孀廖静文所著传记,1915年,徐悲鸿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到上海谋生,“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教授的同乡徐子明先生”热情地向复旦校长李登辉推荐,为徐悲鸿求职。徐悲鸿便于1915年夏天来到上海,但这次举荐无果而终。“不久,徐子明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离开了上海。”[38]此番回忆恰好与教育部档案材料中徐氏1914年回国这一时间点相吻合,进一步说明他在结束留美学习后便开始了任教生涯,没有再去德国读博士的时间。
1960年代,袁同礼在美国先后整理出版了截至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博士论文目录。其中的留欧博 士 名 录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1907-1962[39]一书中,并没有收录以Die Eigentümlichkeiten des Mittelalters为题的博士论文,也没有作者是徐仁锖、徐佩铣、徐光、徐子明或相似中文名译音的任何论文。考虑到袁同礼所编目录存在遗漏的可能,笔者委托友人查阅了海德堡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的博士论文目录(Philosophische Fakult?t)和相关年份的学生注册名单(Personalverzeichnis 1911/12—1916/17),均未发现可能与徐氏有关的记录。[40]综合以上各方资料可以判定,徐子明的所谓海德堡博士头衔,乃是子虚乌有。
在《学林漫步》中,《怀念宜兴徐子明先生》的下一篇文章就是《胡适的博士问题》。汪荣祖称胡适在博士学位未到手之时便自称博士,有失读书人的“真诚”,有“‘欺世盗名’十年之‘罪’”,甚至还举出袁同礼编的“博士榜”为证,[41]可见他早已看到袁氏所编目录。胡适1917年归国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博士论文答辩,但迟至1927年才正式获颁博士学位,个中缘由早已是学界聚讼纷纭的话题。[42]胡适错在以博士候选人的身份提前享用了博士的名号,但至少其留学经历和博士论文本身都还是货真价实的。而汪荣祖一面严词指责胡适,一面却对徐子明彻头彻尾的假博士大加标榜,评判尺度反差之巨殊为罕见。
1975年,徐子明去世后,其子徐弃疾和其女徐令仪将徐氏在台湾的著述辑成《宜兴徐子明先生遗稿》出版。书中收录了徐子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中英文函札多封,其中“复郁德基书”注中附有郁德基1972年致徐氏之信的摘录:“光绪年间先生考取南洋公学之时,基亦在南洋公学肄业,惟仅同学半年,彼此似不相识。至清末宣统三年春间,其时清华大学刚在北平开办,先生考取留学生,当时规定留学生均需在清华大学受美国教授指导半年,然后出国。其时基为清华教习,教普通学生……”[43]而英文信函的最后一封是徐氏于1972年逝世前不久写给英国心灵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的信,阐述了对心灵学的理解和向往,并索取相关书籍。在附言中,徐氏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自称“a graduate from Heidelberg in 1911”(1911年海德堡大学毕业),[44]将获得博士的时间径直提前到1911年。
老友的回忆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徐氏考取出国留学的时间是宣统三年(1911),徐氏本人竟敢自称在这一年从海德堡大学毕业,直到去世仍以博士头衔自居,未免令人齿冷。诡异的是,尽管在文集中徐氏的谎言分明已露出了马脚,这个弥天大谎却似乎从未受到怀疑。台湾“国史馆”出版的《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中收有一篇未署作者的《徐子明先生传略》,文中将其留学过程记述为:“既冠毕业,北上应清华大学甄选赴美留学之试,榜出,名列第一。先生遂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秋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治欧洲近代史及德国文学,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夏毕业,即赴欧,于是年秋入德国海特尔堡大学,治欧洲中古史,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得哲学博士学位。”[45]这段学历居然毫无正确之处,并且还被多次征引,至今仍在误导着学界。[46]
徐氏与北大:从“探艳”到“息邪”
1916年4月,北大刊印了一册《国立北京大学分科规程》,里面载有各科教员的姓名和简介,其中徐仁锖的个人信息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美国威斯康新文哲科学士、江苏宜兴”。[47]这可以说明徐氏确实只有留美经历,否则不会不把最重要的博士学位写到履历中,也说明他被北大聘用时尚有自知之明,未敢造假。徐氏到北大时刚归国不久,周围曾与其一同留学的知情人很多,若要冒称德国史学博士风险极高。根据1917年5月北大上报教育部的《北京大学四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徐仁锖于1915至1916学年度被北大文科聘用,讲授的是西国文学史、英文学和文学概论,[48]都是英国文学门的必修课。[49]该年度的英文门课程中除英国文学史外,还有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和近世欧洲文学史,[50]都可以归为“西国文学史”,具体哪门是徐氏所教,《国立北京大学分科规程》中则没有记载。
徐氏在北大所教均为文学类课程,并非史学,也没有必要冒充德国史学博士。然而汪荣祖或许是为了配合徐氏的史学博士身份,竟还替其杜撰出在北大教历史的经历。在《史学九章》一书里,汪氏写到兰克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时特意抬出徐氏,称“最早通读兰克主要著作的国人,很可能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徐光(子明)先生。他于民国四年(1915)在北大讲授德国语文与历史,傅斯年曾是他班上的学生。”[51]不知汪荣祖在写这段话时是否已经忘记了,就在其早期的一篇论文《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中,为说明五四之前大学中的历史教学缺乏专业性与独立性,作者举徐子明为例,将徐氏称为民国初期“最有近代史学训练之中国史学家”,但在北大讲授的课程主要为外语而非历史,并将原因解释成当时“语文科目远较历史科目‘热门’”。[52]可见汪氏笔下的徐子明不仅不符合真实情况,而且仿佛可以根据行文的需要任意打扮。
徐仁锖在北大任教期间和离职后都掀起过轩然大波,可惜并不光彩,汪荣祖也全然回避了这些经历。许德珩于1915年秋考入北大英国文学门,正好成为徐氏在北大的第一批学生。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写到蔡元培出掌北大后的改革,称蔡氏到校后辞退了一些“学术水平低,教学态度差”的中国教员,“其中有一个英文教员,此人不学无术,而且是个流氓分子,常常往东安市场追逐女性,人称为‘探艳团团长’。我虽然转到国文门,可是对他深恶痛绝,遂与杨振声、杨立诚等七同学,提议驱逐他离开北大。在蔡先生的支持下,终于把这个英文教员赶出了北大。”[53]此处作者隐去了这个英文教员的姓名,但这本主要由许德珩口述,他人记录的回忆录的部分内容在成书前已单独发表过,在《我的回忆——从北京大学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这篇文章里,许德珩将此人称为“英文教员徐××”,其他文字都相同。[54]而在更早写下的《纪念“五四”话北大——我与北大》中,许德珩曾直言不讳地写出了他的名字:“教员方面原有拖着一条大辫子、最顽固的复辟分子辜鸿铭,年轻的英文教员、流氓分子‘探艳团’团长徐佩铣,老顽固、文科学长夏锡祺等人。蔡元培来校后,首先就把他们排除出去了。”[55]许氏口中的“流氓分子”、“探艳团团长”,正是徐仁锖。
1918年1月,也就是徐仁锖离开北大之际,校长蔡元培在北大师生中发起了进德会,约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三戒为会员的基本准则。蔡元培亲自撰写了《北大进德会旨趣书》,将进德会的效用称为“可以绳己、谢人、止谤”。止谤便是针对此前校中的不正之风:“吾北京大学之被谤也久矣。两院一堂也,探艳团也,某某等公寓之赌窟也,捧坤角也,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也,皆指一种之团体而言之。其他攻讦个人者,更不可以缕指计。果其无之,则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然请本校同人一一自问,种种之谤,即有言之已甚者,其皆无因而至耶?”[56]从这番话来看,当时确有“探艳团”一说,而这位新校长在道德方面悬格很高,不能坐视此种风气在校中蔓延。
但蔡元培于1917年1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徐仁锖1918年1月被解聘,中间尚有一年间隔,并非如许德珩所说马上将其排除,还是给了机会以观后效。辜鸿铭则直到1919至1920学年度仍在英文系任教。[57]蔡氏后来表示,北大教员的去留与其政治、文化倾向或私德无关,一切以是否能胜任教学为标准。“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58]这便说明,徐仁锖离开北大,除“探艳”外,应该还有教学方面的原因。许德珩将徐氏归入“学术水平低,教学态度差”之列,那么徐氏在教学上的表现究竟如何?与许氏同于1915年入读北大英文门的李季在其回忆录中恰好有详细记叙:
C先生系江苏人,为英国留学生,年龄约三十左右,中英文俱有可观。不过酷好冶游,性尤骄惰暴戾。他似乎以妓院为家,至少有一大部分的时间是消磨于此,因此不独对于教课无暇预备,即上堂也来得极迟,每点钟照例只上三十分。
“我的英文可以教你们二十年,中文可以教你们十年。”他常是这样夸口夸嘴地对我们说。
有某同学一日问他一个英文生字,说是字典中找不着。他马上很得意地答道:“啊,你可以从我的脑子里面找出来。”
但有时遇着学生质问字义或句子,他解答不出,便眼睛一横,装着发气的样子说道:“这也不知道,要来问我么?”学生本来畏之如虎,再也不敢做声,他便这样鬼混过去了。
我们一班有三门主要功课都由他一人包办,学年试验的结果,三十二人中竟有半数不及格,须留原级听讲……这并不是由于同学的英文程度一定怎样坏,而是他的试题过于刁钻古怪,给分过于刻薄。[59]
李季入学时,在英文门任课的教师只有寥寥几人。[60]虽然徐氏并非英国留学生,但结合教三门主课、沉湎于妓院、籍贯这些关键特征可以判断,李季笔下的“C先生”无疑就是徐仁锖。[61]从李季的叙述来看,身为教师,徐氏绝不仅仅是私德不检的问题,对本职工作如此懈怠草率,足以被任何学校开除。据李季称,那一班的32名学生,到第二年时只有13人正常升班,其余都被迫留级,或转入文科中其他专业。[62]《国立北京大学分科规程》收有1916年4月时的学生名单,其中李季所在的英国文学门一年级共有29人。[63]而这一级最后在1918年只有12人得以毕业。[64]班上甚至还有一位志在学好英文的同学在徐氏手下连续不及格后只得留级转到哲学门,始终无法释怀,碍于校规又不能再转回英文门就读,以致最后精神失常,辍学返乡,三年后便去世了。在李季看来,这位同学英文有中平程度,读书极用功,无任何不良嗜好,是个可造之材,本不该落到这样的不幸结局。他悲愤地评论道:“C阎王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不知道也自觉惭愧否?!”[65]
许德珩在回忆录中还写到他在1916年3月回家料理父亲和妻子丧事,休学一年,“1916年秋回北京复学,转到国文门重读一年级”。[66]但许德珩转到国文门是否出于他的本意呢?许氏称自己转专业后与杨振声、杨立诚等同学一起向蔡元培请求驱逐徐氏,显得颇可玩味。杨振声、杨立诚和许德珩一样,都是1915年考入英文门的学生,[67]而后分别留级转到国文门和哲学门,于1919年毕业。[68]联系李季所说半数同学考试不及格,必须留级的情况,他们改换专业很可能有为成绩所迫的因素,这可能也是他们对徐氏分外憎恶的原因之一。至于徐氏被学生驱逐和离开北大的经过,李季的回忆则完全是另一种面貌。
李季本人在顺利升入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之列,仍在C先生所教的班上。这位先生的表现却日益恶劣:“第一学年每点钟还上课三十分,到第二学年,常常连这三十分都不来上,又不请假。”忍无可忍之下,班上同学联名向校长“F先生”(当时北大校长由工科学长胡仁源署理)申诉C的劣迹,要求将其驱逐,换成本来教三年级的“辫子先生”(指辜鸿铭)任课。但F校长“向来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宗旨”,“绝不肯辞退一个教员,或开除一个学生”,只是极力安抚敷衍。[69]C先生对于学生的指责不肯示弱,学生也对“C流氓这样恋栈”深表愤慨,坚持罢课。双方争执不下之际,F校长去职,校长换成了“Z先生”(蔡元培)。Z校长上任后,将李季这一班的教师改为“辫子先生”,罢课风潮遂告平息。[70]“至于C先生并没有因此失掉位置,只是改教国文学门的英文。他受了我们罢课的教训,此时每点钟足足要上四十五或五十分,有时打过下堂钟,还向学生说:‘请你们等一下,我将这一段讲完,’于是又另加上三五分钟。可是历时不久,他因某事与某先生大起冲突,竟将饭碗打破,在以后两三年中只见他携着手杖在中央公园闲游,再也找不到正当职业了。”[71]
能在出勤方面有所改进,大约是徐氏被姑且留用的主要因素。最终导致徐仁锖去职的“某先生”是谁,李季并未点明,至少应是校中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徐子明先生传略》中称:“会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发行《新青年》,在校中提倡共产邪说,讥讪孔圣,先生见而大愤,切齿而言曰:‘是有甚于洪水猛兽,不揭其隐,数十年之后,吾民尚有噍类乎?’乃面斥独秀,而后引退,撰《息邪》以及《辟谬》两书,由北京骡马市洪文印刷局出版,冀稍遏横流。”[72]《传略》充满失实之处,这段含有生动言论的记叙也经不起深究。到徐氏离开北大的1917、1918年之交,陈独秀尚不曾“提倡共产邪说”,《新青年》的文章集中在批判孔教与倡导文学革命上,并未宣扬共产主义。[73]故而这一说法可信度不高,让徐氏失去饭碗的,未必就是陈独秀。
1917年1月,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发展新文学的八点主张,即所谓“八不主义”。《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旋即撰《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74]文学革命由此成为知识界聚焦的话题。此时陈独秀已在蔡元培的邀请下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也力邀胡适归国后加入北大。[75]1917年9月,胡适就任北大教席,同时在中国哲学门和英国文学门授课。而徐氏则恰于此时不再担任英国文学门的专业课,被安排去教文本科的公共英文课。当时国文、哲学和史学门的英文课将学生按学力分为甲至戊五个班,徐氏所教为戊班,[76]即学生成绩最差的班级。从这份课程表中也可看出,公共德文课的教师是顾兆熊和朱家华(骅),并非徐仁锖。汪荣祖屡次称傅斯年为徐氏所教德文班上学生,不知有何根据。[77]1917年12月,北大各科中的英文教员集体开会,选举胡适为英文部教授会主席。会上还推举十余名教员组成几个委员会,分别负责审查本科和预科现行教科书是否存在问题等事项。[78]作为英文部教授会的成员,徐氏均不在这些委员会之列,可见他此时在北大已彻底失势。到这一学期末,也就是1918年1月,徐氏就被解聘了。昔日留学考试竞争对手如今声名鹊起,自己反而狼狈地失去饭碗,“自命为学贯天人”(李季语),[79]且“妒性天成,人有一能,渠见之即不自安”(梅光迪语)[80]的徐仁锖是否会泰然处之呢?[81]
《徐子明先生传略》称徐氏在离开北大后撰有《息邪》和《辟谬》,则确有其事。1919年8月,北京《公言报》上分八期连载了一篇署为“思孟来稿,文责作者自负”的长篇文章《息邪》,又题《北京大学铸鼎录》,包括蔡元培传、沈尹默传、陈独秀传、胡适传、钱玄同传、徐宝璜刘复合传六部分。[82]在末尾的简短评论中,作者对时局深表不满,认为除执政者不重民生、与民争利外,蔡元培等北大新派人物的妖言惑众是当下乱局的重要成因。在作者看来,“蔡氏之说必至本末倒置,国亡家丧”,故而建议“令军警遏抑邪说,防患未然”。[83]
虽然作者在开篇和结尾打起为民为国的大旗,正文中却并没有对“邪说”作深入剖析,而仅用一些揭短性质的轶闻琐事试图丑化几位传主。写钱玄同、徐宝璜和刘复(半农)的篇幅都较短,内容泛泛,有陪绑凑数之嫌。沈尹默和陈独秀的两篇相对长一些,也更清晰地体现了作者的仇视,渲染沈尹默善玩弄权术,陈独秀私生活淫乱。篇幅最长的是蔡元培和胡适两部分,拼凑各种不相干的细节塑造他们的负面形象,可见此二人是作者意欲打击的主要目标。作者将蔡元培描绘成一个出身低贱,口不能言,无才无学的庸懦之辈,其中充满了毫无根据的毁谤。如称蔡元培“父以卖浆为业数见侮”,蔡氏进士及第后,其父喜称“吾乃今日始见天日矣”。[84]据蔡氏自述,他出生于小康之家,十一岁丧父,父亲在世时为钱庄经理。[85]作者又称蔡元培辞退十余名北大教员的原因是受到陈独秀和沈尹默的鼓动,以图空出名额,“均分其俸”,从而安插亲友任职。英国人Cartwright(克德来)因合约未满向英使馆投诉,使馆通过外交部抗议,于是“蔡氏大惧,以六千金赠英人”。[86]但蔡元培当时已作出澄清,北大解聘的都是不称职或因学科裁撤无课可开的教员,在克氏一事上并无违反合同之处,对克氏要求的巨额赔偿也拒绝接受。[87]
最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对胡适的态度。虽然也是极力歪曲抹黑,如称胡适密谋驱逐北大法科学长王建祖和代理校长温宗禹,[88]治墨子全是抄袭孙诒让《墨子间诂》,[89]其笔下“白话诗之警句脍炙人口者”为“跑出西直门,跳上东洋车”[90]云云,但也罕见地对胡适的学识和影响力给予了一定认可,称“沈陈刘钱之徒不识西字,妄袭谬说,斗筲之才不足比数,足以论新文学之鼻祖,必推胡适。”并将胡适视为极具政治野心的人物:“自充大学教授即以结党为职志,其杂述东欧过激共产之说而以新文学体(白话)行之,殆欲使下流社会晓然于其说,振臂一呼,云从响应,而己为之渠魁。”[91]但胡适对所谓共产之说并不认同,就在《息邪》发表前的1919年7月,他在《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明确反对高谈“外来进口的‘主义’”,[92]引发了一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于陈独秀,《息邪》反而没有预见到其将“以结党为职志”,只是称其因“肄言共产主义”被政府要求北大予以解聘,陈氏怀恨在心,故意撰写散发共产传单而被捕。[93]足见作者对胡适分外看重,俨然将其视为最危险的敌手。
同月出版的第33号《每周评论》“随感录”一栏中,刊登了一段《辟谬与息邪》:
北京大学辞退的教员宜兴徐某前几个月做了一本“辟谬”,痛骂蔡孑民。近来又做了一本“息邪”,丑诋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沈尹默等。这书里说蔡氏“居德五年竟识字百余,逋法三载,又识字十余”。又嘲笑陈沈诸人不通外国文,又说胡适“英文颇近清通,然识字不多”。我们初看了,以为这位徐先生一定是精通西文的了。不料翻开第一页,就见他把Marx拼成Marks。这种“谬”也是该“辟”的了。[94]
《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前期由陈独秀主编,陈氏被捕后由胡适接编(自第26号起)。《辟谬与息邪》作者署名天风,是胡适在这个刊物上的常用笔名。文中虽未直接写出思孟的姓名,在圈内人眼中也相当于揭穿了他的真面目。当时被北大辞退的宜兴籍徐姓教员,除徐仁锖外没有第二人。胡适不但指出《息邪》是出自徐氏手笔,连此前的《辟谬》也一并揭露出来。滑稽的是,《息邪》中还煞有介事地提到了《辟谬》,称林纾指责蔡元培“提倡邪说诱惑少年子弟之罪”后,蔡氏“用诡辩自雪”,“有号秋霜者刊辟谬一书痛驳蔡氏之书,蔡氏亦不能答也。”[95]
1919年2月,林纾应其旧日学生张厚载的约稿,在《新申报》上开辟“蠡叟丛谈”专栏,连载一系列文言笔记体小说。2月17日发表的《荆生》杜撰了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三人放言高论,声称要“去孔子、灭伦常”、“废文字,以白话行之”,结果遭到“伟丈夫”荆生痛殴的故事。[96]这三个反面人物从名字到主张都明显是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97]随后《每周评论》转载了《荆生》,在记者按语中指出这篇小说代表着用武力压制新思潮的动向,荆生则是林纾的自诩。[98]荆生也被认为是指安福俱乐部的首脑徐树铮,[99]林纾当时在徐树铮创办的正志中学担任国文总教,与其多有过从。徐树铮与柯绍忞、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桐城派古文学家交好,被认为具有“慕重师儒之情怀”,同时亦有“武健之本色”,[100]很符合荆生的形象。徐树铮还曾在正志中学演讲时“痛骂讲新学者为丧心病狂”,[101]更使人将其与荆生联系在一起。
无论荆生原本所指为谁,这篇小说都将守旧派对新思潮的仇视和欲惩之而后快的心态表露无遗。几乎与林纾发难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利于北大新文化派的传闻。2月26日,正在北大法科就读的张厚载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一篇“北京特约通信”,称因为北大文科学长和教员“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大总统徐世昌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查办,傅令陈独秀辞职,陈“不安于位,即将引退”。文中还称陶履恭、胡适、刘半农等教授也将一起辞职,而同在北大文科任教的刘师培即将组织《国故》杂志与《新青年》、《新潮》对抗。[102]3月9日,张厚载又发表了一篇报道,称蔡元培对陈独秀辞职一说并未否认。[103]陈独秀等人将要被迫离开北大一事经披露后,幕后黑手受到了舆论的齐声谴责,被视为“受者之耻辱,毋宁施者之耻辱”。[104]免职之说随后被澄清,谣言的来源却出现了多个版本。[105]一时间,旧派文人官僚与新思潮间的对峙闹得满城风雨。甚至有参议员张元奇要求教育部查禁《新青年》和《新潮》,称此等杂志“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扬言要在新国会中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106]
将这场新旧之争推向高潮的便是《息邪》中提及的林纾与蔡元培的辩论。《公言报》由徐树铮出资创办,相当于安福俱乐部的机关报。周作人称“它的论调是一向对于北大没有好意”。[107]陈独秀也曾表示:“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作对,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108]3月18日,《公言报》上刊出一篇报道,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北大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国故月刊》与《新青年》的对抗等事,并发表了林纾写给蔡元培的长信。[109]在信中林纾正面阐述了自己对儒家伦理和古文与白话地位的意见,忧心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危局,劝诫蔡元培要“以守常为是”。蔡元培对林纾的信和《公言报》的报道立即撰长文回应,澄清从未打算“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以思想自由的基本立场为新文化派辩解。[110]《公言报》并未刊载蔡元培的答复,只评论说蔡氏不敢承认北大“自坏国家数千年文明”的“丧心病狂之举动”,同时刊登了《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111]在这封信中,林纾一面承认“传闻失实,不无过听”,同时也表示所求为“存孔子之道统也,伦常之关系也,古文之不宜屏弃也”,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这期间,林纾又在“蠡叟丛谈”中发表了一篇攻击北大的小说《妖梦》,内容较《荆生》更为露骨,[112]反而激化了矛盾。
林蔡之争引发了广泛的讨论,[113]甚至使得总统徐世昌出面,“对于最近新旧思潮之冲突为调和之规戒”。[114]不过舆论焦点旋即被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占据,5月4日,由于山东问题爆发的游行和冲突让这场文化交锋暂告一段落。在此次风潮中,蔡元培被官方认为有鼓动庇护学生之嫌,一度准备将其撤职,[115]甚至传出过要杀蔡元培,捣毁北大的消息。[116]被捕学生获释回校后,5月9日,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悄然离京南下,并委托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校务。[117]被认为袒护蔡氏,对北大“太执宽大”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几度提交辞呈,于5月11日离职出走。[118]北大及京中教育团体多次派代表劝蔡元培回校,并向教育部上书,呼吁挽留蔡氏。5月14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驳回蔡氏的辞呈,随后国务院和教育部亦致电慰留。[119]但蔡氏在回电中称病谢绝回任,[120]经过多次沟通,蔡氏仍拒绝北返。[121]6月3日,大批学生因上街宣传而被捕,风潮愈演愈烈。代行教育总长职责的袁希涛因处理不力提出辞职,被内阁照准,政府同时还决定批准蔡元培的辞呈,委派胡仁源为新北大校长。[122]6月6日,这一任命公布,旋即遭到北大师生的抵制。6月7日,北大教职员二百余人集会,决议不接受政府派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上书总统请其收回成命,并劝胡仁源万勿来校。[123]后胡仁源被改派到教育部任职。[124]通过多方协调,几经反复后,蔡元培终于在7月9日致电教育部和北京学界,表示愿意“暂任维持,共图补救”,[125]后又请蒋梦麟暂时代理校务。[126]
自蔡元培出走起,《公言报》对蔡氏的行止密切关注,报道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倾向性。胡仁源署理北大的任命公布后,《公言报》特意刊载某官员的贺电,表明对胡氏的支持。[127]针对北大师生吁请蔡元培返校,拒绝胡仁源的行动,该报则刊出号称北大本预科1358人联名发表的公开信,声称迎蔡拒胡不代表大多数民意,只是“提倡新文学之胡某等”“假全体教员之名义,以遂彼辈之阴谋”。[128]而此信实为安福部出资收买30余名北大学生、毕业生和投考考生所炮制,以求为胡仁源出掌北大造势。[129]甚至还有报道称蔡元培已经“神经错乱,受病甚深”,“北上一层殆不敢必矣”。[130]面对蔡元培通电表示可以重回北大,《公言报》报道的重点则放在“回京尚无确期”上。[131]蔡氏派蒋梦麟代理后,该报对此未做报道,而是特意登出五人联署要求恢复北大工科的请愿书,[132]又发表声明撇清自己与迎蔡拒胡风波的关系。[133]
《公言报》极力营造出蔡元培不会北返,北大中人善于玩弄权术的舆论导向,攻击蔡氏一党的《息邪》则恰与此导向互相配合,并也将胡适指为“迎蔡拒胡幕后主力”。[134]《息邪》最后归结到“令军警遏抑邪说”,与林纾希望借“荆生”打倒新派的思路如出一辙。陈独秀数月前便已对这样的行为表示了不屑:“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但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原。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135]
笔者翻阅了当时多种报刊,没有发现刊登《辟谬》,也未发现他人对《辟谬》的评论。[136]可以说,在新旧思潮激荡,众说纷纭之时,这是一篇默默无闻的作品,远不足以与林纾的发难相提并论。很可能它根本没有进入过蔡元培的视野,并非“不能答也”。但《息邪》是在《公言报》上刊出,便立即遭到了反击。继《辟谬与息邪》后,北京《国民公报》的“寸铁”栏目从8月8日到8月19日连续发表了十余篇针对思孟的随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棘”和“椿”的批评:
有一个什么思孟做了一本什么息邪,尽他说,也只是革新派的人,从前没有本领罢了。没本领与邪,似乎相差还远,所以思孟虽然写出一个ma ks,[137]也只是没本领,算不得邪。虽然做些鬼祟的事,也只是小邪,算不得大邪。
造谣说谎诬陷中伤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这一类事实,古来很多,鬼祟著作却都消灭了。不肖子孙没有悟,还是层出不穷的做。不知他们做了以后,自己可也觉得无价值么。如果觉得,实在劣得可怜。如果不觉,又实在昏得可怕。(黄棘)[138]
孟夫子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所以做“大学铸鼎录”那位先生自号“思孟”,标明“息邪”,但既是息邪说,便应该将蔡胡诸先生的学说一一驳倒,才算本领,何必替人立传呢。无论他说的是真是假,即使是真,也是攻击私人(personal attack),也是顾而言他(begging the question),也是文不对题,蔡胡诸先生的学说仍然站得住。敬告那位先生,是若想做孟夫子,还请他另做一篇对题的文章呢。(椿)[139]
“黄棘”为鲁迅的另一个笔名,该文也被收入了《鲁迅全集》。[140]“椿”并非该报常见笔名,其真实身份难以确认。从姓名相似度和立场来看,有可能是北大理科教授张大椿。蔡元培出走后,他曾由北大评议会推举为协助温宗禹代行校务的委员会成员。[141]另两位北大中人钱玄同和孙伏园则分别以“异”和“伏”之名,[142]就应该如何回应思孟的攻击进行了一番讨论。孙伏园首先提出,对这样的诋毁,北大方面不该以“不屑与辩”的“绅士态度”对待。[143]钱玄同认为,“蔡等诸君该做的事很多,要是耗去宝贵光阴,去和这班人争论,未免太可惜了。[144]孙伏园又表示,“世间上有个‘思孟’,未始不是他们感化力薄弱的缘故”,所以他们应努力促使“思孟”们幡然悔悟,让这种人再不会出现。[145]钱玄同则称,蔡先生等人两年来都是致力于此,但思孟其人“陷溺已深,恐怕感化甚难。我们局外人,除了口诛笔伐,有什么法子想呢。”同时钱也暗示,当下缺乏独立的司法,如果诉“思孟”于“思孟”,则实属无谓。[146]
二人的讨论言尽于此。对新文化阵营而言,《息邪》只是一本造谣攻击的下流作品,冷嘲热讽足矣,尚不具有作为学理讨论对手的资格。《息邪》抹黑的重点对象蔡元培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在1940年撰写的《自写年谱》中,蔡元培提及“迎蔡拒胡”风波时称:“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他们一方面运动少数北大学生,欢迎胡君;一方又发表所谓燃犀录,捏造故事,丑诋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诸君。”[147]《蔡元培全集》该卷的编者高平叔在注释中称《燃犀录》即指《息邪》,[148]这一判断当属可靠。前理科学长夏元瑮(浮筠)当时已出国留学,[149]与“迎蔡拒胡”一事无涉,《息邪》也未将其列为攻击对象。但“燃犀”与“铸鼎”是诗文中经常并用的两个典故,很有可能蔡元培晚年回忆时出现偏差,记混了书名。[150]如果《息邪》即是蔡氏心目中的“捏造故事”和“丑诋”,也便说明了为何蔡元培对《息邪》不予理睬。他对林纾的回复,也是针对其严肃表达文化观的信,并不是《荆生》、《妖梦》那种诋毁泄愤之作。
徐氏被北大解聘一年有余,才推出这本“鬼祟著作”,时机恰好选在蔡元培离开北大,反蔡势力紧密活动之时。从《息邪》中述及迎蔡拒胡风波的措辞来看,此文写就时蔡氏是否会重掌北大尚未明朗,而在《公言报》刊出时,蔡元培返回北大已成定局。对钱玄同、鲁迅等人的讥讽,“思孟”并未现身反驳,也没有“另做一篇对题的文章”,从此销声匿迹。但徐氏本人却显然并未释怀。四十年后,蔡元培与陈独秀早已作古,徐氏也已远渡台湾,却仍对胡适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仇恨,且发难的时机也是在对方已受到攻击,并有政治势力介入的背景下。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