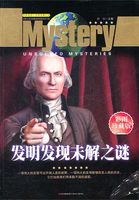以前,平西村和所有的平话村庄一样,流传着对山歌的习俗,这就是着名的平话山歌。平话山歌是平话人民间文艺的一种重要形式,唱的就是平话人的生活,喜笑怒骂,苦乐酸甜,信手拈来,也别有一番风味。平话山歌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按照山歌的内容可以分为情歌、劳动歌、儿歌、生活歌等。按照唱法可以分为独唱、对唱和多声部对唱(三人以上,一唱多和)等形式。曲调悠扬、平缓,是老百姓很自然地表达出的东西,原生态韵味很浓,很讲究押韵且用韵相当固定而有规律。情歌一般为男女对唱,例如:
“(女)天旱也么劝得天,么谷也么劝得田。(男)古话人言十五亮,因何十八到团圆?”
“(女)一路唱家一路去,一路淋花一路开……”“(男)舅是桂花香千里,妹是蜜糖千里来……”
“(女)手拿银刀切月饼,月饼团团四角裁……”“(男)开得四角成双对,个个成双心好开……”
“(男)妹屋坟山葬得好,催出妹来能耿乖,走过深潭鱼摆尾,行过庙堂鬼眼开……”
生活歌一般为独唱,唱起来调侃的味道很浓。
过村鸡,过到人村无敢啼;飞高又怕枪来打,飞低又怕网来围。
唱歌不知歌头尾,吃肉不知哪块肥;想是块块曹头肉,莫知块块母猪皮。
腊月八,日子好,许多姑娘变大嫂;面上哭,心里笑,屁股坐上大花轿。
高山岭顶有块田,中间大来两头尖;自己拔秧自己扦,无人送饭到田间。
对门坡上晒红鞋,妈妈养女外边人;大田大地无女份,白纸写字女无名。
今朝姑爷来拜冬,亚姨烧水杀鸡公;鸡公跳上兰花树,气得亚姨脸通红。
人人笑我无老婆,明年叫我阿爷娶一个;有钱娶个乖乖女,无钱要个豆皮婆。
平话山歌的调子没有多大的变化,不同的是歌词。既然是山歌,就有“出句”和“对句”之分,类似于一问一答歌词一般是即兴发挥,想到什么唱什么,看到什么唱什么,即所谓“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68多岁的梁增启先生从18岁就开始跟村里的老人学唱平话山歌,除平时在地里干活时唱上几句之外,空闲时经常一村一村地去对山歌,一些前人流传下来的山歌久传到已经无法考证年代了,现在他和村里的老歌手们经常看《南宁晚报》,根据上面报道的新鲜事来编山歌。他说:“对唱主要是即兴发挥,见招拆招,它比较考验一个歌手的应变能力,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还很难招架。就像电影《刘三姐》里一样,秀才对不出歌来,是很丢人的。但是一旦进入那种状态,就确实让人着迷。”
住在福建园的黄庆辉自从去年年初一在朝阳广场的一角听到平话山歌之后,就喜欢上它们。2006年7月3日,黄庆辉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收录这些平话山歌,如今,他不但收集了1500多首平话山歌,还把它们分类印刷成册、录制成磁带,每到周末,他基本都会到朝阳广场去,一边收集平话山歌一边学唱平话山歌。住在体育路的梁老伯已经74高龄了,他说,如果周末不到朝阳广场来对对平话山歌,他就会觉得这一天缺少了点什么。
今年70高龄的黄振兴说,他从18岁就开始跟村里的老人学唱平话山歌,除平时在地里干活时唱上几句之外,空闲时经常一村一村地去对山歌,一些前人流传下来的山歌久传到已经无法考证年代了,现在他和村里的老歌手们经常看《南宁晚报》,根据上面报道的新鲜事来编山歌。黄振兴说,今年民歌节兴宁歌台上他和哥哥、山歌队女歌手农凤英唱的《祖国山河花似锦》,就是根据《南宁晚报》上报道的改革开放新气象和风生水起北部湾来自编歌词的。
平话山歌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传承了20几代人。但是现在平话山歌的传承遭遇了困境。据调查,平西村会唱平话山歌的大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整个村子会唱的不超过10人。梁增启先生说:“那些年轻后生们都不会唱山歌,他们对这个不感冒,宁愿花钱去唱卡拉OK,去跳舞。而且现在的小孩子在学校都是学说普通话,平时嫌弃平话土,讲白话(南宁粤方言),更别说用平话唱歌了。前些日子报纸上说平话山歌恐成绝响,我看再过10来年,我们这帮老家伙不在了,真的就没人会唱了。”
按道理像平话山歌方言民歌,由于方言的障碍比较小,又有参与性,交流效果应该比表演唱的形式要好得多,但实践中的效果并非预期那样好。方言是交流和理解中最突出的障碍。平话山歌虽然是音乐,但它的叙述却以语言为主,方言却把本族群之外的人们挡在了门外。更糟糕的是,平话面对着普通话、粤语等主流语言的冲击,并显露出“劣势”,就连本族群的人也对平话语言的将来缺乏必要的“信心”。而且这种原始状态的民歌,主要用语言来叙述,其音乐比较粗糙,如果没有经过加工提炼,音乐的表现力比较差,在与“打扮”的五光十色,包装的光彩夺目的流行音乐较量中自然会“败下阵来”,很难俘获年轻人的心。
不过2007年平话山歌已被收入《第一批南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将继续申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对它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平话山歌的价值,把会唱平话山歌当作了一种“本领”,一门“技艺”。为了使这一特色文化后继有人,福建园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经常组织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能了解平话山歌的魅力。下一步,将对平话山歌爱好者进行培训,在春节、重阳节等节日组织村民进行唱山歌比赛,让平话山歌传承下去。现在,朝阳花园的“平话山歌对唱”更加火了。据说,平话山歌曾经登上过2007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绿城歌台,走进学校进行艺术表演。
四、身份界定与社会认同
随着平西经济文化的变迁,平西人眼中的“身份”、“他人”、“自我”等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要说明这个村庄里的人们身份界定与社会认同的变迁,须事先区分他们对人群划分的几个概念。
通常平西村人的眼里有严格界定的概念区分:在平西人的观念里,有本村人、外村人、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这些可看作是一种文化的界定,一种文化概念。这些概念不单单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还表示界定着利益分配的权利,是一种具有实质权利意义的经济概念。这是像平西这样的城中村特有的概念。
村民,指一切有平西村户籍的人口,一般为农业户口,受南宁市江南区平西村村委会管辖。还有相当一部分原来的平西村户口的人,由于去单位上班等等原因而转为非农户口,虽然仍然在平西村居住,但是受江南区福建园居民委员会管辖。“本村人”并不等于村民。村里人的“本村人”的概念里,除了村民,还包括户籍已迁出、在外地生活工作的原平西村居民,甚至包括户籍从未在平西村但祖籍平西村的人。这些户籍不在平西村的“本村人”,与村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即便没有在村子里,也在平西村扩大与外界的联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然,这些身份的划分同样具有现实经济意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90年代初期,平西村充分利用征地费收入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势力也迅速膨胀。因为只有具有农业户口的平西村民才有获得“三产分配”的权利,因此年终的分红无疑使这种身份的划分更加突显出来。1986年,全村人均收入2000元,是同期南宁市职工人均收入的2倍。尽管今天平西的产业收入今不如昔,但是相对于一些没有其他收益的居民来说,仍然是一种“福利”。这种就极大地刺激了农民保护既得产权和不愿变迁身份的内在冲动。
“外村人”指在平西村附近做生意的当地人,他们来自邻近的村庄或县城,与“本地人”基本属同一范畴。
“外地人”指离村庄距离较远的外省市人,他们包括租房子的学生、外地来的在平西居住的民工等等。“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别标志主要在语言和口音,本地人与本村人说同一种语言(平话),口音基本相同,而外地人与本地人语言和口音有较大不同。
以上这些人都与平西有关系,无论村民与非村民都有一种业缘(以租房者与出租者之间的关系为主)的关系。还有一种非业缘的外来人口,他们是村里各种工程的建筑队与来村里贩卖瓜果蔬菜和日用品的小商贩。1997年,村里开放了一处“自由贸易市场”,辟有摊位店铺,可以卖服装、农具、电器、化妆品、肉蛋、水果、蔬菜等等。平西村向他们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村民”与“居民”,“平西人”与“外村人”,“本地人”与“外地人”,这重身份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而恰恰相反的是,其最大特征就在于它的动态性和相对性。其对应关系有点类似于努尔人的“裂变支”,只有在“平西人”中才分为“村民”和“居民”;只有“本地人”才分为“平西人”与“外村人”,当他们面对更高一级身份类别时,下一级别的人又以相同的身份出现。费孝通先生面对中国这个“乡土社会”提出的“差序格局”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连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如果说差序格局是从私人关系角度出发而提出的,那么社会群体关系与身份认同同样遵循着“差序格局”。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平西在城市化大潮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它的文化内核仍然是“乡土社会”的文化,这和生活在城市空间中主要靠“业缘”和“私人关系”而建立人生网络,而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漠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业缘”在平西村中社会网络中越来越重要,例如房东与租户、商家与顾客,但是维系这个村落社会关系的仍然这种“差序格局”。
对这些概念进行清理和界定对于研究社会分层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概念表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社会分层产生的本身就已具有广泛深远的社会意义。
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它的核心是体制、土地和文化三要素。由农民到商民,由农村人到城市人,许多农民正经历着身份与角色的嬗变。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社会文化因子对农民的冲击尤为强烈,但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许多农民虽然“洗脚上田”,但没有“换脑进城”。这就是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对接的问题。可以这样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存在主体成分(城市文化)而具有兼容性、关联性和变异性的整合过程。在整合过程中,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既有传承又有断裂。
农民,本身是一种职业身份的介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由于中国城乡二元对立,以及城乡差距,“农民”一词被人为的附加了一层文化意义,许多时候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象征。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植根于农业社会中,加之旧的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文化心态:潜意识中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与外显意识中对“城市人”身份的追求,对农民身份的逃避,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悖论。
这种现象尤其在中青年的平西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由于平西没有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所以大部分人还保留着农业户口。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人强调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或亲戚在市里某比较好的单位上班或者在哪里有生意;许多人都会强调自己的户口已经从平西村迁出去了;有的人说平西已经很“发达”了,比起四周的农村“富裕”多了;有些人以“老南宁”自居,说自己原先的房子或土地在城市的中心附近;有的人则很不耐烦,认为平西几乎没有土地了,已经是“城市”了,已经没有他们以为“难为情”的乡土的落后的东西。而乡土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则自认为自己的知识是三教九流,不登大雅的东西。种种现象表明许多平西人对“农民”身份的逃避,以及对“城市人”身份的追求,但是他们仍然固守着农民的身份。
平西村居于邕江南岸,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万达商业广场”、“沃尔玛”、“百盛”等等繁华的商业区隔桥相望。从地理位置上说,平西村绝非城市的边缘,而是非常靠近“心脏”。虽然相距不远,但是江北的整洁繁华与江南平西的杂乱与凋敝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谁也不曾想到高楼华厦之间隐藏其中的竟然是如此一个村庄。上年纪的平西人还是喜欢去“和平市场”(一个档次比较低的批发零售市场)去买衣服,他们还是喜欢去石埠、细樟岭、大沙田去寻亲访友,还是喜欢讲他们的“平话”,喜欢喝他们的米酒,吃他们的土制“梅菜”,喜欢唱他们的“山歌”,看他们的“师公戏”……
尽管城市化带给平西人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上,他们还是“边缘”的。有人说“贫穷是一种心态”,那么边缘也是一种心态吧。平西人习惯于生活在这种以“边缘心态”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之中,这也许是一种文化心理的执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