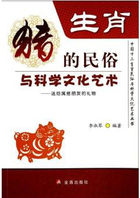从这首记叙新年十日活动的歌谣中可以看到,民国以后,传统的年俗在农村似乎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从祭祖祀神、禁扫地,到出门拜门、压岁钱、新嫁女归宁、迎财神,各项行事一一保留着传统原貌。更具特色的是,还出现了人生日“称人”,谷生日“祈丰年”,天生日“拜佛”,地生日“祭地神”等更为崇信旧俗的行为。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又让人们感受到旧传统中也被注入了新的观念,如“状元及第旧名词,要换共和称五族”,“作事须求脚脚踏实地”,以及旧时宗族制度下父亲家统治礼仪,与妇女“走三桥”以却病疾风俗的消失等等。这当然是因为民国以后民主共和思潮冲击,以及家庭结构变化经所导致的结果。所以旧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在农村,也能体现出移风易俗的演化过程。
2传统节日的革新
民国时期的农事节令、祭祀节日、纪念节日、庆贺节日、社交游乐节日,大多仍保持了原先的一套活动方式,但在这种节日习俗的传承中,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其中的变异,闻到一股新时代的气息。首先,原带有宗教迷信、盲目信仰的旧节令习俗逐渐衰落和被废除。迁安县“七月十五,为孟兰盆会。向年有僧道荐醮,投放河灯,以救溺鬼,近数年其例废除”。《迁安县志》,民国20年铅印本。完县“三月二十日,祀雹神(庙在北坎,旧日演剧四班,今渐衰落)。三月二十日,祀城隍(今改建设局,祀事久废)。四月二十八日,祀药王(庙在关,今久废不行)。五月十三日,祀关帝(旧于是日必演剧致祭,改革以后,迄未举行)。”《完县新志》,民国23年铅印本。新河县“十月朔日,祭祖先。是日,城隍辇出巡游(此举今废)”;“清明日,士女头戴柳枝、拜扫祖茔。城隍是日坐巡,会末人舁之游郊外(此举今废)。”《新河县志》,民国18年铅印本。年节时祭祀意识的淡化,是与民国初期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思潮分不开的,是“五四”时代精神渗入年节风俗的结果。
其次,一些原本以祈福纳祥为目的的祀祭节日,演化为娱乐性的体育竞技活动。如当时苏州河北有所谓黄大仙会者,每逢出会,人数众多,新奇百出,旗伞仪仗之外,有高跷、臂锣、舞叉、打对子等,时人称为武会,以别于城隍出巡之“文会”。而民国十五年(1930年)上海的观音会,更推出了高至丈二的大高跷及活观音等新奇节目,在市内迂回游行,行程费一整天,沿途所过,都设座架棚,万头聚观,人山人海,为自上海有庙会以来所未有之盛况。沈瑞麟口述,朱梦华整理:《老城隍庙史话》。这类赛会,虽起于宗教祭祀的傩戏,但在民国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已完全演化为市民性的喜庆竞技活动了。
再次,西洋式的游乐项目被大量纳吸入我国传统的年节习俗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群体性的游乐节俗。如原来流行于沪上殖民商人中的赛马游乐,民国时已成为上海民众的主要岁时娱乐活动,“每岁春秋二季有跑马之戏”,“每次必跑三日,跑毕,又有跳浜、跳花、萁架诸戏”。致“观者几如恒河沙数,而教坊中姐妹,更无不高架马车,逐认而行”。
更有赛船,“每春夏之交,在苏州河赛船为乐,其船用八人打浆,轻提如飞”。有跳跃之戏,“每年必举行二次”,“戏必以夜,燃地火灯千百盏”,“客袖短衣,互相搏斗”。有打弹子,“择巨室,设长木台长丈许,阔半之,覆以哆叱,而高其边。碾象牙为圆子,如鸭卵大者四枚,拔以木棒,互相撞击,以角输赢”。有溜冰,“择科日严寒之时,空一室,浇水于地”,“冰厚盈尺,西人乃穿铁齿高屣飞行其上”。黄本铨:《淞南梦影录》。在节日娱乐中,民国时期纸牌、麻将成为首选之俗。此外,还有演奏会、赛花会、俱乐部、西式饭店、酒店、烟馆、戏院、“西国青楼”、“梨园北里”、“粉黛南都”等冶游渊薮,在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盛行开来,已成了现代节日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后,民国以降,都市中节日的内涵还被灌输了浓浓的商业化的味道。随着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又在辛亥革命、政体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一些西方思潮的冲击影响下,投射在节日民俗中的活动性质也发生了相适的变化。某些节日与历史事件、人物发生的关联被斩断了,节日内在的古老的民俗信仰被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商业气息所冲淡,商人把节日作为发财获利的良好时机,而民众也乐意在节日中尽兴地消费。民国期间,上海的商人在新年初三过后,就开市营业,计算起银钱来:
新年一过市开场,收拾官厅作帐房;
领顶又将毡帽换,蓝青不换话青黄。
也有些商人择在新年吉日开张新居,并以优惠价招揽主顾:
每当新店挂笼旗,结彩悬灯竟炫奇;
招得门前人似蚁,为因初市价值宜。
以上节日习俗的四个方面的演变转型,必然导致人们节日心态的淡化,使人们对节日习俗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着名作家梁实秋曾在台湾报纸上发表题为《过年》的文章,回忆他家民元前后在北京所进行的生活方式的“维新运动”。在他父亲主持下,革除了许多时的旧过年仪式。他写道:
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过年不再作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分装四个圆笼,除日挑到家中,自己家里也购备一些新鲜菜蔬以为辅佐。一连若干天顿顿吃煮饽饽的怪事也不再在我家出现。我父亲说:“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逛厂甸我们是一定要去的,不是为了喝豆汁儿,吃煮豌豆,或是那大糖葫芦,是为了要到海王村和火神庙去买旧书。白云观我们也去过一次,一路上吃尘土,庙里面人挤人,哪里有神仙可会,我再也不作第二次想!梁实秋:《过年》,《大陆·台湾》月刊创刊号。
梁氏父子改革这过习俗的言行,说明民国期间传统节日的规范、整合作用正日趋变小。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人们在平日里也可品味年节时的美食佳肴;娱乐方式及场所的增多,人们也不必要等到年节时才放松自己;而节日名目的增多,包括外国节日引入,又使得节日给人的神圣和喜庆之感变得淡漠。所有这些,必然导致民国节日的内涵及外在表现形式剧烈的嬗变。
(第六节)民国汉族信仰风俗
一、封建迷信趋向式微
民国初年,掀起了一次破除神权迷信的运动。“自民国成立”,“激烈反常之辈,又主张废弃孔祀”,“破除迷信神权之说”,“一唱百和”,到处出现“毁坏佛像,打碎城隍,占据寺院庵观,驱逐僧道女尼”的现象。《三教大会议》,《大公报》1912年19日,“杂录”。湖南、安徽、浙江许多省份,都发生过毁庙反神的风潮。各类神职人员,惶惶不可终日。“僧人也,尼姑也,今皆在淘汰之列”。《僧尼道与学堂之关系》,《申报》1913年3月8日,“杂评三”。家庭中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也有遭取缔的。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则以“赛先生”(即科学)为武器,猛烈抨击有神论和有鬼论。陈独秀发表《有鬼论质疑》,指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法则说明,所谓“天合天罚天幸”、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鬼摄影、扶乩、风水、阴阳五行等都是万不可信的,森罗万象中并没有神灵为之主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如果“鬼神之说大张,国家之运告终”。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民国的宗教信仰风俗较之前代有所收敛。在天津,“自历代以来,佛教颇盛,寺院遍设各处,香烟若云,梵吹如雨,晨钟暮鼓。声闻全市。津人之信仰者,十凡八九。有志之士,痛夫国势之受凌夷,知非大兴教育,不足以开通民智,抵御外海,乃盛倡毁寺办学”。自民国“毁寺兴学之议起,佛寺十九被毁,所存者寥寥数处而已”。张焘:《津门杂记》。上海在近代以后,渐成为中国佛道两教的中心之一。据民国《上海县志》记载,到1927年为止,载入名称的79个寺庙中,只有近50个还在部分或全部仍作为宗教寺院继续使用。
二、农村俗神崇拜风头不减
民国时期,在各地城市及知识分子中,宗教信仰之风虽然有所弱化,但在广大农村及城镇的普通市民和手艺工匠中却仍信神重祀,对各种神只膜拜不已。此时,汉族社会的神灵崇拜主要表现在庙会和常年供奉神像等方面。庙会,往往和人们祭祀土神、各行业祭祀祖师以及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活动紧密结合。
在北方,有常年供奉神像的习俗。将近年关要祭祀可供神灵。此时除了供奉各种美味食品外,神桌前还要设香炉、蜡扦、花筒或香筒等。蜡扦上插大型“素蜡”,有些烫以金字,如“花开富贵,云现吉祥”。蜡扦下压黄线、千张、元宝等,称为“敬神钱粮”。花筒内插上金银佛花。神桌前地下摆蒲团,供礼拜用。家宅六神,如灶王、财神、土地等均须上供、烧香。如果家中没有常年供奉的神像,一般要在除夕日临时设天地桌,也要摆祭器、陈供养、挂钱粮、烧香秉烛。据说除夕夜至初一晨为诸神下界,考查人间善恶,所以届时人们都须恭谨行事。同时在院内正中要设香炉点上檀香和芸香,富室要烧藏香,以迎接诸神的光临。北京接神仪式一般由尊长主持,首先查好当时喜神、财神、福神以及阳贵、阴贵诸神的方位,然后主祭人才正式举着高香到院中向各个方位依次叩首,表示恭接诸神。礼毕举香回到堂上,插入香炉,再三叩首,全家按尊卑长幼次序三叩首。然后请香根,将神像和黄线、千张、元宝等一起请下,拿到院中钱粮盆里与松木枝、芝麻秸同时焚化,最后燃放鞭炮,表示接神仪式完毕。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130页。
民国时,所供奉的神甚多,大约有天神、灶神、财神、火神、宅神、栏神、门神、井王、土地等,而以天、灶、财三神为最上等。淮阳人所以敬奉这些神的理由是:天神调风雨,灶神主家政,财神司财源,火神司烽火;宅神保院庭,门神掌门禁,井王管水泉,土地司五谷。各司其职,各掌其事,对于人类的祸福和生活的安危有极大的关系。敬奉神时需用礼品,以香纸炮烛最为普通。不过较为级别较高的神,如天神、灶神、财神、火神、土地等,则除了普通礼品外,还供以食肉、果品之类,以示有别。
此外,农具有农具之神(如车、套、犁、耙、石磙等),工具有工具之神(如爷、锯、钻、凿等)。甚至老树、旧窑、古墓、巨坑、大桥等也各有其神。只是对于这些神的敬法与上不同,其礼仪比较简单。如农具神、工具神等,除了石器以外,均在旧历正月初一以后第一次使用时敬奉,仅仅供以香纸即可。至于老树、古墓、旧窑、巨坑、大桥等神,则不是向其问病,即是向其求药,而在平常时间并无任何敬奉的举动。《淮阳乡村风土记》,1934年铅印本。
民国时期的工商业户则有行业神崇拜。他们除了在公庙祭祀其行业先师外,各户也在家内进行祭祀。如豆腐及粉行祭祀淮南先师(即汉淮南王);铁匠祭祀太上老君;食品旅游业祭祀关帝;药材店祭祀孙思邈;木工、石工、砌工等祭祀公输子;笔业祭祀蒙恬;纸业祭祀蔡伦;酒业祭祀杜康;服装业祭祀轩辕;刻字印书业祭祀文昌帝;靴鞋业祭祀孙膑;剃头业祭祀罗祖(一称安清道友);印染业祭祀葛翁;伞业祭祀鲁班妹;妓业祭祀眉公(即白眉神);木牌业祭祀杨泗将军(与祀洞庭神同);茶业祭祀陆羽;道士祭祀张道陵等等。在祭祀行业先师的同时,都祭祀财神,而且互相封锁,因此有偷盗财神的习俗。《醴陵县志》,1948年铅印本。
三、祭祖祀宗城乡有别
民国时期由于家庭结构小型化,长辈地位式微,科学思想广泛传播,祖先崇拜这一家庭宗教功能也逐步衰落。早在1919年周作人就发表文章抨击祖先崇拜:“这宗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火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借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卖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祖先崇拜》,《每周评论》第10期,1919年2月。到了二三十年代,部分城市居民也认识到祖先崇拜的害处。据1927年对317人所作的调查,85.5%的人不赞成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祖先崇拜,72.6%的人认为中国社会正力求进步,祖先崇拜助长守旧崇古心理,应绝对废除。绝大多数人(81.5%)认为祖先应该纪念,但不应采取祭祀方式,可以用其他方式代替。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新月书店1929年版。据30年代初的一项对大学生进行的调查,188人中有82.5%不赞成祖宗祭祀,71.7%的人认为应废除祖先祭祀而代之以其他纪念方式。周叔:《家庭问题之调查》,《社会问题》第1卷第4期,1931年1月。可见,带有迷信及偶像崇拜色彩的祖先祭祀观念正在城市中逐渐被淘汰。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祭祖活动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如同以往一样,民国祭祖活动的主要形式依然是家祭。家祭,是一般民众以家里所设的祖宗神主牌位为对象的祭祀活动的统称。通常,它是在自家的祠堂内进行。依旧俗,民国时期的祭祖之礼,大行于春夏秋冬四时和祖先的忌日。新年伊始,超乎其他任何节俗,要事便是奉祀祖先。除夕,五鼓一筹,家家户户供祖先像于堂中,罗列果饼,更烛炷香,以祈一岁之安。有的人家悬挂五世同幅的祖宗像,称为“五代图”。正月元旦,鸡初鸣,全家即起,肃正衣冠,由家长率妻儿女依次拜之。缙绅之家,多有家庙,此礼则在庙中举行。有上海歌谣一首,是记叙奉祀祖先仪式的,其说从座位的排列和礼拜的顺序,都有一定的规矩:
十丈高墙有根基,各家人家祭祖先;
祖先代代宜孝敬,逢时逢节弗忘记。
四面门窗齐关闭,碗盏盅筷排整齐;
八仙桌,栲栳椅,古铜香炉锡蜡扦。
两行红烛煌煌亮,一柱清香一篷烟;
老辈祖先朝南坐,后辈祖先坐两边。
合家大小齐拜跪,男先女后论规矩;
焚烧锭帛完来送,子孙兴旺有铜钱。
除除夕之时祭祖外,每届元旦、清明、端午、中元、重阳、冬至及祖宗亡故之日,阖族之人也要分赴祠堂,面对供奉着的祖先牌位。献上时新果蔬、鱼肉菜肴。至于祠祭活动的具体仪式,各地有着不同的做法。在吴县,宗祠祭祀各有定倒。太湖西山的叶家祠堂,订有《祭宗祠规则》。其中规定,春祭、秋祭定于清明正日和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新岁定例点烛焚香,初一启门1日,以俟子孙瞻拜。祭礼要设祭筵1席,备杯筷12双、熟香半斤、半通1对、四两烛1对、茶食16色、荤肴10碗、小食16色、三牲1副、高果5柱、果盒1具、卷蒸5碗、小馒头5碗、总饭2碗、风糕5碗、大馒头2碗、茶汤各12盏、锡箔足6块、楮帛10提、千香3股、百鞭1串、双声20个,并请鼓手5名。祭时,主祭一人,长袍玄褂;襄祭两人,立于左右。在主祭的主持下,祠祭经过揖、跪、叩首、初献爵,并读过祭文后,就算完成了基本的仪式。祭过祖后,所有参祭人员要在祠堂里会餐。祭祀之物尽供活人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