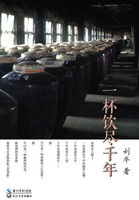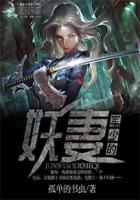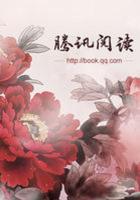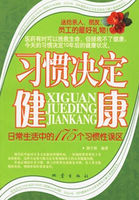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90年代的初步发展,跨入21世纪后,人类学已开始在中国崛起。
一
人类学在中国崛起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人类学的本土化。笔者在《人类学本土化论纲》一文中曾说:
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解决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队伍的本土化。回顾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向独立发展,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事中国人类学体系的建立。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人类学的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学的论证方法。”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地域限制,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其研究对象。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的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反对全盘照抄。纯粹的“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只有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在学习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同时,发挥个人研究专长,在研究中强调综合取向,跳出西方学术界固有的窠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进行研究。为此我提出:
1.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
举世皆知,中国历史的悠久是举世公认的,其相关历史文献丰富也是世所罕见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人类学一座古老而丰富的学术宝库。但是,几千年来,虽然出现过以《史记》作者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他开创了纪传体的研究方法,在《史记》中对当时中国的民族作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志描述,但其后,尤其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兴盛,他们运用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研究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使得近现代的学者往往只重史料的考证,却忽视对经过考证的材料的理论升华。今天我们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推进人类学本土化的今天,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重新整合,作出新的解读和分析,从中概括出新的论题,升华出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受到一次洗礼。
2.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一向是人类学家们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今天,由于人类学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调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人类学家只有深入基层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才能突破他过去所坚持的理论及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所构成的认识框架,让人类学理论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经受一次锤炼,从而使人类学的理论升到一个新高度,甚或从中升华出新的理论来。
3.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西方人类学界有许多流派,其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中国学者的特点是擅长历史文献的考据。而人类学的研究则既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从考据中跳出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又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要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中国的人类学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具有生命力。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正是沿着本土化的轨迹从恢复到发展到崛起。如果说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类学家杨成志的《云南民族》、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王同惠的《花篮瑶的社会组织》、陈序经的《昼民研究》、林耀华的《凉山夷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潘光旦的《开封犹太人》、杨垄的《灶神考》、杨庆垄的《中国家庭与社会》等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的话,那么,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是当代中国人类学家蔡华的《无父无夫的社会》、阎云祥的《礼物的流动》、罗红光的《不等价交换》、庄孔韶的《银翅》、王筑生的《中国景颇人》、景军的《神堂记忆》、郭于华的《在田野阅读生命》、张小军的《场域论》、周永明的《云南毒品》、张鹂的《北京浙江村》、刘欣的《阴影之下》、刘锡诚的《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等则为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铺就了一条进军之路。此其一。
其二,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类学家从本土中吸取营养,通过对本土的田野考察,从中概括、提炼、升华出人类学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打破了人类学家只研究异文化而不研究本土文化的传统模式,因此,国际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作《序》,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1]
为此,1980年国际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先生1980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奖;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人类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赫胥黎奖。
如果说费孝通是中国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国人类学争得国际荣誉的代表,那么,蔡华是当代为中国人类学争得国际荣誉的代表。
蔡华对居住在滇川边界的纳人(汉族称为摩梭人)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纳人的亲属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观察、描写和分析,从中概括、提炼、升华出“婚姻家庭都不能再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普通现象”的结论,从而重新定义了血缘关系、乱伦禁忌、婚姻与家庭四个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因此,当代国际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评论蔡华的《无父无夫的社会》时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是一部传世之作”。并在该书英文版封二上写道:“蔡华博士对西方人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多亏了他,现在纳入在人类学典籍中获得了一席之地。”[2]
为此,蔡华荣获法国科学院授予的2002年度“法语国家金奖”。
两个时代,两个代表,他们都为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人类学界赢得了声誉。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在《读书·评论·学术发展》研讨
蔡华的《纳入》一书成功地挑战了学界和常人已经成为常识性的知识和理念,是中国20世纪以来诸多人类学着作中的佼佼者;这一系列成果标志着“中国人类学的第二个春天终于出现了”[3]。
二
人类学在中国崛起的另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人类学作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地位的广泛认同。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地位是自然科学界公认的,而人们对人类学作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数学”的认识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被定判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枪毙”的往事自不用去说道,自20世纪80年代初人类学在中国恢复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其一直处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缘,默默地但却顽强地在中国做着“扎根”工作。20年的潜移默化,在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互动中,逐渐被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认同,人类学作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地位逐渐凸现出来。最近《光明日报》发表了杨孔炽一篇论述人类学对教育理论研究的启示的文章,十分深刻。好在该文不长,引述如下:
人类学研究对于教育理论创新研究的启示之一,是注重观察基层群众的实践活动并加以分析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将群众文化实践活动的观察研究方式规范化,变成了研究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研究阶段和一种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所谓“田野工作”。田野工作,是指人类学家为了真实地了解某一地方人类的行为,而将自己融入当地群众的生活之中。因此,人类学的“知识建构过程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经过田野工作回到书斋,再把得自生活的新知写进书本”。
与此相比,当今我们关于教育的一些课题研究,却常常显得书斋气十足。在这些课题研究中,究竟有多少是研究者从长期观察和深入分析基层教育活动开始的,又有多少不是从教育专家们预先设定的理论框架出发的?而人类学社会学的专家们在研究中涉及到教育问题的田野调查,可以说为教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范式。“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学科的一种基本研究理念和方法,给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实际上,一切学科理论研究的创新都应基于认真的实践活动。教育理论研究也不例外。
文化人类学研究对于教育理论创新研究的启示之二,是它以“整体性视角”对某一文化进行全貌性的深入研究。试图给出一个全貌性的观察和整体性的结论。这种研究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调文化的背景分析,从而将从田野工作中所观察到的文化现象与广阔的背景联系起来,由此更好地解释和理解所观察到的地区人类社会生活特征。
教育问题的研究应当借鉴人类学研究中的“整体性视角”和多方面的“背景分析”,注意运用更为广泛的背景材料。对于许多教育上的现象或问题,如果能从多雏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那么将会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或效果。此外,过去我们在研究一些教育问题时,虽然也注意追寻它的历史,但往往对历史发展线索进行简单的梳理与引证,缺少深刻具体的历史分析和文化透视。而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看待一些教育问题时,应当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理念长期以来对教育和人性转变的作用及影响,并结合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开展研究。
文化人类学研究对于教育理论创新研究的又一启示,是它的“跨文化研究视角”或“交叉文化分析”。像其他许多社会科学一样,人类学家也必定要跨越某一特定的文化研究边界进行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如同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教育”那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的比较方法或交叉文化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相比,更具有自己的特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研究中“跨文化视角”背后的指导思想,即是所谓的“文化普同论”和“文化相对论”。坚持这“两论”的人类学家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是生物学上的同一种属,文化无优劣之分,但各有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的价值。因此,各种文化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采取宽容的态度。人类学的研究要从主位文化量度及客位文化量度两个方面来观察和分析社会及人们的行为,反对“民族中心主义”或者“文化沙文主义”。坚持以这种观点指导人类学的研究,可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为如果认为自己所处的文化高人一等,必然会引起对其他民族文化理解上的偏见,从而难以获得真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也达不到预期的客观公正的理论研究成果。
当代中国的教育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统计和比较的方法。应当说这是教育研究方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我们的教育研究缺少通过长期深入的基层生活获得的具体而实际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统计结果往往存在某些误差。同时,学者们的所谓教育比较,也只能将国与国之间的宏观或亚宏观比较作为主要内容。建立在教育研究者亲身参与观察和调查基础上的教育比较研究成果,可以说目前还十分少。而“文化普同论”和“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分析异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以克服和减少我们可能产生的某些偏见和短视。
对于人类学与教育学的这种互动态势,杨孔炽在文章的结尾还有一个画龙点睛之笔,他说:
一百多年前,被誉为西方“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泰勒在论及人类学的学科定义时曾经指出,正如挑运重物时增加一条扁担的作用一样,人类学的加重也会“快捷地促使研究负担的减轻,而不全加重……它把日常教育的零散科目合为一个便于掌握的整体”。的确,尽管人类学的观点以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非十全十美,但人类学研究所包含的对人的各个方面的全面性的研究,对于我们教育理论的创新仍然有着多方面的启示。除了以上涉及的几方面之外,人类学研究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文化适应的观点和两代人之间三种文化传承模式的划分(所谓“三喻文化”)等,都对教育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因为人类学与教育学的密切联系,才产生了二者结合的“教育人类学”。随着我国人类学研究的深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对于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影响将越来越大。[4]
正是由于人类学对教育学的这种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基础作用,所以德国人类学家诺尔(HermanNohl)于1930年出版了《性格与命运--教育以人为主》,开教育人类学的先河。20世纪70年代后期教育人类学学科基本确立,这时不仅成立了教育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还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及学科理论;不仅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着,还出现了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不仅构建了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和学科研究的框架,还形成了教育人类学的分支学科。现在中国的教育人类学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有中国教育的文化承继性、学前教育观察点--幼儿园、多民族国家的双语教育、多元文化整合的教育理论构想等。教育人类学的领军人物滕星及王军、董艳等推出的“教育人类学丛书”:《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族群文化与教育》、《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以及滕星的《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等着作,都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的一次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