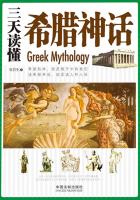一是对女性家庭权利的某种承认。在《布洛陀经诗》中就有涉及财产支配权的叙述。比如,《解母女冤经》说到:主家的女儿赌着气“出去成家”,并且一走就是九年,从不回家看望爹娘,直到落魄时才空着手回来,“来争大母牛,争要手中镯,争要父母钱;争要大峒田,要强壮奴婢;争要大公鸡,争要栏里猪。”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这一段叙述是对远古时代里妇女享有较高财产权的反映,此说应该毋庸置疑;也许还可以说,从该女子对娘家的强硬态度,以及在争财产时的“理直气壮”来看,这种现象在当时并非偶然,或者说是以女性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基础的。当然,这种对女性有利的传统已面临冲击,所以这个女儿的行为受到了谴责和诅咒,并要举行仪式来“绥”(Coih,即修正)。而在《唱罕王》中也有隐喻“母权”的叙述:那位再嫁的寡妇来到王家没多久,就把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接来继承家业,同时处处排挤王与前妻生的儿子,可是王却装聋作哑,不敢制止:“晚窃窃私语,早不断教唆。田埂遭水泡,田间跟遭殃;狠心后母来,父也变后父。”如果剔除经文中对这位再嫁寡妇自私自利行为的谴责,就不难看到她确实拥有相当的财产支配力。这些都是对现实中壮族妇女“当家做主”情况的真实写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壮族的家庭也是以男子为中心建立的。但壮族的男权是一种不彻底的男权,妇女有一定的地位。一家祖父掌权,祖父死后祖母也可掌权。在壮乡,夫妇正当年而妻子掌权的家庭也不是个别的。”[35]
子女婚嫁也是家庭生活经常性问题。在《解母女冤经》中,父母因女儿不答应媒婆的上门提亲而夜不能寐;于是在媒人第二次登门时,“问下家婶母,问上家伯娘”;在媒人第三次登门时,“其父不开腔,其母自答应:进栏抓大鸡,人笼抓肥鸡,陪媒人吃饭;开箱要八字,开箱要命书,列生日时辰。”《唱罕王》也有类似的叙述:当媒婆多次登门要求那个寡妇嫁给鳏居多年的“王”时,斟酌再三并“问下家婶母、问上家伯娘”的是寡妇的母亲,最后作出决定并对媒婆叮嘱再三的也是寡妇的母亲。不难看出,在对子女婚嫁的问题上,母亲比父亲更具有决定权;在这些事情上,婶母伯娘也比叔伯更有发言权。
二是对母亲养育之恩的强烈感怀。由于壮族女性是原始农业的主要创造者,后来又在稻作农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加上在子女生养育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氏族社会存在与繁衍的维系者,因而决定了她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性别的众多理论研究成果表明,妇女在家庭中最为有利的莫过于对“母亲”角色的扮演。壮族社会的尊母传统首先可以从龙母文化的广泛流行得到证明。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娅迈”(即寡妇),有一天捡回了一条濒死的小蛇,并从此与之相依为命。一次寡妇切猪菜不小心砍断了小蛇的尾巴,因此给小蛇起名为“特掘”(“特”指未婚男子、“掘”指断尾)。“特掘”越长越大,寡妇因无力供养只好把它送到河里去谋生。有一年三月三寡妇去世,正在村里人为她办丧事之际,一条巨龙在雷雨交加中把寡妇卷到一座高山进行安葬。以后每年这个时候“特掘”都会回来扫墓,三月三也由此成为一个重要节日。这个故事实质上是对母亲的歌颂,三月三实际上就是壮族的“母亲节”。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36]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远古时代的妇女因在两种生产中都有重要作用而获得崇高地位;后来随着她们在公共领域、社会劳动中的地位作用日益下降,其受尊重的“根据”只能从在家庭劳动、尤其在生儿育女中的“付出”等方面来寻找。《布洛陀经诗》似乎也很懂得这样的道理,比如《唱童灵》就是依此“根据”对母亲进行高度评价的:“童灵乖又乖,放牛在山坡;忽站又忽趴,母牛生犊苦。回家跟娘说,讲给众人听,娘就这样答:牲畜不够苦,母生子更难。小牛头尖尖,生一阵即过;胎儿头是园,痛三天四夜。灵把娘话刻脑里,铭记在心头;灵传娘话下三寨,游说上五村。”所以,到母亲逝世的时候,童灵拒绝众人分吃母亲遗体的传统要求,并且想出妙招化解这种陋习:“牛肝代娘肝,牛胆代父胆,向众人致意。”《献酒经》也有类似的唱颂:“你怀儿下田,你怀儿种地。怀胎九个月,母生女儿来,父千包万裹。父母有好吃,先想到小女,盼女快长大。”尽管认同“孤雌繁殖”的时代早已逝去,虽然父权的影响日益强盛,但壮族先民并未因此而抹煞母亲在生儿育女中的“主要贡献”。比如《解婆媳冤经》有云:“打养子会外逃,打亲子哭怀中;养子难驯服,喂天鹅难饱:不经血染脚,不经手扯笪。”即是说,儿女对父母的敬重首先来自扯心裂肺的“阵痛”。《献酒经》也说:“拿什么还礼,有什么报恩?拿杯酒表意,跪在神台下:母生我痛苦,掰墙又扳床,喝这杯保身。”《布洛陀经诗》自始至饱含着对母亲的尊重和感激之情,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三是对夫妻和睦相敬的一些强调。家和万事兴,壮族及其先民十分懂得这个道理。比如,作为壮族的道德经,《传扬诗》的第三大部分就专门阐述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道德问题,目的就是为了和睦与兴旺。其中关于“夫妇”的要求,首先就是同心同德:“一家两夫妻,相敬不相吵。有事多商量,和睦是个宝。人生只一世,婚姻当要好。儿女同抚养,双亲同侍候”。作为壮族巫教的经文,《布洛陀经诗》在唱颂布洛陀和姆六甲创造天地万物、规范人问伦理道德之时,也比较频繁地涉及夫妻的和睦关系问题。比如,作为“大家长”的布洛陀和姆六甲,自始至终都是以“夫唱妇随”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而在有关“缟”(Gweu,即聚拢)的思想中,更直接包含有夫妻同心同德的祈愿。《祝寿经》说到:“锣钹配唢呐,星星绕月亮,公羊守母羊;父亲陪母亲,相伴成新婚,密似蜂进窝,亲如榫进洞,勤像鱼下簖,绞成对鸳鸯,如青春男女。”当然矛盾无所不在,关键在于男女有了冲突之时要及时、合理地进行解决。对于夫妻之间的不和谐,顺着巫教的阐释模式,《布洛陀经书》认为在于“冤怪”的作祟。比如《造火经》说:“西方妖怪来,夫妻就相骂。”《唱罕王》也说:“西边冤怪来,夫妻就离心。”既然夫妻矛盾的原因来自于超自然力量的作用,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做仪式来“解冤”。这些都向我们表明,夫妻的和睦和谐乃是壮族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
注释:
[1]梁庭望编着:《壮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2]梁庭望着:《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3]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上,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4]梁庭望着:《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页。
[5]蓝柯着:《壮族的史诗,婚姻的教本--试论壮歌(盘同古)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特色》,《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6]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上,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7]林耀华着:《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
[8]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2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9]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上,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10]同上,第238页。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
[12]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上,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14]梁庭望着:《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页。
[15]参见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上,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16]《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242页。
[17]《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页。
[18]梁庭望编着:《壮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19]廖胜、王晓南着:《太平天国寡妇再嫁问题辨析--兼论寡妇再嫁不能作为太平天国解放妇女之论据》,《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20]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1页。
[21](美)梅里·E·威斯纳一汉克斯着:《历史中的性别》,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22]参见梁庭望着:《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0页。
[23]《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24]《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25]参见廖胜、王晓南着:《太平天国寡妇再嫁问题辨析--兼论寡妇再嫁不能作为太平天国解放妇女之论据》,《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26]西蒙尼·德·波伏娃着:《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28](美)梅里·E·威斯纳一汉克斯着:《历史中的性别》,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29]西蒙尼·德·波伏娃着:《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30]参见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31]卡罗尔·帕特曼着:《性契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32]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中国妇女出版社1978年版,第36页。
[33]《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34]梁庭望着:《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35]梁庭望着:《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