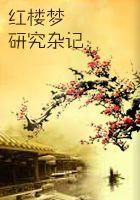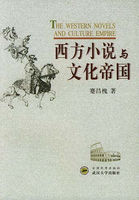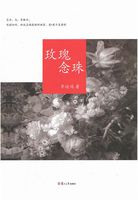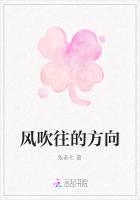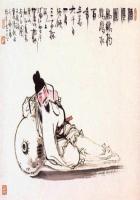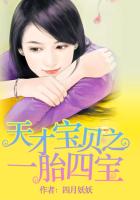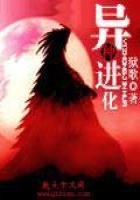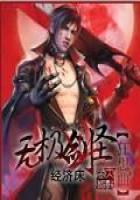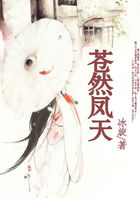《崇文总目》卷五别集类四著录:“汪遵《咏史诗》一卷。”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别集类著录:“《汪尊诗》一卷。”案“尊”字,盖“遵”之形讹。
《通志略·艺文略》第八别集类著录:“江遵《咏史诗》一卷。”案“江”字,盖“汪”之形讹。
《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别集类著录:“王遒一作遵《咏史》一卷。”又著录:“汪遵《咏史诗》一卷”,杂于宋人诗集之间。案宋元公私书目无著录“王遒”者,当为“汪遵”之误。《讲史与咏史诗》五《汪遵、褚载与罗隐》云:“……《宋史·艺文志》皆著录有汪遵咏史诗一卷。(《宋志》唐人、宋人中两见,首作王遒者字之讹也。)”甚是。又俞如云《宋史人名索引》谓:“王遵 撰咏史一卷”。案此条索引据《宋志》原注“一作遵”而既改“遒”为“遵”,却不据《宋志》又著录“汪遵《咏史诗》”改“王”为“汪”,失之眉睫。
《唐才子传》卷八《汪遵》条云:“有集今传。”此当指其《咏史诗》集。
汪遵诗于今虽称一卷,然殊非古代书目所著录一卷之旧观。据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七四录汪遵“《览古》三十九首”,注曰:“本一百首,有前卷已见并删去者”。知汪遵咏史诗集原题为《览古》,有一百首。《讲史与咏史诗》五《汪遵、褚载及罗隐》谓:“宋代著录汪遵《咏史诗》皆为一卷,以胡曾《咏史诗》每卷五十首衡之,知今所见尚无缺佚。”此盖未细读洪氏自注,致有误推。所谓“前卷”当指卷四二已录汪遵诗二十一首。由此推知,洪氏曾在不同时间,据《览古》集与另一集本抄录汪遵诗,而这两种本子所收之诗有同有异。故《宋志》既著录“王(汪)遒一作遵《咏史》一卷”,又著录“汪遵《咏史诗》一卷”,盖非无因。
按照洪氏《万首唐人绝句目录》体例,凡某人于前卷已抄得若干首,后卷又有拾遗补缺,则于后出者以小字注“再见”、“三再”、“四见”。如在卷五三列“胡曾一百首”之目,又于卷五五列“胡曾一首”之目,且注“再见”。又如在卷四三列“张祜八十四首”之目,又于卷六十列“张祜一首”之目,且注“再见”,又于卷七〇列“张祜十九首”之目,且注“三再”,又于卷六九列“张祜二首”之目,且注“四见”。亦有注“集外”字样的,如在卷二列“李白六十七首”之目,又于卷五九列“李白四首”之目,且注“再见”,又于卷七〇列“李白一首”之目,且注“集外”。然而,遍观《目录》,唯一的例外乃属汪遵,卷四二列其目为“汪遵二十一首”,卷七四又列其目为“汪遵三十九首”,却无小字注。显然这后三十九首不属于拾遗补缺的性质,而是从《览古》集中正式节录下来的,与前面从别一集本节录的二十一首为平行关系,故不注“再见”字样。还有一个现象能说明问题。在卷四二的二十一首与在卷七四的三十九首中,有好几首的咏史内容相同。如前者的《绿珠》、《升迁桥》、《隋柳》、《桐江》、《陈宫》等,与后者的《金谷》、《升仙桥》、《汴河》、《严陵谷》、《破陈》等,所咏为同一史事。兹各录两首如下,以资比较。
升迁桥(卷四二)
汉朝卿相尽风云,司马题桥众又闻。
何事不如杨德意,解搜贤哲荐明君。
仙桥(卷七四)
题桥贵欲露先诚,此日人皆笑率情。
应讶临邛沽酒客,逢时还作汉公卿。
陈宫(卷四二)
椒宫荒宴竟无疑,倏忽山河尽入隋。
留得后庭亡国曲,至今犹与酒家吟。
破陈(卷七四)
猎猎朱旗映彩霞,纷纷白刃入陈家。
看看打破东平苑,犹舞庭前玉树花。
又卷四二有《项亭》、《乌江》二首,乃同咏项羽者。而卷七四有《三闾庙》、《渔父》、《招屈亭》、《屈祠》四首,乃同咏屈原者。可见当日汪遵咏史之作与胡曾相似,同一史事,在不同时间反复吟咏。所以,在编辑诗集时各有取舍,有一部分诗在两本之间是交叉互收的,故而出现有同有异的现象。由此益明洪氏所谓“删去者”乃删同存异之谓也。
洪氏于卷四二既录二十一首,有咏史之作十六首,后又于卷七四据《览古》集抄录时删去卷四二已有之篇,得三十九首,但仍是节抄。后人遂合二为一,编在同卷内,原录于卷四二者在前,卷七四者在后,计诗六十首,见明人重编本《万首唐人绝句》卷三五。《讲史与咏史诗》五《汪遵、褚载及罗隐》谓:“《万首唐人绝句》卷三十五,讲史与他作杂厕,共诗五十九首。”案此误计。盖《咏酒》为两首,共五十九题,六十首诗。《唐音统签》重新编次为一卷,又补《长城》一首,得诗六十一首,同上:“《唐音戊签》四十二(《唐音统签》卷六百四十四)……凡录七言绝句诗六十首”。亦误计矣。见卷六四四。《唐诗》稿本直接剪贴自明嘉靖刻本洪氏《万首唐人绝句》,亦补《长城》一首,编为一卷。然其次序却与重编本《万首唐人绝句》刚好相反,原录于卷七四的《览古》三十九首在前,录于卷四二的二十一首在后,《长城》一诗则剪贴自明汲古阁刻本《唐诗纪事》而殿于卷末。《全唐诗》照录《唐诗》稿本,不仅编次全同,且稿本在《题李太尉平泉庄》首句“水泉花木好高眠”之“水”字右旁,据《才调集》校批一“平”字,亦被《全唐诗》吸收,在“水”下出校记曰:“一作平”。同上:“《全唐诗》第九函第八册,此与《万首唐人绝句》是一本,惟将其前半(《题李太尉平泉庄》至《苍颉台》)移于后,将其后半(《彭泽》至《斑竹祠》)移于前耳。盖其所据即出《万首唐人绝句》,惟分订两册,遂致上下互易也。《长城》一首则据《鉴诫录》或《唐音统签》补入,故附于末。”盖未参考《唐诗》稿本,致有此误说。
据上所叙,尽管各丛编本皆源于洪氏《万首唐人绝句》,但由于洪氏分抄于两卷,各家合编时又以己意为序,致使编次大异,不易寻讨。兹以表列示,可一目了然。
汪遵诗的编次,也同于胡曾自编《咏史诗》的体例:“以首唱相次,不以年代为先”。洪氏据诗人集本抄录绝句时,均依其原编的次序。那么,《万首唐人绝句》中的汪遵《览古》三十九首尽管是节本,亦当不例外地依次抄录的。今观《览古》三十九首,完全不按所咏史事的时代编排,与胡曾自编本《咏史诗》的编排如出一辙。《讲史与咏史诗》五《汪遵、褚载及罗隐》谓:“其诗最初殆亦如胡曾诗不以年代为先,按史事排次当出后人之手。”案汪诗“按史事排次”乃出明人胡震亨之手,观表即明。
汪遵咏史绝句步趋胡曾,以上所论还只是形式上的。最能显出效法痕迹的是构思上的模式化,形象上的类型化,立意上的同一性,语言上的通俗性。兹以胡、汪所咏同类题材为例,各举四首,以资比较。
胡曾咏史绝句汪遵咏史绝句函谷关
寂寂函关锁未开,
田文车马出秦来。
朱门不养三千客,
谁为鸡鸣得放回?函谷关
脱祸东奔壮气摧,
马如飞电如雷。
当时若不听弹铗,
那得关门半夜开。姑苏台
吴王恃霸弃雄才,
贪向姑苏醉绿醅。
不觉钱塘江上月,
一宵西送越兵来。越女
玉貌何曾为浣沙,
只图勾践献夫差。
苏台日夜惟歌舞,
不觉干戈犯翠华。(续)乌江
争帝图王势已倾,
八千兵散楚歌声。
乌江不是无船渡,
耻向东吴再起兵。乌江
兵散弓残挫虎威,
单枪匹马重突围。
英雄去尽羞容在,
看却江东不得归。南阳
世乱英雄百战余,
孔明方此乐耕锄。
蜀王不自垂三顾,
争得先生出旧庐。南阳
陆困泥蟠未适从,
岂妨耕稼隐高踪。
若非先主垂三顾,
谁识茅庐一卧龙。
然而,汪遵毕竟是以咏史得名于时,如《鉴戒录》卷九《卓绝篇》即云:“陈羽秀才题破吴王夫差庙;汪遵先辈咏绝万里长城;程贺员外因咏君山得名,时人呼为‘程君山’;刘象郎中因咏仙掌得名,时人呼为‘刘仙掌’。已上名公,称为卓绝,千百集中,无以加此……汪先辈咏史诗曰:‘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不及尧阶三尺高’”。而《唐诗纪事》卷五九谓汪遵以《长城》诗“得名于时”。此外,汪遵咏史绝句亦有不事蹈袭,自出机杼之作。如《夷门》:
晋鄙兵回为重难,秦师收亦西还。
今来不是无朱亥,谁降轩车问抱关?
此诗借古寄兴,感慨遥深。朱亥是具有将才而隐于市的屠夫,礼贤下士的信陵君通过隐士侯嬴结交他,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果然不负所望,夺得兵权,进击秦军,解除赵国都城之围。像侯嬴、朱亥这样的人才,自古无时不有,当今无处不在,而能礼贤下士、求才若渴如信陵君者,又有几何?又在哪里?寄慨深婉,发人深思。又如《昭君》:
汉家天子镇寰瀛,塞北羌胡未罢兵。
猛将谋臣徒自贵,蛾眉一笑塞尘清。
此诗立意深邃,构思新颖,对在强敌面前束手无策的昏庸君主、无能将帅,进行辛辣讽刺,真可谓蛾眉纾国难,须眉自当羞。再如《西河》:
花貌年年溺水滨,俗传河伯娶生人。
自从明宰投巫后,直至如今鬼不神。
此诗取材于西门豹治邺,讴歌其略施小计,巧妙破除河伯娶妇的愚昧作法,造福一方,泽流后世。可能是事小人微,历来鲜有人咏及,而汪遵不仅赋以为诗,且开掘出深刻的主题思想。诗中表现西门豹的贤明,不只是在于他采用计谋来简单地、暂时的遏制愚蠢行径,因为“投巫”之举乃治标不治本,而是发动百姓开渠道,修水利,使田地得以灌溉而能旱涝保收,家给户足,自然消除了百姓祈求河伯降福的迷信心理,取得鬼神永远不灵的效果。时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
汪遵咏史绝句,在古代历史小说中亦有插引,如《西汉演义》第八十四回叙写项羽在乌江自刎而亡,“后唐、宋诸贤有诗曰“……‘不修仁政枉谈兵,天道如何向力争。隔岸故乡归不得,十年空负拔山名。’”此即汪遵《项亭》一诗,惟首句后四字及次句的“向”字为异文。七孙玄晏《六朝咏史诗》考论唐代咏史组诗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