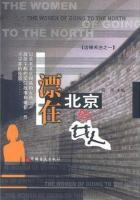湖洲荒草疯长的季节,我赶回了娘家,父亲再度生命垂危。父亲生命的这种危象,近几年来有过好几次了。
前些年,我们把父亲接到城里治病,医生诊断,父亲的病是脑萎缩、腔隙性脑梗塞、帕金森氏症。进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对症整治了一个疗程,花了近万元。
人是好多了,但医生天天催交费用,他心痛得不得了。我们诓他,有什么心痛的,这么些天才一千多元钱。
记得第一次做CT,弟妹们左劝右劝,他就是不上放射台。我办完住院手续赶过去,一边脱他的军力士鞋,一边说,就五十元钱,请您在台子上睡一两分钟的事,这难不倒您,也难不倒我们。
不久,父亲因脑血栓、偏瘫再次住院,我们又一次把他扶上了CT台。在医院折腾了几个回合,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在城里呆了,他似乎感觉出了离地狱直线距离最近的是医院。用他的话说,自己这把老骨头恐怕熬不住了,儿女们花钱也挡不住驾了。
回到乡下,我们买了原屋场堤坡下一间不怎么通风又谈不上敞亮的房子。房前屋后搭了厨房厕所,和住在那栋平房里的几位老人共用一口摇井。在简陋的房间里,我们给父亲开了一张大床。回乡下的父亲就睡在这张床上,能把握的姿势,就是躺着。
也就是说,这屋,这床,这地球的某一个表面上躺着我们的父亲。一位年轻时曾也英气俊朗、横枪跃马的军人;一位把几个年幼的孩子放在一块能浮起的木门片上,夫妻双双激战在防洪北堤的指挥长;一位大跃进时期操心千人填肚,自己糠饼充饥的米厂厂长;一位诚朴正直,而又屡遭运动冲击,饱经政治磨难的“运动员”;一位临到七十岁还在靠锄头养活自己的老农民。他是架中国式老水车,浇灌了成群儿女茁壮成长,如今实在转不动了。
进家门的路,是一条窄窄的堤坡小路,路边满是菖蒲和狗尾草。我们一拨一拨,淋着雨水,踏着泥泞,从各处回到家,屋前屋后围满了人。父亲的后人们都围在他的床前哭喊着,我那学生命科学的外甥女儿,拉着外公枯瘦的手,眼泪像窗外的雨丝,流个不停。
父亲笔挺挺地睡在床上,昂起下巴壳,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任凭怎样叫喊,就是不搭理我们了。一阵哭喊之后,长辈们开始劝我们静下来,我们也只能停息下来,宁静地守候着。
父亲曾对我们说过,他死后要穿中山装,穿军力士鞋,要运到城里去火化。显然,他想后事从简,不随俗。但继母老早已吩咐我们为父亲操办了若干专用品。比如女儿、孙女、外甥女都要给去了的老人盖被,光绸缎被面就花花的买了一大包。父亲还有口气睡在床上时,就已经动不了了,在棺木里也就更不能动弹,干吗还要穿多少层,盖多少床地把他裹着?谁说一死便成大自在?
从父亲叫不应起,继母一直忙着。她连父亲落气后用的串钱、鞭炮都差人买来了,似乎一切都操办好了,只等阴阳两界交接的某一个时刻到来。
孙儿女们一点都不怕爷爷,不时贴在他的心口上听听,不时为他把脉。他们肯定和我一样,以为父亲只是轻微脑溢血,一时昏厥,不动他,等会会醒来的。
有帮忙的人要来给父亲擦身子,穿寿衣。我示意他们先别动他。父亲的老伙计,村里的老支书徐茂爹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在父亲沉睡五个钟头后,他做起了我们的工作,我跟你伯伯、叔叔都商量了一下,劝你不要再折腾了,你父亲这样性烈的人,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成天躺在床上,想翻个身都要求人,身上的褥疮,烂了又好,好了又烂,别造孽,就让他早点上路算了,莫东想西想。
这时,雨已停了,小弟也被人拉去,给父亲看“金井”地去了。村里好多人手在清除屋场周围的柴草,村长还带人把继母开发到地坪里的菜土给平掉了。手扶拖拉机正在一车一车地运柴火来。
父亲,您醒醒,大家都以为您大限在期。您不能就这样走了。十四年前,三月飞雪,母亲脑溢血一旦旦走了。这些年,我们为疏忽了母亲的高血压病肠子都悔青。记得前年大热天,您也是这样昏过去又醒过来了。我和妹妹帮您清洗伤口,好长好长的沙布条,填到您烂了的肉洞里还不够。您的脸上滴着豆大的汗珠。我们要您痛得厉害就喊几声,您还说,那么些年的兵岂不白当了?
去年,继母打麻去了,您摔下了床,我们赶回家时,您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们把您送到医院,输氧输液抢救,您时醒时迷糊。稍清醒一点,就交代,说您死后的悼词要我写,不劳别人。您还抓紧告诉了我二件事。一是告诉了我您当兵时,受编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16团第四野战军政治处,您那时是一名马背上的通信兵。二是,您曾在农场联合加厂任厂长五年,1964年面上社教时,您为困难户开了一些糠饼、酒糟的后门,授人以柄,被争权夺利的小人陷害,打成了“走资派”,撤了厂长。不久,您把自家喂的一只黑山羊杀了,答谢厂里正遭饥荒的职工,又一次被揪出来批斗,最终被排挤出厂,下放生产队务农。
父亲您醒醒啊,还跟我说说您的那些往事。
父亲沉睡快七个钟头的时候,屋外面似乎热闹起来。那只被捉来等父亲咽气时宰杀的公鸡不知怎的,扑棱、扑棱地挣脱,往屋后堤坡边飞去。呼、呼、呼,好像有人从后门跑了进来,一个帅小伙一闪进来,扑到了父亲床前,大声哭喊着外公,并用手轻轻地摸着父亲的脸。我这才回过神来,是我的儿子赶回来了,他坐火车、“水上漂”到喊出租车,从武昌赶到外公家只用了4个多小时。他有备而来,从行李包中拿了一台电子智能仪器,测量着父亲的生命指数。继着又大声喊叫外公,还要我也一起大声喊父亲,一时间,围在床前的人都喊着叫着。我分明看到父亲的喉结滑动了一下,妹妹也感觉父亲有反应,于是把脸凑到父亲跟前,大声问他要喝水吗。“冰!”大家都清楚地听到了父亲说出的这个字。很快,我们从幸福港赶来了冰块、冷饮。用冰块敷,将冷饮一滴一滴灌进他嘴里。醒了,活了,我们的父亲只触摸了一下上帝的神袍又转回来了。
我们马上拨打120,救护车几分钟就赶来了。父亲的骨头肌肉都伸不得手,一挨近他,就痛得打战。送到医院,医生都直摇头。
在一次比一次加重的病磨后,父亲一点一点地从人生世界里离去。他最后的世界只剩下一张床了。神志已不很清楚了,一张被痛苦扭曲的脸已不堪多瞧。他求我们给点药他吃了走。继母还时常从他枕头底下搜出剪刀、绳子之类的东西。父亲连自己把握生命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任我们恪尽孝道地摆布。这对父亲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悲哀的幸福。看他的乡亲们都直摇头:梅胡子实在是好人,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磨难?
2007年8月
写是触摸,回忆是触摸,梦也是一种触摸。每写,每梦,每回忆,都感觉读到了母亲灵魂的色彩。
——题记
我又梦见您了,母亲
襁褓里不只有婴儿
凌晨四点就醒了,最先醒来的是眼睛。因为,一睁眼,梦中盯住的两盏大灯就灭了。
那两盏灯,是晚上照着母亲翻耕、相沟的指挥灯。
母亲,我们知道您是个很棒的农机手。五八年开荒建农场,苏联专家手把手教过您。您是咱们国家第一代女农机手。
您最辉煌的人生,就是在伏克森拖拉机上,抛颠,腾跃,向前。
昨晚,我又梦见您随父亲进湖洲开垦新农场的那些事。
其实,都是我听童话一样,从您那里听来的。不过还是有些亲历的印象。特别是夜晚,那两盏照着您拖拉机开垦的大灯,印象极深。
浩浩洞庭,千年浪涌。时间的大手,把南洞庭泥沙淅淅托出水面,形成了很多洲子。有一块洲子最大,远看像茶盘。五八年,政府令围湖建场,砍杨树,伐芦苇,修大堤。堤围圈起来的湖洲,就叫茶盘洲农场。
父亲从部队转回,踌躇满志,不顾老人们的反对,带着我们娘俩,响应党的号召,奔沅江南竹山而下,开垦新农场。
父亲进湖洲,管开垦人马的吃,位立打米厂。母亲,您是名副其实的垦荒者。
湖洲芦苇飘飘荡荡,千亩沃土泥香草香。黑压压的农垦大军在前面砍杨树,捆芦苇。你们机务队一排排苏式伏克森,锃亮亮,新崭崭地紧随其后。
翻出来的黑土,一块,一片,一天地。您兴奋得忘了自己是女人;忘了自己是奶孩子的母亲,甚至,忘了自己的孩子放哪里。
您说开犁之际,您也惊恐过。那是随着黑土地翻开,飚窜的草蛇,被犁铧削得血溅起老高。您胆战心惊。
一个傍晚,您回工棚,把我抱起来喂奶,解开抱巾,蛇往外直窜。您惊悚得呕吐不止,真想抱着我回沅江老屋里。
您告诉我,您没有退缩。第二天,叫人帮忙把我的摇窝吊起来了,吊在一个临时搭起的木架上。
往后风雨几十年,您也没有犹豫,退缩过。
我开始懂事了,也知道害怕了。害怕工棚里出没无常的蛇;害怕路边窜来窜去的黄竹筒;晚上,害怕杨树山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野鹿嚎叫声。
工棚里没有大人时,母亲您常带我去上夜班。您把我和父亲的军大衣一起塞到您的副驾驶位上,还是专心开您的车。
因为您是开沟标兵,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开示范沟。您晚上开沟不要打石灰线,只要土源档上有两盏灯,照明灯又叫行距灯。您端着身子,握紧方向盘,眼盯着那盏刚移动位置的灯,朝直住前开。开到档上,身后就留下一条又深,又匀,又直的土沟。
晚上,一班一班的人来学,您不厌其烦。老是那句话:白天看线开,晚上看灯开。眼盯着远处的灯,朝直开过去,要一气呵成,不停顿,沟就开直了。
湖洲很静,只有拖拉机轰鸣声;夜晚很黑,只有由远望到近的两盏灯。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母亲,您白天开一天沟,说骨架子都抛散。晚上还要示范到半夜。您哪顾得了我。
有一天晚上,您睡一觉醒来,没看见我,找人家去问,害得大家伙儿,灯笼火把红了半边天去找人。我仍还睡在您拖拉机副驾驶位上。
小时候在湖洲长大,其实,荒野里也滋润着紫丁香,春雨也扰动着树枝,更有那不知名的芽苞四处绽放。童年的眼里,也有过蝶儿闻花,蝉儿鸣叫,鸟儿扑飞。但我的生长环境不产生文学细胞,没有浪漫因子。以至于,后来,我进文学班学习,看到广阔的原野,喜看云卷云舒的句子,就把它改成,原野的夜空,我始终盯着远处那两盏不灭的灯。
我十六岁参加工作。教书,再读书。坐办公室,也做公务员。工作了三十多年。退休了,还熄不下来。去到一家驰名文化企业上班,做一介准编辑。且莫说异地躬耕,要过语言关,转行关,人缘关。就只说搭车上班,也够我托一杠上头的。从家到我上班的传奇文化园,路程不多不少,公交三十二站。每天有近三个钟头在赶路赶车。
事实上,母亲您的奋发和坚强又何尝不是照耀我前行不止的两盏灯。
外号很有名气
母亲,别人给您起了个外号。每有人叫您外号,我都不理人。那是我青葱年纪不懂事。现在做梦都想听人那样叫您一回。
小妹出生,已是您的第五个孩子。您给她取名叫多多。孩子的拖累,使您感到空前的压力。但您仍然乐观生活,拼命工作。
下班路上哼着歌,周末照样打场球。您的外号就是打球得来的。
您经常加班,星期天开会,搞活动。父亲更忙。我们五姊妹年龄挨个只差一岁多。高矮也就像那楼梯墩子。您让我们集体对外展示的机会,是看您打篮球。您是队长,又投篮准。我们看您打球不亚于过节,欢天喜地。
有次,您告诉我,星期天下午有场球。上半场打食堂那头。我背着、拽着几个弟妹,早早地在球场旁食堂那头等候。
我们是您最给力的拉拉队。每个人都不失时机地给您鼓劲。妈妈,加油!换场地,我们一窝又挪到另一头喊加油。看您打球的多,看您这一窝崽女西洋镜的也多。您在场上运球回场,速度很快,齐耳的短发一蓬一蓬,在场外给您加油的,干脆就喊“抱鸡婆”,加油!
二弟比较发调。有次,您在对方篮板下抢了球,快速运球回场,后面几个人穷追不舍。二弟情急之下,冲口喊道:“抱鸡婆”,快跑!加油!
满场都笑翻了。您也抱着球笑得直不起腰。您爽朗的笑声,在场的人都能理会到。母亲爱着自己这窝子女。母亲的羽翼真温暖。
“抱鸡婆”是“四最”农机手,棉田开沟最直、最深、最匀、最好。农场喇叭里,天天叫,天天吹,名声在外。看标兵红榜,大家都指着说是“抱鸡婆”,没有一个人去看您的真名。听农机课,要是“抱鸡婆”讲课示范,就没有一人逃课。小孩一个一个上学,说是“抱鸡婆”的,都有好位子坐。
您虽然很爱孩子们,但您毕竟是职业女性。实在忙不过来时,您的法子是把我们送出去寄养一段。去外婆家或其他亲戚家。
面上社教那几年,国民收入不景气,很缺吃。二弟毛几被送走的次数最多。一担水桶,一头是二弟,一头是糠饼,糠饼是电米厂的废弃物。对河公社里的干爹爹担着二弟出门时,是您最难受的时候。二弟总是扯着您的工作服,央求您:不要送我去公社里,那里吃的是猪食。那时吃野菜加糠很正常。
在家的几个除了我,也好不了多少,大弟吃熬酒的糖膏子,以至于现在都懵了心。
小弟小妹吃的是母亲节省的口粮。母亲去开沟,生产队职工都认识“抱鸡婆”,都这个送给您几斤鸡窝豆,那个送您几斤豌豆。虽然,这一定程度上能填饱肚子,但把您眼睛都吃绿了,害您工作都停了几天摆。
我是幸运的,到父亲那吃食堂。每天按时去食堂翻牌子吃,能吃上白米饭。享受厂长待遇。
后来厂长被打倒。原因之一是经常去食堂灶台勺菜汤吃,罪名是油抹布厂长。
当然,还有一个大罪名是资本主义厂长。父亲当兵在北方,会养羊。家里养了几只羊,闹饥荒时,父亲捉了几只羊到厂里杀了,让职工元旦会餐。管人事的杨女士会餐后立马向上级汇报。我吃父亲的白米饭,就这样断了。
疯狂的年代,常有荒唐的事。
那时期,“油抹布厂长”的坏名声和“抱鸡婆”的大名气,旗鼓相当。
白沙在握的优雅
“九九那个艳阳,天啦哎哟……”这歌是我的摇篮曲。我在母亲温软、甜润的歌声中长大,也常在母亲依稀的歌声中梦哭。
父亲的问题,在无休止地清算。
反对在聪明中级别最低。父亲没有文化,也有点冥顽不化,一味地顶撞领导。被一撸到底。最后一次处理,回到了老祖宗的本行,务农。
父亲和奶奶拖着我们一窝,又要去队上,住泥巴湖芦苇的茅屋了。母亲您心里哭成了海洋,也不洒落一滴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