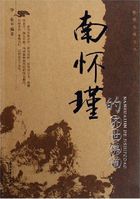绿光就像一个投影仪,照出古朴的某个室内场景,一男一女站在铜炉前。男子看上去也就三四十岁左右,形容憔悴,呈现不健康的红色,说两句话就大口大口喘气。他身边侍候着的姑娘我见过,不,正确来说在杂物房中“梦见过”。如果我没记错,她大概叫迷咩吧!老人脸色凝重把手中的一个物件递给迷咩,略带沙哑地说了:“切记,双簪合一,方能起效!此物费尽吾家数代人心血,但……
“咚——”的一声,绿光收敛了,簪子似乎被什么东西打落,掉到铺着毯子的地板上。我也一下子回到现实,首座悠闲地品茶,春仁一贯以似笑非笑的石膏脸面对着我。那簪子无声无息滚到我脚边,而春仁他们任由我捡起簪子。
这时,我下意识仔细端详簪子:碧绿晶润,簪头雕刻成云朵状。粗一看,跟寻常簪子没分别,但“云朵”的其中一面线条却很奇怪雕作阳线,而不是常见的阴线,另外一面就没有线条,磨成光滑的平面。
我搔搔头皮,一时间没法替簪子产生的古怪情状找个“科学”的说法,眼角瞥到春仁那张扑克脸,竟气闷得一屁股盘腿坐在离首座不远处一把“凳子”上。那首座“嘿嘿”笑了,鼻梁上的伤疤附近臃肿的肌肉挤在一起,我本不在意他的外貌,这会儿突然感到恶心。但脸上保持波澜不惊。“哟,是‘跏趺坐’!从前支公……自贡过峨眉山,一路转车,一路折腾,我到达那也是这么坐法。好嘛,有脾气的好姑娘!”,那首座好像自说自话,春仁顺承他说话的语气:“首座,小女孩还是需要时间调教的嘛,不如归我好……”这是什么腔调呀!春仁刻意放柔的语气,腻得我五脏六腑都翻江倒海,插口:“好什么?我来这里专门给你们消遣的?没事儿,我就走了,反正簪子的事情,事不关己,己不劳心。”说完,顺势把簪子往外抛,这下慌得春仁连忙用足球守门员救球的速度跑上前接着簪子。
“哎,姑娘真性急!你就不想知道刚才绿光中见到的情形究竟什么回事?还有,你以为没有阿春带着,你能往回走?”首座作势摸摸自己的皮带扣,慢悠悠地劝着。我心里暗叫糟糕,难不成他们打算劫持?于是不顾一切地,我朝着刚才进来的门口冲去,猛地打开那扇门,本想抬脚迈出去,可惊得我往后退了:
见鬼了!外边的走廊的电梯早就不亮灯,接驳一楼的楼梯不知什么时候无影无踪,剩下黑黝黝的墙壁。这里透着古怪!
我调转头,看见春仁一步步走来,把簪子又塞回我手心,脑门突突突地冒着汗。谁知他们并没有进一步举动,春仁更退到首座身侧。那首座叹了口气,略带可惜地说:“看来我们的节电举措,让你受惊了。我呢,是因为看上戈小姐的认真、喜欢探求真相的个性,就让阿春邀请你加入我们‘时光机1号’的实验。也许你觉得我贸贸然选人吧,你可知道为什么你看见簪子里出来的人儿像你?”这……我不是一直有这个疑问吗?我欲言又止,不料他笑眯眯继续说:“瞧,我说对了吧?因为我们查证过,这个簪子就是解开人类能否在时空隧道来去自如的钥匙。别怀疑我们,我们有一队人经过长时间明察暗访,得出的结论是,钥匙的人似乎和你有血统上的联系。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加入!春仁拍拍陷入迷茫中的我,加了一把劲:“妹妹,如果解开了时光隧道之谜,你不就可以穿梭时空。到时候,你可以公开成果、名留青史。”
我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突然觉得春仁拍的肩头之处传来酸酸软软的异感,蔓延全身,好像身体不再听从使唤。脑袋不断闪过很多画面,不少是我小时候与马佳相处的时刻:
“马佳,这是我的压岁钱里拿出的。你放心去交午餐费了,不用还我的。”等我转身不久,马佳跑到另外一个角落对着墙边的阴影说:“这钱有了,咱们去买漫画吧。反正戈兰说不用还她……不可能,这不是我认识的马佳!“你这么样做能行吗?戈兰貌似只是把作业借给你抄而已”,初中时代的隔壁班王大强在小声对马佳说,谁知道马佳随便一句:“借给我抄和借给你抄都是抄,没区别啊……
“我没有这样表里不一的朋友,我不需要这种朋友”——我大喊道。睁开眼,触目所见雪白柔软的被铺,墙上靠窗的地方烧着香料,升着缭缭轻烟,而春仁则在窗前的桌边笑吟吟地说:“你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