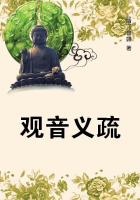望着瘫倒在我怀里的戈兰,如同棉花糖一般任我揉捏。我满意了,这才是乖女孩嘛!之后,她获得的待遇将是——被我全身五花大绑塞入一个早藏好在一堆垃圾家具下的行李箱。临末,照她嘴上贴了块厚厚的封箱胶,以防万一。虽然我对自己配备麻药的量很有信心,到底留一手准备比较稳妥。
所有一切就绪了,我就把人肉行李箱拖着带走,另外又换了一个人皮面具,从外表看来,我就像个行色匆匆的旅客。站着破破烂烂的门槛边,环顾一下这仍带着焦糊味道的房子,我摇摇头了,原本趁着麻药的效力在,就地採血为好,再干净利落了结她的生命。但考虑到在脏兮兮的环境里,恐怕会对血液造成污染,毕竟簪子多年未尝过人血了,一定不能沾上半星的杂质。如此大费周章,不如我从前处理得痛快,特别我进入永生后处理掉的第一人。
回想起来,那个家伙本来是死有余辜的。为什么这样说?就凭躺在战场上枉死的冤魂,就凭傅君对我曾经的恩惠,他的恶行足够死上两三回。
要说能在交通不发达、通讯手段落后的东汉碰到他,可谓老天开眼。当我遍寻羌寨,再也探不出一丁半点关于另外一枚簪子的下落时,唯有一个人漫无目的沿着洮水南下,看见路边的酒肆人声鼎沸,就过去闷着头吃酒。不意隔三张酒案那边有人高谈阔论,声音挺宏亮。本来这种借酒助兴的场合,声音大点,实在太正常了,但在汉羌交界的地方,故意用洛阳话摆谱,就有点令人憎厌了。
我循声望过去,突然全身血液像要沸腾了,不禁暗呼:甘万寿,你这个叛徒,临阵倒戈,害死了傅府君和一干兄弟。今日我要教你晓得我的厉害!边想边不自觉用手按着腰间宝剑的剑柄。这旁边的人没有惊讶于我的举动,要知道羌人勇悍,出入带刀,附近汉人各个乡里为求自保,也相继持械傍身,久而久之,边地民风习以为常。只要不抽出白刃,无人以为犯事,假如换作京畿管辖范围,我的些微举动,早有人举报与官府。
却听得甘万寿自矜得意,又语带可惜说了:“怪只怪那对小鸳鸯互相猜忌,不然际山怎么会
信了我说的话?小贱人自己没福气,当初要听了我的话,别说保全性命,进京面圣那也不是不可能。至于好婚事,更加如囊中探物。”他身边充当捧场客的凑趣:“好歹是你亲姊妹,人已经去了,你怎么也得做个悼念姿态?”甘万寿眼珠子轮了一眶,轻蔑地哼了哼:“姊妹?谁和她有亲!她啊,是家父的外宅妇,我家名册上有她母女的名字?从前家里交口赋,她们俩有出过什么力?家父去世后,是我这个长兄供她吃、供她穿,到头来她竟然不知廉耻,和个蛮夷种搞在一起。要是她乖乖献出宝物,我现在早就飞黄腾达。”
好笑,“供她吃、供她穿”,一句话就把我、阿奴、阿成三人抚养阿菀的功劳抹杀了。轻巧,真轻巧!
岂料,甘万寿同席的人,哪壶不开提哪壶,接着发问:“前不久传出消息,说你和迷吾把酒言欢啊,那汉兵那边你又如何应付?”甘万寿恬不知耻,脸不红、耳不赤说了:“你懂什么!这叫左右逢源。我转头向朝廷出售羌人的机密,同样可以获得青睐。让朝廷出俸禄是富贵,与满意交易获取巨额山货也是富贵。要什么名垂千古呢,不是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我已经不要大名了,富贵我总还能追寻吧。”
越听下去,我的内心滴血得越厉害。其实,我早知道遥远的皇帝陛下,他的光辉根本不能遍及边地的每片村寨。傅君崛起迅速,而遭致灭顶之灾,固然有其本身贪恋功名利禄的深因,可四海之内,谁愿意甘心屈就人下!前有卫霍赫赫战功,当时有窦固击匈奴,后来者更不知其几。但我之所以愿意襄助傅君,是因为从他身上看到我将来平视世界的可能,而随波逐流地,匍匐在一座又一座大山之下。
这并非夸饰——自我懂事以来,主人闪动的双眸,如令箭所指,那种威慑力只供人仰视,也提醒着我,每天面对的是一棵深不可攀的参天巨杉。当我带着阿奴、阿成兄弟四处流浪时,原以为能够成为他们俩的依靠,一旦受严重的温饱困扰着,我们不得不寄身于阿奴父辈呆过的羌寨内,于是我心中本来崛起的山岭颓然崩溃。
直至某天,我外出采办村寨物资回来,盯着主人遗留下的玉石,不断想着怎样充分利用这些充满灵性的宝物,以待日后借机查明主人枉死的真相。我背后的门口“嘎啦”的响,阿奴进来了,手里托着一管莹莹碧绿的簪子,放在我面前,簪子底下还压着一块写满字的大木牍。看着我愣神的样子,阿奴解释道:“仲恒兄,此乃我与阿成想出研发玉石为簪的雏形,当然用的是普通劣质玉石。但咒语我也想了不少。哈哈,师尊的遗书果然令我等受用不尽啊!”阳光在他背后包裹着他的笑脸,就像给他的头顶罩上耀眼的光环。我吃惊之余马上快速浏览木牍上的咒语,企图找出阿奴方术里的破绽。
没有,为什么没有!我心中那座崩塌的土丘,瞬间被风沙肆虐得荡然无存,整个人只想着瑟缩到角落。原来只需要他们俩兄弟商量,我回一句:“研制女娲留下的灵石至关重要,为何就你俩费力研制?教我知晓,岂不是多一份力量?”阿奴摸摸后脑壳,笑呵呵说:“是我们俩性子太急了。汉羌之间情势微妙,我怕有个万一好歹,咱们又必须逃亡。还不如早早定了,好利用来为师尊洗刷冤屈。”我的手在下摆人说看不到的地方揉捏着:好吧,万一日后研发簪子中,出任何乱子,我概不负责!
兄弟呵,兄弟。这就是兄弟了?嘿嘿,古谚说的好,“谁为为之?孰令听之”,沙颗怎么能跟山岭比较?所以傅君给予我一扇带着阳光的窗子,有时能在日间偷来的一点空隙里,幻想自己的背脊上也生出像阿奴一样的光环。尽管我刚毁容那刻,确实产生了包括他在内的强烈抵触,那不过怕自己再次被害罢了。然而又是傅君,用实际行动解我燃眉之急。因此,我领的就是这份情,报的就是那份恨!
刚好,那家伙自己喝大了,飘飘然不知所以。眼看着他挥手作别同行友人后,竟独自返归,丧失了必要的警惕,醉眼惺忪地在野地接手。我尾随而至,他的一举一动,我尽收眼底。时机差不多了,我倏然扑出,狠狠地摁倒他,赚他个出其不意。为了防止他反抗,我上来即一顿胖揍,使甘万寿从醉醺醺的状态直线落入两眼金星的处境。等他真的醒来,已经迟了,手脚捆上牛皮筋造的绳索,由着我强行拖走。
“呀,这是什么?壮士……”甘万寿大概万万想不到,明晃晃的白刃架在他的脖子上,寒光闪闪。毕竟,见过世面,他很快就镇静下来,腆着脸、赔笑着:“壮士是何人氏?若为财货,某不吝其数,人命关天的,你别冲动!”嘿,有趣!死到临头,大多数人即便遇上剪径,怕已经吓得大喊救命,甘万寿这家伙却马上记得用手上的财货谈判。我决定耍他一耍。
于是板起面孔,对他说:“甘君大错特错了。我乃泰山府君座下勾魂使者,今奉命押解你。且把你生前犯过的罪行从实招来,如有隐瞒,小心我给你身上画个花儿,呆会马上送你下炮烙大刑!”边说边用匕首在甘万寿的腿上反复摩擦。四下里刮着冷风,顶上是黑峻峻的夜幕,我的话又故意说得阴森森,吓得姓甘的额头添了几条水痕。
他牙关打着颤儿,说:“是……是,小人有死罪,上仙饶命!”我微微翘起嘴角,反问:“例如呢?”“小人……骗了迷吾,平白得来不少山货……”他憋出这么一句。岂有此理!面对“神明”,还尽挑些不轻不重的。我手上使使劲,“啊……别……”,甘万寿痛得呲牙咧嘴、泣涕不止,他的大腿也一片殷红。看到效果差不多,我冷冷地说:“这叫什么罪呀!你不老实坦白,就得付出代价。”
甘万寿眼里满是哀求,一个劲说:“好好好……我说,我说……我为了前程和富贵,骗了际山从阿菀手里夺来簪子……”怎么?姓甘的,竟跟簪子扯上关系了,可我不是听说际山和阿菀已经身亡?手上用匕首抵着甘万寿的另外一条大腿,喝道:“所以你杀了他们?你这个畜生!”“冤枉啊上仙,小人岂敢!小人跟他们俩争抢簪子的时候,一团混乱,阿菀自己堕崖在先,际山那小子痴心一片,跟着去了。这和小人有什么干系呢?再说,后来小人也没得簪子。”
我差点想骂娘,到底簪子在谁手上,你倒是痛痛快快一口气讲完!于是,按捺住心头冲动,我轻轻在甘万寿另外一条腿上切了个小口,他随即夸张地叫了:“我说的都是真话!那晚上我为了簪子,亲自跑下去悬崖下面看。谁知道我碰到另外一个人,他身手胜过我百倍,打不了我只能逃走。簪子自然落入那个人手上。”“你碰到谁?”我逼问。这次匕首已经改在他的脖子上摩擦。“是……我当时认不得清,他蒙着面呢。但我记得,那人手腕处有个碗口大小的疤痕。”
阿成?我兄弟三人对彼此的身体特征,了然于胸。阿成小时候顽皮,曾钻进后厨,不小心打翻灶台上刚出锅的热汤,手腕因此留了个疤痕。原来簪子辗转到了他手上!很好,日后总算能找到方向,不用像盲头苍蝇般,四处游走。
然而,另外一个问题冒出来了,甘万寿到底知道簪子的秘密多少?以他好财货的性格,决不会看上平民百姓的所谓传家宝。夜长梦多,留了后患,着其祸无穷。我把匕首往甘万寿的颈部抹过去,鲜血喷溅。姓甘的手脚扑腾了几下就不动了,好笑了,这就是万寿无疆吗?他应该改名“无寿”!
那年头,把人一扔,连坑都毋须考虑挖,我就能潇洒离去。而现在?唯有苦笑!拉着沉沉的行李箱,我忍不住发牢骚了:“看着戈兰那小蹄子一点都不肥,为何就沉甸甸的?哼,果然要减肥!”
“仲恒兄,小心舌头!女孩子最忌讳就是别人说她老、说她肥。难怪千年下来,你总是孤单一人。”前方有个人影挡住我的去路,并用久违的乡音说着。我应声停住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