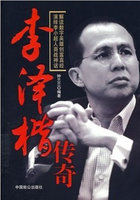章友三说的“破案”,实际上是制造了两起冤案。戴笠在上海苦恼了两天,为了向蒋介石交差,由陈恭澍派人抓来一个兜售水果的小商贩,硬说他是共产党的基层支部书记,是他指使行刺影佐的。至于放毒,影佐、臼井和王顺民都不怀疑李玉英,遭殃的是二楼的接待员宋丽英和靳丽华,“黄泥掉进粪缸里,不是大粪便是屎。”宋丽英怎么也不承认她放毒,被活活折磨至死。靳丽华在严刑拷打面前屈服了,想到近日重庆街头张贴着捉拿贩毒犯张一明的通缉令,她灵机一动,就说他是延安派往重庆的共产党员,用两千元钱买通她毒死影佐。但是,靳丽华的交代无法得到证实,她被投进了重庆监狱,暂时不放也不杀。经过何应钦和张群一场变戏法,监狱里的一个男性犯人就变成了逃犯张一明。臼井离开重庆前夕,他由章友三和王顺民陪同,在监狱里与这两个人见了面。这两个人想到监狱长的许诺,只要能够蒙蔽日本人,不仅可以很快获得自由,而且可以得到一笔巨款,于是,都当着臼井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谋杀影佐的指使者。现在,谷正之要求将这两个人交给日方审讯,章友三想到的并不是国际上没有这种先例,有失国体和有失民族尊严,而是担心他们既没有获得释放,也没有得到巨款,肯定在日本人面前反口不认账。
“我的意见,来一次暗杀,把章友三和汉德威干掉!”芳子淡淡一笑。但凡当特务的人都有副歹毒心肠,她那语气和神色,杀两个人好像杀两只鸡。她顿了一会,进一步说,“影佐先生赴重庆的消息传到东京以后,引起日本朝野许多有影响的人士和普通臣民的严重不满,东京街头出现好几种传单,其内容大致是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派影佐赴重庆,是日本政府低三下四的表现;二是重庆如此对待影佐是对日本政府的当头棒喝,三是日华和平运动,华方必须以汪先生为旗手。”她两只会说话的眼睛骨碌一转,说道,“我们不是常说‘因势利导’吗?章友三和汉德威被干掉之后,可以利用日本人的这种不满情绪散发传单,就说是对重庆当局的报复,或者叫惩罚。”
“这样做,对南京政府极为有利。”李芳兰补充一句。
“衷心感谢姐姐的开导和支持。”徐珍感情真挚地说。她想了想,又说,“我的意见,最好抓活的,不处死他们,但可以印发他们被绑架的传单,这可以增加一点神秘的色彩。”
芳子愣怔片刻,不解地问:“又不是撰写高深的理论著作,为何要使人感到神秘莫测?我看,还是把他们干掉痛快!”
“把这两个人抓到之后,我想把他们秘密送往南京。”徐珍的眼睛里闪耀着异乎寻常的光辉,“在适当的时候,或作为一份情意将他们交给日本政府,或作为一定的条件交给重庆政府,看哪样做对我们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有利。”
芳子对徐珍的老谋深算很钦佩,也不固执己见,微笑着说:“翠子妹妹想得周到,那就抓活的吧!不过,人们不免要问‘这两个人怎么会落到南京政府手里?’”“感谢姐姐的提醒,让我好好想想。”徐珍陷于沉思。“我看可以这样应付过去。”张冰洁说,“日本朝野不是一股强大的反蒋拥汪势力吗?就说是这股势力范围中的某个团体或某些人将这两个人秘密交给我们的。”“行!走一步想一步,先把人抓起来再说。”芳子把抓人的手段说了一遍,大家又你一言我一语做了补充,决定晚上十二点以后动手。晚饭后,张冰洁和李芳兰都提着补品,随同徐珍、芳子和谷荻,由双方的女卫士护送,驱车来到医院的影佐病榻前。
影佐斜靠在床头上,脸色苍白,眼窝深陷,颧骨高隆,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如果不是眼睛还在动,与死人无异。他张开嘴,接受妻子用调羹送去的肉泥稀饭,一眼见到徐珍和芳子等人到来,立即停止吃东西,想挣扎着起床,但感到力不从心,被谷荻按住他的肩膀制止说:“不用起来,就这么斜靠着。”
“这是汪主席夫妇赠送给影佐先生的四斤干荔枝和一斤人参。”张冰洁把礼品递给影佐妻子。“这是金司令赠送的五盒十全大补丸和四两鹿茸。”李兰芳也把礼品递过去。
“这怎么行?麻烦汪主席夫妇和金司令破费,实在受之有愧哩!”“影佐先生不用客气,一点小意思,实在拿不出手。”芳子说。“战争时期在东京买不到好东西,这么一点东西,只能说是礼轻情意重。”
徐珍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近来感觉怎样?哪些方面不舒服?影佐先生!”“头昏得厉害,有时好像要断气似的难受,再就是浑身没有一点劲。”影佐有气无力地说,“感谢诸位来看望我。”“你继续吃吧!影佐先生。”芳子把滑到影佐大腿上的被单轻轻地拉到他的胸前。
“不想吃了,胃口不好,好像吃泥巴一样。”影佐将客人一一介绍给妻子,然后难为情地对她说,“茶杯不够,连请客人喝茶的条件也没有。哎,床头柜里还有点苹果,你拿出来请客人吃吧!”
“不用了,你留着自己吃。”徐珍制止影佐妻子开床头柜。影佐住的是二号病房,房间里除了一张病床和一个床头柜以外,只有两张骨牌木凳和两张各可以坐两个人的长条木靠背椅。“真对不起,座位也不够,有三位客人只能屈坐在床沿上。”影佐妻子抱歉地说着,又埋怨起来,“三年日华战争,唉!连第一流的东京大医院也变得这么寒酸。”
“是呀!实在是委屈了诸位贵宾。”影佐感到内疚,轻轻叹息一声。
“没关系,坐在床沿上很好。”刘淑珊说罢,主动拉李玉兰往床沿上坐。芳子的两个卫士相互谦让了一番,一个挨着刘淑珊坐着,一个坐在骨牌凳上。
影佐想打听芳子和徐珍出访东京的打算,但感到这中间有着一层厚厚的隔膜,终于没有开口。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徐珍和芳子也把影佐当成局外人。
房间里的气氛表面上是融洽和亲热的,实质上是僵持和冷漠的,各怀戒备,也各怀鬼胎,在相互窥探,也在相互猜疑。好像乌云里蕴藏着风暴雨雪,又像平静的河水深层潜伏着激流。
“我的情况相信诸位都知道了,我,我对不起汪主席夫妇!”影佐想争取主动。他显得笨嘴拙舌,似乎很难过,也似乎很痛苦。“那天接到首相府的电报,说有紧急绝密要事,要我立即回东京,我只好从命。那份电报我也给汪主席看了。如果,事先知道是要我赴重庆,我可以用种种借口推辞不去。从东京动身去重庆的前一天,正好西义显先生从东京返回南京,想把我这次秘密行动由他转告汪主席,但害怕泄漏绝密治罪而不敢。不过我绝非有意背着汪主席!我只好暗暗告诫自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一定不要丝毫损害汪主席在中国的领袖地位。”
“真的是这样吗?影佐先生!”徐珍冷笑一声,“当然,阁下的重庆之行,是出之不得已,汪先生表示谅解。但是,你说的所谓丝毫不损害汪先生在中国的领袖地位,那仅仅是让蒋介石恢复他离开重庆前的职务呀!”
“影佐先生在重庆的所作所为,汪主席他们了如指掌。”芳子与徐珍同一个鼻孔出气。她性格放荡不羁,也不管影佐受不受得了,直截了当地说,“汪主席他们是那样以诚待你,你应该说真话。也就是说,你应该检讨,应该痛改前非。”
如同癞痢头被人揭了帽子,影佐感到无地自容。一阵沉默之后,他哭丧着脸说:“我真无脸见到二夫人,也无脸再去南京任军事最高顾问团首席顾问,真不如死了好!近两天,每当我想到这里,就埋怨重庆的两个学长,埋怨他们把我从死里救活过来!”
徐珍暗暗骂道:“如果你影佐真的想死,为什么不拒绝接受医疗?伪君子你哄谁?”但她表面上却是另一副嘴脸,以宽容的语调说:“尽管如此,汪先生和君姐,以及陈院长、周部长和褚外长他们,仍然以诚相待影佐先生,欢迎你病愈后赴南京共事。”她为了让影佐妻子给他以严重的精神摧残,以解心头恨,把严珍妮的死,汪精卫他们拨款和派人为她料理丧事等情况简要地说了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两张遗书影印照片,一张递给影佐,一张递给影佐妻子,装出一副伤心的样子对她说:“请夫人过目,你这位中国妹妹死得好惨啊!”
影佐面对妻子是恐惧,面对遗书是悲伤,想哭不能哭,想说又不知说什么好,有一种无法用语言描绘的痛苦。他的妻子则是满腔愤慨,顾不得有那么多的客人在场,一头撞在丈夫的胸脯上,哭喊着:“原来,你七八个月不回东京,又不让我和孩子们去南京看望你,因为你嫌我老了,又找了新欢!我的妈呀,您若在天有灵,可怜可怜你这苦命的女儿啊!”她由于狂怒,嗓门变得沙哑了。
徐珍感到痛快极了,本来就很明亮的眼睛愈发明亮了。这时候若看她一眼,准会把她当作领奖台上的冠军。她仿佛在奇异的幻景里看到了自己征服一切的力量,心胸里荡漾着一种豪迈。
“噢!原来夫人还不知道影佐先生在中国娶了姨太太。我真懊悔自己失言,请影佐先生原谅,”徐珍又敬巫师又做鬼,“不过,夫人不必伤心了,人已经死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今后你们这对结发夫妻一定会恩爱如初哩!”
“恩爱如初?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他那个爱妾不是在遗书里说,希望他再找一个比她更好的爱妾吗?”影佐妻子仍然将头在丈夫胸脯上乱碰乱撞,披头散发像一个女疯子。
从广义上说,女性对男性纳妾都是极为反感的,芳子也不例外。她为了使徐珍的此番用意获得更好的效果,用比平日提高八度的咏叹调大声对影佐妻子说:“只有女人才能真正理解女人的思想感情,我完全理解夫人此刻的痛苦和不幸。”她扭过脸对影佐说,“影佐先生!你就向夫人表明个态度吧!保证今后不再有别的念头,一定与夫人恩爱如初,白头偕老。”
“金司令!我怎么这样命苦啊。”影佐妻子双手握着芳子一只手使劲摇着。她心中的怒火更加炽热地燃烧起来,又一头撞在丈夫胸脯上,痛哭着喊道,“你是不是还想再找个中国姨太太?你怎么装聋作哑不说话呀!”泪水从她双层眼皮里冒出来,像瀑布一样往下淌。
影佐体虚,又突然被惶恐和悲痛折磨,造成大脑功能的严重紊乱,加之被妻子这么一阵无情的折腾,脑袋一歪,昏死过去了。
他妻子见此情景,既惊慌,又懊悔,立即停止了哭泣。妻子毕竟是妻子,她擦着眼泪喊医生去了。
徐珍希望影佐不再苏醒过来,他如果这样死去,责任还在蒋介石身上。但是,事与愿违,经过医生抢救,他又活了下来。她见影佐妻子不再哭闹了,又对影佐发起精神上的进攻,说道:“既然影佐先生在南京纳妾的事,夫人已经知道了,不妨再说两句。这是影佐先生赴重庆的血的教训啊!严女士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她年轻俏丽自不待言,最难得的是她那么聪慧能干,那么心地善良,那么通情达理。”她望了影佐妻子一眼,继续说,“就是夫人见了,保管你也会爱她三分,亲她三分,痛她三分呢!”
徐珍的话,并没有引起影佐妻子的同情,她伤心地说:“我不爱,我不亲,也不痛她!这个女妖,夺走了我的丈夫,她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
但徐珍的话,却引起影佐一场痛哭,他呜呜咽咽地说:“我一定以自己赴重庆的痛苦经历,尽可能地说服内阁五相会议诸成员,让他们死了这条心,从此不再与蒋先生往来。”他再也抑制不住对严珍妮的悲伤,五内俱裂似的哭着说,“妮珍呀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呵!”他妻子很反感,似乎又要发作。影佐拉着她的手说,“我同样对不起你呵!从今以后,让我们白头偕老,你原谅我吧!”
“好了,好了,一切都如同一场噩梦一样过去了,影佐先生伤心也无用,夫人悲怨也枉然。”谷荻劝慰说。他叹息一声,又说,“的确是一场噩梦,也是一幕悲剧。诚如昨天下午汪主席接见阿部特使和我时所说的,与阴险狠毒的蒋先生讲和平,犹如跟老虎交朋友,不会有好结果!”
影佐想了想,解释说:“汪主席的论断是无比正确的,我刚才说了,一定以自己的痛苦经历,帮助内阁五相会议诸成员认清蒋先生的阴险本性。不过,这回在重庆谋害我的,是共产党干的,若不是臼井先生在监狱里见过行刺和放毒的两个指使者,而他们也一一供认不讳,我真不敢相信呢!”
徐珍当然心中有数,冷冷地说:“共产党的确可鄙可恨。但是,蒋先生的话绝不可信,如果将那两个人提交西尾总司令他们审讯,保险是假的,也保险会真相大白!”
“正因为如此,章友三不肯将那两个人交给日方审讯,这中间就是有鬼!”
芳子的话一针见血。
“难道我们上当受骗了?”影佐沉思着。
这时,美静子欣喜地走来,高兴地对徐珍说:“近卫首相特地派我来通知徐特使,他说有重要事情磋商,晚上九点在首相府单独接见徐特使。”她看看手表,“只差二十分钟了,请特使女士上车。”
徐珍一听,觉得一股热烘烘的血突然从心底涌到脑子里,后脑一阵阵发烫,每根头发的根部似痛非痛,又似痒非痒。她想去,又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她无法自立,乖乖地站起身来随美静子上车。临走时,她向影佐告辞说;“我走了,请多保重,过两天我再来看望你。”回头又对芳子说:“姐,我走了,你们再坐一会。”芳子没有吭声,只沉重地点了下头。她对徐珍曾一度是近卫的情妇很清楚,明白“单独接见”意味着什么,望着徐珍走出病房的背影,心中泛起一股人老珠黄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