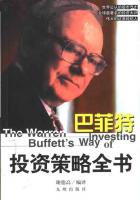皇帝心中反复的思忖,已然是颇为意动。
“既然如此——”皇帝沉吟着开口。
褚琪炎却是急了,近乎是有些失态的一下子站了起来,因为动作太过剧烈,刚刚放回桌上的茶碗不稳,砰的一声砸裂在了脚下。
皇帝诧异的看过来一眼。
这个孙子向来稳健,和褚琪枫不相上下,可是今天——
他似乎是有些失态了。
褚琪炎的面色一僵,赶忙跪下去请罪道:“琪炎一时失手,请陛下恕罪!”
“不过就是打碎了个茶碗,没什么大不了的,起来吧!”皇帝道,倒是没往心里去,只对旁边宫婢吩咐道:“收拾了,重新换过。”
“是!”宫女应诺,收拾了碎瓷片,跪下去擦拭地面水渍。
皇帝手里捏着两分庚帖就要旧事重提,褚琪炎见状,一咬牙就又往前一步道:“皇祖父,太子对浔阳一向看重,即使是再合适的八字,也总要问过太子殿下的意思,若是越过他去,怕是不太好。此事不必急在一时,等询问过太子殿下的意思再下定论不迟。”
他的语气平稳,尽量掩饰住心中急切的情绪。
延陵君稍稍飘过来一眼,唇角勾起一个弧度,眼神里面却透着丝丝凉意——
他是之前就察觉了褚琪炎对待褚浔阳的态度有问题,但是现在看来,这问题可远比想象中的要严重的多。
皇帝那里,似是被褚琪炎说动了。
风邑抿抿唇,朝延陵君递过来一个询问的眼神,见到对方一副有恃无恐的摸样,心里无奈的叹了口气,就又拱手一礼,笑道:“南河王世子多虑了,此事已经不需要再额外征询贵国太子殿下或是浔阳郡主本身的意思了,因为——”
他说着一顿,脸上笑容就越发灿烂了起来,道:“太子殿下那里已经表示十分属意此事,只要陛下首肯,那么咱们两家人都是皆大欢喜。”
皇帝听了这话,就只下意识的以为他是和褚易安私底下有来往,脸色立刻就变得十分难看。
风邑却是全不在乎,还是笑意绵绵的扭头冲延陵君一抬下巴道:“君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事到如今,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舅舅能为你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你还不请皇帝陛下成全?”
满殿的人都面面相觑,惊诧不已。
延陵君往前走了两步,挨着风邑跪下去,道:“荣烈倾慕郡主已久,还请皇帝陛下成全!”
这一刻,他脸上笑容隐去,神情极淡,和以往众人眼前那个风流倜傥谈笑风生的延陵君完全的判若两人,却是——
清俊而卓绝的一个人,从容镇定,不卑不亢。
着是历尽千帆的皇帝,这一刻也有些难以接受这样错乱的身份转变,他的嘴唇蠕动,却是半天没能说出话来。
褚琪炎狠狠的闭了下眼,掩饰住眼底自嘲的情绪,再重新睁开眼的时候,眸子里还是一片清明冷然的神采道:“安王殿下您确定这不是在开玩笑?眼前这位刚刚辞官而去的延陵君就是您那重病缠身的外甥?”
延陵君现在的确是身染恶疾,但很显然,当初他刚到西越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
“南河王世子这是何意?外甥难道还是可以随便冒认的吗?”风邑说道,面上还是一副坦荡又无关痛痒的表情。
“既然你肯认了,那就好。”褚琪炎道,语气冰冷,神情淡漠,“如果本世子没有记错的话,年前他荣家公子初到我朝之时,正是两国兵戎相见,战争打的尤为惨烈的时候,那种情况下,他堂堂南华镇国公府的嫡系子孙却改名换姓,编造身世,混入我朝为官,还千方百计的接近陛下身边,他的此种举动,您就不觉得不合时宜吗?”
皇帝心里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一重,心里的芥蒂之意突增。
“这个么——”风邑被他问的一脸尴尬,掩饰性的干笑了两声,才有些底气不足道:“世子所谓的不合时宜具体是指的什么?方才您带来的这位所谓神医和那些太医们不是都有言在先的吗?你这意思,难不成是指的君玉图谋不轨,有谋害西越皇帝陛下的嫌疑?这话你方才怎么不说?便就要等到本王当众认了外甥之后?这其中是否就有针对的嫌疑了?就因为我们是南华人?如果本王所闻非虚的话,我是记得之前君玉曾在年初的宫宴上救过皇帝陛下一命吧?本王承认他隐姓埋名是有不对,可是就事论事——你若是真的拿出他图谋不轨的罪证来,本王无话可说,而你要只是因为他是出自南华而一定要栽一个欲加之罪下来——”
风邑说着一顿,随后便就冷了脸,寒声道:“你要明白承认是这回事,本王也不与你再分辩,万事都请皇帝陛下休书一封去同我皇兄谈吧!”
如今两国正处在缓和关系的关键时期,如果就只因为延陵君是南华人就要追究——
无异于是当众给了南华皇帝一记耳光。
皇帝也是搜肠刮肚的想,竟然真是不曾找出延陵君身上的什么错处来。
褚琪炎碍着皇帝的面子,也不能过分和风邑争论。
延陵君便是冷笑一声道:“还有世子你说我隐姓埋名我认了,至于编造身世一说,可就是无稽之谈了。当初我来你西越之初就和简小王爷说的很清楚了,我是来投奔我师伯的,我母亲师从鬼先生,是他的关门弟子,这也有问题吗?你倒是说说看,我有哪一句是编造出来的?当初陛下准我接管太医院,无疑也就是看中了我的这一重身份,我是没有主动言明我父母姓甚名谁,可我师公一生就只收了我师伯和我母亲两名弟子,如果皇帝陛下认为我这样也算刻意隐瞒的话,我也无话可说!”
延陵寿的脾气古怪,又神出鬼没,皇帝是早就从陈赓年那里知道他还有一个女弟子,可是对这女弟子的身份,陈赓年却是绝口不谈的。
延陵君这明显就是有备而来——
他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漏洞,显然是从他来西越之初就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防备着有朝一日东窗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