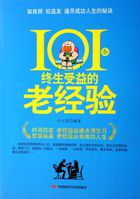儿子虽然小,但好奇心非常强。每当门口来个磨剪刀之类的江湖艺人,他会眼巴巴地围看几个小时,直至艺人走出多远,儿子仍是意犹未尽。适逢有人在街头搞修配,那怕风再大,天再冷,儿子都会津津有味地围在一边,寸步不离。儿子看着别人忙忙碌碌,回家之后也非要实际操作一番不可。儿子让我给他找出锤子、钳子之类的工具,模仿着看到的一幕,在板凳上敲砸得“梆绑”有声。有一次,儿子竟然把几十根小钉子全部砸进了板凳。没有亲眼所见,我根本不相信这是儿子所为。我当时只是想到,一定是哪位手脚没处放的人,故意在板凳上“恶作剧”。妻了却一再声明这千真万确是儿子的“杰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半信半疑。我不相信不到两岁的儿子会把一颗颗钉子,那么准确无误地砸进板凳里。一天,儿子又在板凳上“梆梆”地忙乎着什么。我近前一看,只见儿子一手拿着锤子,另一只手捏着钳子,儿子为了不让锤子砸着手,用钳子夹住钉子,正一下一下往板凳里砸钉子。那一瞬间,我为儿子的聪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儿子小小的年纪就非常讲究条理。他骑的童车,总喜欢固定摆放在一个地方,头南尾北,倘若谁哪天改变了这个位置,他就会不顾
一切地纠缠,直至把童车错误的方向再改变过来!
因此,儿子的认真,有时就让我觉得有些任性,使我感到丝丝不快。儿子的某种思想没得到我们的认可,或是我们根本忽略了儿子的所思所想——这时的儿子,就会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直至我们七哄八逗,他才从地上慢慢爬起来。
瞅着满身灰土的儿子,有年长的老人就戏谑地对我说道:“真是不愧为遗传!不用学,你儿子就把你从小的模样又捡回来了!你肯定不记得了,从小有人一旦逗弄了你,你就会一下子倒在地上,啥时不哄劝,啥时不起来……”
当人们说这话时,我只感到心头热热的,似乎儿子的举动,一下子又拉近了我和童年的距离。我这才真切地感知什么叫“遗传”。有人只在乎遗传的结果,却没有人检点一下遗传的“基因”。这一生,我不指望给儿子传下百万财产,但我要做一位普普通通的好人。做好人是一笔财富。
儿子,愿你的身上遗传着这个吉祥的字眼!
错过今生一段美丽的缘
我做梦也没想到,因为搞文学创作,今生还会欠下别人一段情债。
那是1999年3月的某一天,正是杨花吐絮、春绽枝头的季节。
凌晨4点的时候,我忽然被一阵电话铃声搅醒。朦胧中,睁开惺忪睡眼,抓起话筒,耳边传来一位女孩儿的声音。
我问:“你是谁?”
女孩儿说:“我是洁。我是安徽天长市的洁。我是你的忠实读者。我在《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上读过你的不少作品。”
我说:“哦,洁,你好!请问你咋这时候给我打来电话?”
洁说:“我想专程去看看你。我已乘坐了一天一夜的车,现在下车到了你们的县城,但我不知道如何去你们的小镇。”
我说:“你就在农业大厦下面等着我,40分钟之后我过去接你!”
我又简单交代了洁几句,便乘上了去县城的过路班车。
我原想相距60里路的县城,坐车最多需要40分钟就到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班车在半路上抛了锚。为了不让到手的生意“得而复失”,售票员好说歹说,千方百计挽留每一位乘客,不让我们下车。等车修好了,赶到了县城,早过了约定时间。这时我在农业大厦下面,左寻右找都不见洁的踪影。那一瞬间,我对洁的不见作了种种猜测。是洁长久不见我来,到附近的商场转悠去了?但这似乎不大可能。一个女孩儿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又一天一夜没有阖眼,根本没有这份闲情雅致。那么,是洁久等不见我去,受了冷落,一气之下又坐车回去了?可她明明是来看望我的,既然是来看望我,又不辞而别,岂不虚了此行?——那么,是洁看见有开往我们小镇的班车,独自一人毅然踏上了去我们小镇的路?但这又仿佛不成立。洁在电话里明明让我去接她,怎么又会擅自改变主张呢?洁会不会住进了旅社?但这似乎也不大可能。要住旅社早住下了。洁在电话里明确表示,只想尽快赶到我的家。那个上午,我在县城的农业大厦下,等侍、徘徊、找寻了洁许久。我把目光专注地投放在每一个行人身上,篦子一样,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篦来篦去。我生怕错过每一个眼神,和洁失之交臂。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为别的,只为自己的一篇小文章,就感动了一位女孩儿隔山隔水来看我,实在不易。茫茫人海,相识相知也是一种美丽的缘吧。接电话的那一刻,我差点没为女孩儿的大胆行为而感动得热泪盈眶了!
那个上午,我在县城的农业大厦下,足足等了洁两个小时。后来,没吃早餐的我,不得不拖着饥肠辘辘的身子,怏怏而归。
走到家,妻子告诉我,洁在农业大厦下没见到我,后来就住进了旅社,在这中间洁给家里打了几次电话,妻子都告诉她,我早就到县城接她去了!
当我又一次赶到县城,果然找到了洁下榻的银河旅社。不过那时洁已退了房间,独自一人又踏上了开往安徽的班车。
总台的服务小姐指着旅客住宿登记薄,不无惋惜地说:“这位小姐正是你要找的那位!你早来一步就好了,她刚刚走了不到十分钟。这位小姐十七八岁,蓄着学生短发,牛仔裤,白褂子,背着一个坤包。登记房间不到半小时,又要求退房。当时我们看她眼睛哭得红红的,以为她遇到了什么困难,让她告诉我们,我们说要尽力帮助她。她说她来见一位朋友,结果没见着。退了房间,我们看她边抹泪,边朝车站的方向走了……”
谢过服务小姐,我赶忙又奔向车站,可是开往安徽的那趟班车早已发车了。那一瞬间,我呆呆地立在车站里,失意万分,对于洁的不辞而别,我作了种种猜测。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洁把我晚去接她的原因看成是有意躲避。
后来我想着法子和洁取得联系,都不见洁回音。洁单位的人告诉我,洁早辞职到了南京的一家公司,具体什么地址,谁也说不清。
我想和洁的这段一面之缘,怕是永远再也续接不上了。
生命无常
侄女的死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一种宿命的色彩。
侄女死于何年何月何日已记不清楚了。只依稀记得侄女的死与大嫂有关。那时的大嫂动辄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大哥大吵大闹,往往把大哥骂得狗血喷头,大哥还得待在一边噤声不吭。倘若大哥惹怒了大嫂,大嫂就詈骂不绝,几天躺在床上任大哥哄劝。俗话说骄兵必败。正因为大嫂的骄气恣肆,后来才葬送了侄女的一生。
侄女死的那年已有十七八岁了。记不清因为什么事,大哥和大嫂吵了嘴。吵嘴之后的大嫂,几天不吃不喝,侄女几次劝她,都遭到大嫂的不理不睬。
侄女:“妈,你和爸吵嘴,其实根本不怨爸。”
大嫂:“我就知道你们父女是一条心!——你甭喊我‘妈’!我不是你妈,你妈早已死了!”
侄女:“让你死还不如让我死!”
侄女后来又劝了大嫂几次,大嫂仍是不听。
侄女就在秋天的那个下午喝了有机磷农药。没喝农药之前,谁也没看出侄女异常。侄女在遭到大嫂的呵斥后,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小屋里睡了一个下午。侄女后来就喝了农药。侄女喝了农药后,还爬到她家的平房顶上帮我父亲捶了一会儿豆荚。
侄女边捶豆荚,边泪水婆娑地对我父亲说:“爷,你回头把我爸和我妈好好劝劝,别让他们再吵嘴了……”
侄女说这话时已“扑通”一声栽下了房顶。
事后,我老眼昏花的父亲回忆说,他当时实在没看清我侄女是一脚踏空栽下去的,还是侄女有意跳下去的?据我分析,侄女喝下的有机磷农药,那时正好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