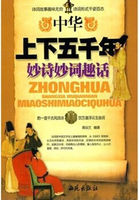【品评】
此文作于宋绍兴二年(1132)十月。李清照于此启中真实地反思了于赵明诚逝世三年后误嫁张汝舟的教训,并表达了对綦崇礼感恩戴德的由衷之言。
关于李清照于49岁时改嫁张汝舟一事,于宋绍兴年间李清照去世后不久,即有记载。如宋胡仔云:“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苕溪渔隐丛话前编》卷十六)宋王灼说李因“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碧鸡漫志》卷二),不一而足。宋赵彦卫则更于《云麓漫钞》卷十四抄录清照《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可见李清照晚年改嫁乃是不争的事实,当然由于封建传统观念作祟,清照改嫁之事又被讥为“传者不无笑之”(宋胡仔,同上),“晚年颇失节”(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晚节流荡无归”(王灼,同上),云云。而明、清文人却多怀疑清照改嫁的真实性,竭力辩解此事乃无中生有。这固然有爱惜人才的因素,但也是封建保守观念的另一种反映。如明徐煳认为清照此启“殊谬妄不可信”,认为李“老矣,清献公(按,当为清宪公)之妇,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乃“太诬贤媛也”(《徐氏笔精》卷七),就是颇具代表性的说法。又如清俞正燮云:“读《云麓漫钞》所载《谢綦崇礼启》文笔劣下,中杂有佳语,定是窜改本……余素恶易安改嫁张汝舟之说,雅雨堂刻《<金石录)序》,以情度易安不当有此事。”(《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诸如此类的辩解之词甚夥。其出发点自然有好心的一面,但称“易安改嫁,千古厚诬”(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书后》),只是感情用事,并无翔实的证据。
本启第一段主要是陈述误嫁张汝舟的原因,记叙上当受骗的来龙去脉,充满“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意。开头以“素习义方,粗明《诗》、《礼》”自许,含有自我辩白的味道,似乎说此事本不该发生,与自己素来的品性、学养不符。接下把“失足”原因归结为客观:一是病几入膏肓,使自己头脑发昏,理智不清;二是受弱弟影响,而弱弟实被张汝舟欺骗;三则是最重要的,张汝舟此人巧舌如簧,善于伪装,自己一时未能识破。因此虽然自己亦曾犹豫莫决,但最后还是糊里糊涂与张“同归”,以致造成“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才”的悲剧。清照婉转述说,哀哀动人,意在博得对方的同情与理解。而言词中隐然可感清照羞愧啮心之态,这又反映了一代才女此时强烈的自尊心。
第二段记述自己婚后的悲惨境况,意在表明自己坚决与张汝舟离婚的原因,并向帮助自己实现离婚愿望的綦崇礼表白感激之情与崇敬之意。由于张汝舟之娶李清照,意在谋夺其珍宝之物,但婚后发现其企图落空,于是原形毕露,大打出手,令清照饱尝“老拳”。两人本无感情,又遭殴击,这就道出清照必欲与其分道扬镳的原因。李清照为达到与张汝舟离婚的目的,乃采取控告“其妄增举数人”之“私罪”而得以人官的策略。但文中对此并未明说,甚至没有点出“张汝舟”一个字,此乃囿于“地告天”即妻告夫亦属犯上的忌讳而有意回避。这是文章的聪明之处。对于自己与张汝舟同堂受审、共关一狱的遭遇,李清照愤愤不平,连用两个典故形容自己羞耻之感,可见对张不共戴天之恨。最后由于綦崇礼的暗中帮助,使皇帝亲自过问此事,下诏将张汝舟罢官除名,流放到柳州编管,而清照与张的婚姻关系亦被解除,且免除坐牢之灾,綦崇礼真是鸿恩无量。故此启对綦说了些赞美之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亦是发自内心的。但清照对自己名誉十分看重,在感激綦“如真出己”之馀,仍期盼綦崇礼以“智者之言”“止无根之谤”,再为自己说些好话。
第三段是本启的小结性文字。一是再次强调自己与张汝舟水火不容,意在说明与张离婚的合理性;二是再申请綦为自己“湔洗”耻辱之恳求;三是表白此后将吸取教训,安度馀生,并铭记綦氏之鸿恩。
此文一个鲜明特点是感情色彩强烈,特别是对张汝舟的不齿与愤恨,充溢字里行间;对綦崇礼的感激与崇敬亦发自肺腑。语言则文采斐然,颇多四六对偶句式,对仗工整,言简意赅,叉富音韵铿锵之美。读完此文,觉一个受尽屈辱而又不失自尊的坚强才女形象栩栩如生。
4.《金石录》后序①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②取上自三代,③下迄五季,④钟、鼎、觑、鬲、盘、匜、樽、敦之款识,⑤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⑥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⑦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⑧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⑨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⑩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已,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疏衣缲,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邪?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馀。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虽处忧患贫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惨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别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栽,乃先弃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馀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馀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茈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馀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得活,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馀遂牢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邪!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邪?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人间邪?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