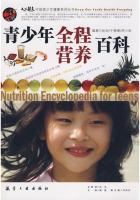在这一事件上,国家公器及科学本身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由此被唤醒,禁止使用高毒性杀虫剂和除草剂的呼声在美国此起彼伏。——那些反对的、攻击的和捍卫某种利益的声音从此偃旗息鼓。这时候,人们不得不承认,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现实:“每个人从胎儿未出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的。”尽管如此,化学农药仍旧在森林、牧场、城市和乡村被广泛使用,遍及每个角落。因此造成的昆虫、野生动物及家畜、人的各种灭绝和疾病一再爆发或卷土重来,且有不少的新的疾病,在世界各地如同幽灵一般隐匿和流行。农药不仅危害了现有的大自然自身的防御和平衡能力,且对人、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基因和染色体构成了致命影响——人类及地球所有生命都面临着不育不孕、甚至会亡族灭种的危险。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阿尔·戈尔)蕾切尔·卡逊以严谨详实的科学论据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普世主义精神,证实了她发现和说出的“农药对大自然及其生命的污染是致命的,且影响到了这个世界所有生命的健康与安全”;今天的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自然破坏、疾病、灾难和灭绝景观,好像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命运——因为我们做了,就必须要做好承受的准备。蕾切尔打开的是上万年以来人类思想意识当中,另外一条从未有过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往是人类的明天与地球及其所有生物的命运前景,矫正了人类“人定胜天”、“控制自然”等愚昧意识和人类长期以自我为中心的狂妄思想。——“蕾切尔·卡逊是一位现实的、收到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并且秉有一位诗人的洞察力和敏感。她不后悔对自然做了一次有感情的回应。她知之愈多,她称为“惊异的感觉”就生长得愈多。正因为此,她成功地将一本论述死亡的书变成了一阕生命的颂歌。”(保罗·布洛克斯)
蕾切尔说:“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世界如果真的像蕾切尔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说的那样:“当天空不再是蓝色,小鸟不会飞翔;当江河不再有清澈,鱼儿也离开家乡;当空气不再是清新,花朵也失去芬芳;当乌云遮住了太阳,世界将黯淡无光;当冰山逐渐融化,地球是一片汪洋;当城市的车川流不息,从此没有一点安详。”作为其中一个,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子孙又该当如何?由此,《寂静的春天》意义还在于,环境问题的根植于更深层次的人类生活和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要促使人们改变以往的信仰和思想,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这个理念,在当时世界各国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1962年,美国国内已有40个提案,要求在各地限制使用杀虫剂。1964年4月14日,一生未嫁的蕾切尔·卡逊在马里兰去世,享年57岁。人们将她葬在大海边,并朗诵了她的《在海边》最后一章,以使这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开启新时代的伟大女士灵魂得安。——“无论是谁,最终万物归于大海——海洋之神。入海的河流,就像流水般的光阴,开始,结束。”43年后,美国一位副总统说:“她(蕾切尔)的照片和那些政治领导人——那些总统们和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它已经在那里许多年了,它属于那里。卡逊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阿尔·戈尔)
说明:
1.文中引文分别出自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李长生、吕瑞兰译)、琳达·利尔《蕾切尔·卡逊:自然的见证人》及克林顿政府副总统阿尔·戈尔为《寂静的春天》一书再版所写的序言。
2.本文为《<寂静的春天>导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一书所作的人物生平介绍。
暗恋李清照
我常常在梦里,想起或者梦到一个女子,她的叹息从窗外的花枝和露珠上传来,在现代的玻璃窗上,像麻雀啄食。那时候,宋朝的北方是繁华的,到处都是酒肆、妓馆、丝绸、驻扎山头的禁军。叫卖声和旅客的马蹄声在青石的街道上此起彼伏,交相呼应。写词和弹琵琶的人在挂着红色灯笼的阁楼上,有人醉眼惺忪,有人弹铗而歌,有人在人的怀里卧倒,有人在低矮的屋檐下看着对面的朱漆大门。
那个时候,我该是什么呢?清照的一根长发,或者她用过的一张宣纸或者一只毛笔。在她那里,我是无意的,她攥住或者铺展,在她内心的墨迹和皱褶的抒写当中,我是沉醉的,没有意识的,我只是一个物质,没有灵性也没有多少生命。往往,她用过了,就扔掉,或者无意间掉落在泥泞的地上,她和他们踩来踩去,我就深陷下去,不能自拔也不求自拔。有时候,她会把我揉做一团,冲着后窗的芦苇和青草——我弹跳出去,在阳光下干燥,在雨天腐烂,在火焰之中,呈现灰烬的容颜。
而我仍旧是沉醉的。一个旷古的女子那里——在这个尘世上,我再也不会找到比清照的身边更为合适和幸福的地方了。清照年轻的时候——好玩的女孩子,在花园、竹林和小儿呼啸的池塘边儿,夏天的蝴蝶,秋天的蜻蜓;春天的花朵在青草中间,浓妆艳抹,香气盈面;很多的鸟儿在树枝和绿叶之间飞纵鸣啾。薄暮黄昏或者清凉早晨,她也喜欢到村后的竹林和槐林里去玩,坐在岩石上吹箫,在随风而响的竹叶中唱着自己写的歌。她的笑在夕阳中是两只蹁跹的蝴蝶,她握住花朵,听见她们的欢笑和呻吟;她看着东边的树影,想到时光和过客。她喜欢在花园里面打秋千,一边咯咯笑着,她和婢女一起玩耍,在清凉的晨风和晚风中,揽镜自照,用象牙的梳子梳理长发,用修长的纤细手指轻粘脂粉。她散开的云鬓和裸露的胸口之中,兰花的香气凭空而来。
我依稀记得,赵明诚迎娶她的那天,早上下了一阵小雨。房檐的雨滴一下一下地,打在青色的石头上。或许是天长日久的缘故,那些石头上都被雨滴砸出了深深浅浅的凹槽。有一些蚂蚁死在里面,有一些尘土落下又被洗净。不一会儿,乌云散开,太阳出来了。锣鼓和花轿,唢呐和长笛,在李家深深的院落和外面的青色巷道里,吹动了整个宋朝的清晨,也吹动了整个宋朝内心最为隐秘的情感。我就站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上,任由迎娶她的脚步踩来踩去。她的花轿刚刚出了大门,东边的天空出现了一群巨大的鸟群,它们嗓音婉转,羽毛漂亮,不一会儿,就遮住了半个天空。
那些鸟儿比我幸运——它们随着清照,穿街过巷,一直跟随到赵家的深宅大院,甚至还在他家的屋顶上,集体落下来,直到客尽灯灭,清照和明诚在洞房之内卿卿我我。那个夜晚刚好还有月亮,不过不是满月,而是稍微残缺的下弦月。我记得,在彻夜笙歌的宋朝,月亮下面的人和事物都沉静的,没有人去感怀旧事,也没有人在半夜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尽管西边的天空中时常升起狼烟,军队的刀戈和马蹄在风中扬起尘土,战乱的痕迹和征兆如同梦魇一般。可是再莽撞的人也不会惊扰一个幸福的女人。在明诚那里,是清照一生最幸福的时光了。金石本来就是一种坚硬的象征,而一个女人的柔情和绝世的才华一种浸染和加强。
明诚出门久了,清照就慵懒起来,总是日上三竿,竹影拍窗之后,她才缓缓而起,坐在花香充溢的房间,轻舒四肢,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自己的容颜。小鸟在门外叫着,蹦蹦跳跳。午后的太阳在房脊上摇响风铃。她端坐窗前,或者园中凉亭,看燕飞燕去,天上云卷云舒,蓝得令人轻盈的天空——众多蔫去的树叶和青草,成团的花朵被蜜蜂和蝴蝶围困。她信手落墨,欢笑作歌,惆怅为词,一点一点的墨痕,一个一个的汉字,每一颗都触动着这个世界的内在肝肠。有时候,她一个人在黄昏把酒,在花间,嗅着一波一波的暗香,静夜缓慢如钟,蛙声在临近的水波中荡漾。大地何其安静呀,连绵的城郊千户无声,吹送的清风拂眠如掌。清照额发掩眸,偶叹东风,说人比黄花瘦。
宋朝崩塌了,在蒙古和金兵的铁蹄下,半壁江山风雨飘摇。仓皇南下的船只和行人,北方的萧条在离散的悲痛中显示出了一个王朝在时间之中的废墟模样。清照也跟着众人的脚步,向南而去,一路上颠沛流离,从健康而台州,由台州而杭州。宋王朝的宫阙和街道上到处狼藉。清照看清了这世间不停的这兴旺交替,而她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看清自己,乃至近在咫尺的个人遭际命运。是的,这世间暗藏了太多的厄难和轻忽的变迁。明诚死了,对清照来说,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心疼和绝望。我知道从此以后,清照再也不是从前的清照了。一个幸福中的女人,什么都可以瞬间消失乃至强行剥夺,而最不可失去的就是她一生依傍和珍爱的男人。
清水洋溢,花枝招展的李清照一下子枯了。她最不可或缺的不是那些为她赢得万世声名的文字,而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爱和绝望。后来那个娶她的男人,我始终没有记住他的名字——直到现在,我也不愿意去这里那里翻检他的名字——对于清照和后世的人们来说,那个男人的名字和意义已经随着肉体的腐烂而腐烂了,再有一万年的时光,也不会再有一丝响应。
在杭州的那些年,南宋的光景就是李清照的生活背景,也是她内心的形式和颜色。日复一日,彻骨悲凉。四顾无人,李清照只能顾影自怜,在落花。碎泥。残爪和流离多变的个人遭际中,偶尔掀开昔日的梦境,在连续吹过心灵的风中,看见一世的虚妄、败坏和苍凉。多少个黑夜,她独身不眠;在漆黑的午夜,用自己抱紧自己。时常一个人坐在锈迹斑斑的铜镜前,看自己满面深纵的皱纹,看青丝成雪,云鬓摇霜。那么多的忧愁与怅惘该向何人排遣?莽苍苍的大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究竟有那一只肩膀可以将一个年衰的天才像孩子一样抱紧?没有的,那时候,清照就看到这繁华世界背后的荒凉。她总是一个人在旧漆剥落的门楣前,望着北回的大雁,珠泪婆娑,寸断肝肠。她把酒黄昏,把宋朝的所有阑干拍遍,或者登高望远,而回过身来,偌大的尘世之上,到处都是繁华烟柳。而晚年的李清照却通体冰凉,连一颗曾经蓬勃的心脏,也冻疮斑斑。孤独的门楣之前,行人匆匆,车马冷落,回忆的昨日欢笑都如一阵轻浮的烟岚。在孤独的酒杯之中,雨疏风骤,清照浑然不知今夕何年,只是一人独坐夕阳,只道“风住尘香花已尽,物是人非事事休。”
清照竟浑然不觉,她使用过的那些朱笔和宣纸竟然暗恋她那么多年。而物质只是物质,怎么能生出人类的躯体和情感呢?当清照吟出“感风吟月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的时候,我就在她的身边,她的眼泪已很浑浊了,一滴一滴,也不怎么连贯,落在我身上,慢慢渗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知道,多少年之后,我将以清照的这些眼泪,在时光中流传千年。
有一年冬天,我随着一阵持续的大风,从烟雨江南回到北方,在清照和明诚的旧居前,我以一只朽烂了的朱笔,一张破碎的纸张的模样,站在旧朝的废墟上,在倒塌的墙垣和石砾之间,仿佛嗅到了清照当年的体香。在夜晚的唧唧虫鸣之中,听到了她的呻吟和欢笑。李清照死的那年,我站在北方的高冈之上,遥望烟柳江南,猛然觉得内心锥疼——我知道,它是不灭的,它必将要持续千年。而千年——又似乎转眼之间,迅即之中,李清照以自己的那些传世华章,打败了总在泯灭一切的时间。她本人的一副香骨玉魂,也总在尘世和人类的内心隐秘的高贵部位斗折留恋。而今,我百转千回,终于脱胎成人。这么多年来,在偌大的土地之上,在匆匆的行走中,我一次又一次看见了众多似曾相识的面孔,而唯独不见当年的李清照。
其实我们没有好好爱自己
她得了癌症,卧病在床,总是喜欢和来看她的人说起“当年”,她提到了如何到深山躲避鬼子的扫荡、与村子里某个家族抑或个人的恩怨纠纷、如何在生产队挣工分、在大食堂吃大锅饭,还有她一生遭遇的那些在别人听来索然无味的日常琐事。上年纪的人喜欢听她絮叨,或坐在她充满霉味的土炕边上,看着她只剩下两张皮的嘴唇,持续不断在白天和夜晚张合。年轻人则厌倦不堪,常常借故走开。
有时她会笑出声来,有时候则流出眼泪,更多的是叹息。她苍老而微弱的声音像是从岩层下面发出来,幽幽的,嘶哑的。临死那天晚上,她把儿女们都叫来,看着被烟火熏黑的屋顶,不断说出她自己或家庭的陈年往事。其中夹杂了不少感叹,既有对个人和他人生命的,也有对自己整个家庭的,有自身的悔恨,也有对他人的褒贬。咽气时,她先笑了一下,然后长长叹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