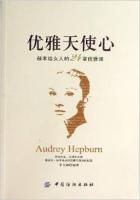李存葆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难道自己真的要从ABC学起?但宽厚的李存葆还是说,莫言同志可以再读一读,这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作品,结果这个作品拿了当年的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的头奖。莫言则因为自己的少年轻狂被所有人盯着,看他能写出什么作品来,写不出来,当然就会成为笑柄。他就憋着一口气,因为自己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要用作品来证明自己。这以后他写了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白狗秋千架》等作品,而李存葆好像再也没写过小说,转写报告文学、散文,并在莫言写出《白狗秋千架》的时候说,这个小子还是有点造化的。单凭这句话,李存葆就是有胸怀的大男人。后来,莫言说自己一直想和李存葆恢复关系,莫言和李存葆的事情在文坛传的很广,莫言后悔了,觉得自己很幼稚,没有城府,更不应该轻狂自大。
其实,进入文学系的时候,有很多同学瞧不起这个仅仅发表过几篇文章的乡下少年,他的一篇作业《天马行空》就是因为看不惯班里很多同学的傲慢所写的。在军艺的文学院里,傲慢也是常态,因为这里集中了全军最优秀的人才,李存葆就不必说了,还有南京军区报告文学作家,凭《唐山大地震》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的钱钢,莫言根本就不算什么。据同学黄献国回忆,开学后不久,徐老师向大家推荐《民间音乐》,班里就有人问:
“作者是什么人?”有人开玩笑说:“就是咱班眼睛老睁不开的那个。”
因此,大多数时间,莫言在班里很低调,坐在教室南边靠窗的一个角落里,不怎么说话,发言也不积极,讨论也不太参与。但他从来不缺课,也不像有些同学故作高深地读书看报,或者大声咳嗽,或者很悲壮地愤然离席,以显示自己比老师的学问还高。莫言用他的谦虚来告诉所有人,低调是对付浮躁最好的方式。
2
军艺的学员宿舍是四人间,莫言和崔京生、施放一个寝室。有的寝室里,为了不相互干扰,大家都拉上了帷幔,各自为营,走进去有点像迷宫,可莫言的宿舍比较懒,不勤奋写作,还一派清清爽爽。那时候,天气冷,暖气不热,房间里都能结冰,刘毅然说,他每次去莫言宿舍,都看到其他人在侃大山,而莫言则趴在桌子上写他的小说,他还可以随时站起来回应,随后又坐下来接着写,他的手稿大多是一气呵成,很少涂改的。有时候,莫言无法安静地写作,就在文学系的阶梯教室里写,当时军艺正大修大建,四处都是泥浆黄土,相当的接地气,有利于写“高密东北乡”的小说,所以莫言的灵感迸发。
同学刘新增说,那时候莫言一天最快写一万字,他最喜欢莫言的《爆炸》,因为父亲要打儿子,一巴掌写了3000字,真心佩服莫言的语言能力和夸张能力。莫言有段时间要听着音乐才有灵感,喜欢听艾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边听边流泪,还说里面一定有痛苦的爱情。曾任《人民文学》编辑的朱伟在文中提到,莫言那时候借了一间教员宿舍专门写作——
晚上在大家睡觉前夹着书本稿子出去,天亮再毫无倦意地回来,由此他是军艺那种16开500字薄薄的绿格子稿纸最多的消耗者。军艺当时的稿纸分配是有数的,他过多的消耗,只能从他的好朋友刘毅然那里去要。
刘毅然是莫言他们的影像课老师,常常放一些不错的电影,他的家也成为莫言这帮朋友聚会之地,比如改善伙食吃点红烧肉,比如喝酒闹腾闹腾。
朱伟还提到:
从1985到1986年底,我骑着一辆凤凰牌破自行车,就这样经常跑军艺,莫言当然是我最重要的追踪目标。他给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是《爆炸》,他交给我的是特别干净的稿子,每一字都写得方方正正,字体扁而几乎一致,其间几乎没有涂改。偶尔增加的句子,都会清楚地标示,一如他整洁的床铺。莫言写作,是不打草稿的,崔京生说,他在开笔前只是在一张纸上列出顺序、交叉、拐弯抹角处,然后就开始动笔,基本一字不改。在停下来思考的时,除了抽烟,还会用一把已经磨得亮亮的小梳子梳理其实不多的头发。他是极注重整洁的,但很朴素,永远是穿着衬衫的样子,天冷了就加件夹克。尽管有时也会挺直腰板,但我却总难有他穿着军服的印象。他真的不是一个军人坯子。
3
莫言后来感慨道:
“这一时期收获很大,方知文学是怎么回事,决心搞出一点名堂来。那时写作似乎已经成癖,一天不写东西,感到对不住自己,创作欲极强。”
写作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到了半夜,饿了,就用“热得快”烧水煮泡面吃。方便面是个好东西,学校伙食差,吃饭还要排队,喧闹如集市,在宿舍里煮面则自由多了,学校里禁查电炉,可是屡禁不止,莫言还买了二两虾皮,煮面的时候放上两粒,鲜美无比,吃过莫言面的人,都称赞不已,那时候,莫言以为方便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面本来是两毛钱一包,后来涨到了两毛五,因为怕涨价,莫言就一次性买回了50包,放在床底下的旅行袋子里。
深夜两点,文学系还是灯火通明,隔壁的李本深就用勺子敲着铁碗在楼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有人把文学系宿舍称作“造币车间”,因为通过写小说,有的同学写成了万元户,而莫言就是头号“造币机”,因为在军艺的两年里,尽管白天要上课,莫言还是写出了80多万字的小说。还有传闻,每天晚上,同学们有的外出访亲探友,有的喝酒侃大山,有的看书,只有莫言,躲在教室里一写就写到凌晨2、3时。当时不排除有人背后讥讽:这能成吗?
莫言很快就开始爆发了。从1985年开始,他陆续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枯河》、《秋水》、《三匹马》《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石磨》、《红高粱》等。国内文学界到处在打听:谁是莫言?他是干什么的?当知道莫言是军艺文学系的学生时,许多杂志的编辑,以及文学爱好者,都跑来狭窄的宿舍,找他约稿,探讨文学。他只得躲起来。1986年,著名作家张洁应邀来军艺上课,她说她刚从法国回来,外国的作家问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她说,出现了莫言。
莫言后来回忆说,离开军艺之后,自己再也找不到那种在军艺看书写作的感觉了,尽管那时候军艺条件差,到了冬天脚上会生冻疮,洗澡也只能一星期洗一次,数百人争抢十几个莲蓬头,但大家都摽着一股劲儿,即便是平时嘻嘻哈哈,到了相互评作品的时候,也会严肃起来。
只要跟莫言熟悉了,就会发现这个同志不只会沉默寡言,还时不时一鸣惊人。刘毅然说,有次系里联欢会上,莫言和崔京生反穿着雨衣推自行车上台,身上贴着方便面,手挥舞着用卫生纸做的宝刀,嘴巴依依呀呀唱着不知名的调子,颇有些后来《红高粱》电影中“我爷爷”的味道。同学们很惊讶,同时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莫言,聪明、机智、幽默、充满了想象力。
外出体验生活时,莫言讲起故事来就是个话唠。有次莫言和刘毅然一起做火车卧铺去新疆,莫言讲的故事,像是野史又像是家史,他讲完了,自语这是个中篇小说,结果就有了小说《奇死》。莫言的很多小说都是给刘毅然讲故事的时候产生构思的,这种方式其实就是蒲松龄把听来的故事变成《聊斋志异》的过程,只不过在学习这位祖师爷的时候,莫言“青出于蓝”啦,他可以边讲故事,边记忆,故事成了他的素材。
学无止境
1986年,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莫言利用等待分配工作的时间,讨个安静,继续“爬格子写稿”,后来被分配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工作。1989年11月,尽管1986年创作的《红高粱》已经获奖无数,但部队还是给了这作品“首届总参文艺奖”。孙毅老将军为他颁奖,莫言也因此荣立二等功一次。莫言在总参政治部文化部期间,写了报告文学《一夜风流》(1991)、《千万里追寻着你》(1994)和《水中之鱼》(1997),以及电视剧本《神圣的军旗》(1991)等作品。
1
关于《千万里追寻着你》,这篇报告文学是由孙毅老将军题写的标题,发表于1994年7月7日《解放军报》的“长征”副刊,后以全票获得全军“庆祝建国45周年国防现代化报告文学征文”优秀作品奖。那年6月,为了撰写这篇报告文学,莫言和同事杨永革、周余霖一起去了西安近郊某地,这里的通信团是他们采访的对象,他们去陕北采风。
莫言在这次采风中,并不莫言,他先是跟路边的一位老人闲聊,关于白水雷牙哨所的战士,老人说:知道,那两个娃,有名得很,连我们县委书记都去给他们送金匾哩!在这次采访中,宋杰是山东莱阳人,莫言看到他的相册,说“咱俩是老乡,我是高密人。”。晚上一起吃饭,有个小女孩用地道的河南话说她吃饱了,莫言还站起来为她和她父母高歌一曲《九月九》。
后来,全军和总参文艺创作座谈会相继召开,总参成立了电视艺术中心,准备把解放军军事五项队的事迹拍成电视剧,莫言负责剧本创作。他换上迷彩服,到八一军体大队体验生活,采访写作,半个月后拿出了四集电视剧《神圣的军旗》,这部电视剧在中央一套播出,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宁海强导演执导,荣获了“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不少的地方男女青年看了片子纷纷给莫言写信,想托他去当兵,为国争光。
1991年夏天,南京市六合县新集乡滁河大堤决口,5米多高的洪峰,咆哮着扑出堤外,莫言则身穿迷彩服和战士们并肩作战,并根据此事写了报告文学《一夜风流》,发表于《解放军报》1991年11月19日的“长征副刊”上,并荣获当年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金奖。后来,莫言说:
“我经常想起战士们忘我救人的景象,这就是我们军人爱祖国爱人民的最好表现。这样的爱孕育的军队,什么样的敌人都能战胜!”
此外,关于抗洪的另一篇文章《水中之鱼》,发表于1997年2月20日《解放军报》上,作品用“你”来抒发感情,主人公张金垠幻化成一条鱼,是一种童话式人性回归和还原。
2
莫言的上学梦还在继续。1988年8月,莫言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第一届作家研究生班,由北师大授予文学硕士学位,学制原本两年,但由于1989的缘故,延迟到1991年才结束。据何镇邦的文章介绍:
一九八八年七月至八月,研究生班的招生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全国各地八十多名创作上颇有成绩的青年作家报名。……入学通知是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发出的。加上同年十二月补充招生录取的几名学员,共有四十余名进入预备班学习,他们是:
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王刚、严歌苓、肖亦农、邓九刚、路远、刘毅然、宫魁斌、李沙青、李本深、刘亚伟、张坚军、王连生、季清荣、刘恪、毕淑敏、冯敬兰、江灏、雷建政、王宏甲、简宁、李平易、黄康俊、王树增、魏志远、彭维超、海男、洪峰、何首乌、陈虹、白冰、寇宗鄂、李秀珊、蔚江、于劲、王明义、千华、岛子、贺平、黄殿琴、孙大海、徐星、贝奇、叶文福、芳洲等等。
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预备班是于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的,经过四个月的学习,开设了政治、文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等辅导课,……入学考试的科目正是上述辅导课的相应科目,只是写作是限时命题作文,当场完卷,记得写的是每人的创作自述,参加考试的各位开玩笑说:“为了进入研究生班,把自己的家底子都卖了!”我在判阅这些试卷时,也常忍俊不禁,当然也因此加深了对各位青年作家的了解。
据贝奇女士的回忆,她能记住的同学是:
蔚江、江灏、海男、萌娘、严歌苓、千华、黄殿琴、迟子建、陈虹、毕淑敏、冯敬兰、于劲、孙大梅、沙青、洪峰、叶文福、王明义、邓久刚、余华、莫言、王宏甲、王刚、白冰、刘恪、路远、徐星、何首乌、寇宗鄂、简宁、彭继超、黄康俊、刘亚伟、刘毅然、刘震云、王树增、沙林、岛子、王宁生、刘以林、杨新民、雷建政、肖亦农、严啸建、魏志远、季清荣、李本深、班长宫魁兵。
还记得老师有:唐因、周艾若、何镇邦、冯立三、童庆炳、王愿坚、鲍昌、唐达成、张契、李国文、林斤澜、孙津、文怀沙、谢冕。
莫言跟余华是一个寝室的,余华的夫人陈虹也在研究生班里,我后来觉得怀疑余华《活着》里福贵的命运,也就是赌博赌光了家产反而捡回一条命,就是莫言无意中讲的。因为当时两个人在同一个宿舍,不“卧谈”吗?况且,莫言写好了《酒国》还托余华拿去给浙江的一家大刊物,看看能否发表,因为余华那时候在浙江嘉兴编《烟雨楼》,可惜人家那编辑说了:
“这样的小说我们怎么可能发表呢?”
过了几年,《酒国》才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莫言获奖后,迟子建在微博中说:
二十三年前,我与莫言同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有天放映内部电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莫言见我进来,非常严肃地对同学说,迟子建还是儿童团的,不能让他看!同学们都笑。莫言获得诺奖,让我们这些同学,得以在不同的地方,获得了与二十年前一样的愉悦心境!这个夜晚的绚丽属于莫言,祝贺师兄!
严歌苓在谈到同学莫言的时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