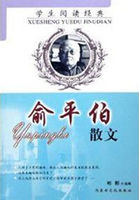扇动
蜻蜓飞进的这间教室正在进行着一堂公开课。这是一堂很重要的公开课,它关系着将由谁去参加县上组织的“课堂教学竞赛”。名额只有一个,报名者却很多,每个人都想让这唯一的名额落到自己头上。每个人都明白,一旦能到县里上课,就有可能获得领导更多的青睐,甚至因此改变一生的命运。对于一个在如此艰苦的乡村学校默默无闻教书的乡村老师来说,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
这唯一名额给谁呢?学校领导揣着这事也很犯难,为了能够尽量公平,不出怨言,他们组织了这次“选拔赛”。从“选拔赛”的通知发出到现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小余老师都在积极地做着准备。她钻研教材,查阅资料,备课,上课,修改,再备课,再上课,再修改。她把她所教的班级作了她的实验场,让孩子们和她不断地咀嚼那一张别有滋味的馍。同时她还请那些教学经验丰富的,尤其是有可能成为“选拔赛”评委的老师给她提意见。她把姿态放低,做一副虚心好学的模样,实际也在套取着这些老师的经验,捕捉他们的“兴奋点”。她因此找到了一些可以获取高分的办法,比如多笑多动,打情感牌;比如使用教具,幻灯,多媒体,打科技牌(这些洋玩意不管对她所要执教的那堂课是否有用,但至少它对那些于现代化教学手段不甚了了的评委们的震慑是巨大的)。可以这么说,在所有报名参赛的选手中,小余老师的准备工作是做得最充分的;甚至比赛还没有开始,就有人预言,比赛只是例行公事,走走过场,它对小余老师获得那唯一名额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影响了。
不错,蜻蜓飞进的这堂课,正是由小余老师来执教的。小余老师已经上完课的前半节。应该说,无论从课堂效果,临场发挥,还是学生反应,这前半节都是相当不错的。事情正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可就在这时候,一只蜻蜓飞进来了。蜻蜓是从打开的窗户飞进来的。这是小余老师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件。课前小余老师想过很多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不过这些想象大都是围绕学生展开的。关于蜻蜓或者别的什么昆虫是否会飞进教室,她可没去想。不过,就算她想到了,她也不可能做任何防范措施。天气很闷热,教室里又坐满了太多的人(原本教室里的学生就已经很多,教室又小,却还要在后面摆上两排评委席,密密麻麻地挤满评委以及虽不是评委却希图学习小余老师教学经验或者寻找小余老师教学破绽的人),这使得不打开窗户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窗户打开,并不说明蜻蜓就一定飞进来。蜻蜓之所以飞进来,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小余老师正在放幻灯。小余老师把幻灯片画得很漂亮,有绵延的群山、弯弯的溪水,有碧绿的树木、青青的草地。蜻蜓的眼睛虽然又大又鼓,其实视力并不怎么好,再加上在闷热的户外给灼得昏了头,因此它对是幻灯幻影还是真实物候分辨得就不是很清楚。它莽莽撞撞就进来了,快乐甚至有些得意地,并且正好又遇上一扇打开的窗户。
不过现在去追究蜻蜓为什么会飞进教室已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它已经进来了,而且此刻还正在教室里。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当一只蜻蜓飞进正在上公开课的小余老师的课堂的时候,她该如何去处理。这应该算是一个突发事件,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个重要的突发事件。在它飞进来的那一瞬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转过头去看它。那是一只漂亮的蜻蜓,它有着荷梗一样碧绿细腻的颜色,竹节一样修长微翘的尾巴,薄纱一样透明俊巧的翅膀。而且那还是一只勇猛无畏的蜻蜓,当它进入教室后,它没有做过多的调整,就直截了当地向它心目中的青草地冲去。这个变故来得太突然,在蜻蜓撞向屏幕的一刹那,小余老师本能地手一抖,关掉了幻灯。不过小余老师的这个本能动作对蜻蜓来说却也是致命的,它想不明白那些山那些水那些碧绿的树木青青的草地怎么会突然就消失了?但是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它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屏幕上。所幸屏幕有一些弹性,它给反弹了回来。不过作为一只没什么思想也不计较后果的小蜻蜓来说,它显然比小余老师要灵活一些,给反弹回来后,并没有晕头晕脑掉到地上,而是一个挺身,又往另一个方向飞去。起初还有一些碰壁,在雪白的墙壁上,在看似空无一物,实则潜藏着巨大危险的窗玻璃上。后来就从容起来,优柔起来,在窄窄的教室里,转着圆圈,急停急起,急升急落,打个旋子,翻个跟斗,轻灵的翅膀弄出一小片白白的风声。
事情正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在蜻蜓没有飞进以前,小余老师的课是流畅的,圆润的,她已经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她甚至几乎要为自己的精彩表演所感动,心中一阵一阵地涌起那种潮乎乎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的弥漫,又使得她的讲课更充满征服的力量。但是蜻蜓飞进来了。而且当蜻蜓从小余老师眼前掠过的时候,它也同时带走了孩子们长久地停留在小余老师脸上的目光。它一抖翅,刷一声冲向某个角落,在撞向墙壁的一刹那,突然一个转身拔起来,又去了另一个地方;它贴着孩子们的脑袋瓜一阵俯冲,像一架小型轰炸机;它绕着评委转来转去,尾巴一点一点,像是在跳舞,又像是在数数。孩子们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它身上,随了它的飞行转来转去,就像湖面上刮起一场风,粼粼的波光散乱了,不再能聚成一个焦点。小余老师似乎已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不仅仅是蜻蜓和她争夺孩子们目光的问题,这还涉及到她这节公开课的成败,那唯一到县上的名额。但是,为难的是她又不能直截了当地撵那蜻蜓,直截了当地提醒孩子们,那些评委目光正在后面虎视眈眈,为她忧心或者看她笑话。她闭了闭眼,对着教室轻轻咳了咳,她希望这样能够重新集中孩子们的注意。
孩子们是听话的,他们的目光又回来了。但这只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小余老师的讲课孩子们已经听过无数次了,所有的过程、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都已经烂熟于心,而小余老师却还做出一副启发的样子,这未免有些无聊,真实的哈欠就忍不住要冒出来。恰好这时候,一个蜻蜓飞进教室来了,那是一只可爱的有表演欲的而且手段不错的蜻蜓,这样的特点对枯坐无趣的孩子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不过迫于小余老师的咳嗽,他们只得强直了脖子,努力地把目光固定在老师脸上。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仍然还是发生了,当蜻蜓在教室里飞过一阵后,它无趣了,累了,开始寻找着陆点。这时候它便发现了小余老师那因为要上这节公开课而经心修饰过的头发,她把头发的前面烫出一个上翘的凤头,她以为这样要精神一些,给评委的印象要好一些。但不知这却成了她的又一个漏洞,被蜻蜓当成了着陆点。蜻蜓在空中稳住身子,长伸了细腿,抖颤着翅膀,便要落下。小余老师发现了,但她不好伸手去赶,她抬起手,往后掠了掠头发,以这个巧妙的动作惊走了蜻蜓。但是蜻蜓盘旋一周后,还是觉得再也找不到比小余老师的头发更好的着陆地点,便又抖着翅膀往那里伸出脚……
喘息
这个早晨和往常不一样。往常的校园,在没有上课之前,是散漫而快乐的。有三三两两的孩子穿过林荫道,一边被他们自己说的趣话儿乐得笑弯了腰。操场上是一大群高高矮矮的孩子,打球,追逐,跳橡皮筋。教室的门口出出进进,学习组长挨个地检查作业,挺着小肚,摆一副小老师的样子。有孩子在背书,摇头晃脑的,一句话在嘴里叨来叨去,怎么也接不上下一句。那个聪明而细心的女孩子似乎已经做完这一切,她把文具盒放到桌子的右上角,书本放到左上角,又拿出一支铅笔细细地削,悄没声息地。
这个早晨却显得神秘而紧张。打球的,收了球;查作业的,放了书,追逐的,停了步;散步的,快快走,全校孩子都来搞卫生。纸屑、果皮、瓜壳、落叶、尘土、阴沟里的积水、道路旁的荒草、窗玻璃上浮的泥点、天花板上挂的蛛网、墙上的墨水渍,花坛瓷砖表面的污物。孩子们拿了扫帚、拖把、铁锨、抹布。人太多,抹布太少,就掏出口袋里的手绢、脖子上的红领巾,在水桶里浸得湿了,拧干,拿到墙上擦。桶里的水已经很脏,孩子们的抹布在桶里淘过和没淘过已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还认真地一遍一遍淘,一遍一遍地擦。又孩子心性,一边擦,一边把水淋淋的手扬来扬去,把污黑的抹布甩来甩去,手上的抹布上的泥点水渍又重新回到了墙上。那个矮矮的胖墩墩的孩子,他是班上的卫生委员,他在一旁吆喝着大家做。可又说不到点子上,就有人不服,有人不听他的指挥,还有人把冰凉的水点溅到他脖子窝里。卫生委员生气了,他一边扭着脖子,一边扬言要告老师。却正好在这时候,老师来了。老师也是在刚吃完早餐后匆匆赶来的。那顽皮的孩子吓得脸色黄了,赶紧埋头做事,时不时拿眼睛瞟卫生委员,并且在心里酝酿着反驳的理由。卫生委员在一边偷偷笑,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鬼脸,告老师的话却是,我们大家都做得很好,老师你表扬表扬啊!老师双手叉了腰,望着那玻璃上的墙上的树桩的树枝的梅花竹叶的图形,什么话也不说,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孩子们没见过他们的老师这么叹气,都举了污脏的冻得红肿的小手问,老师,今天干吗要这样搞卫生啊?老师看了孩子们一眼,老师反问道,难道你们觉得不该搞卫生吗?难道我们的校园还不够脏不够乱吗?孩子们想了想,对啊,是很脏,是该打扫打扫了。但是……但是什么?老师截住孩子们的话头,说了一句结论性的话,如果我们每天都这么打扫,我们的校园还会是这样的吗?孩子们虽然觉得老师似乎话中有话,但都很信老师,所以也就不再开腔。埋了头认认真真地做自己的事情。
孩子们终于上课去了。校园是空前的干净。拿一个老师的话来说,干净得不忍落脚,那脚要扛到肩膀上才敢走。当孩子们都去上课以后,偌大的校园里就只剩下一个人,那人是校长。他巡视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都令他满意。他穿了西装,打了领带,踩着锃亮的皮鞋,倒背双手,甩开大步,脸上露着欢悦的表情。这样清洁的校园让他很放心,他觉得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到他的校长室里,泡一杯茶,让心情在袅袅的茶香中变得平稳一些。
但是校长一会儿就坐不住了,他总觉得有一些什么东西不很踏实,心里一阵一阵莫名地慌,似乎在什么地方还有纰漏。什么纰漏呢?他也说不上来。他重又站起来,走进校园里。他觉得他该守住这校园,只有守住,心里才踏实,才安定。孩子们都很听话,让他们把垃圾放进垃圾桶里,他们就放进垃圾桶里,绝不乱扔。他忍不住一阵快意,他感到他的学校是一所正常运转的学校,老师们孩子们都能依了他的手指扭成一股往一个方向走。不过他虽然发现没有纸屑,却很有些落叶。深冬了,树木不落叶是不可能的,他能管住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但是他管不住落叶。他苦笑着摇摇头,他俯下身子去捡。
但是他即刻发现靠他一个人捡是很困难的,落叶太多,而且似乎落下的速度比他的手还快。他也不能一个人这样捡,堂堂一个校长,这样捡太掉价。他决定停了一个班的课,让孩子们专门来对付这些落叶。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却又发现了另一件让他更加恼火的事情。原来操场上正大摇大摆地走着一群鸡。前面的是一只公鸡,几只母鸡跟在了后面。那公鸡似乎很得意,高昂了头,间或伸长脖子雄叫两声。还忍不住要挥洒挥洒它的得意,转过身来,掸了翅膀绕着母鸡转来转去,并试图踩到哪一只母鸡的背上。母鸡并不情愿,往一边小跑两步让开。公鸡很皮性,受了冷落,却并不知趣,又往另一只母鸡的背上踩。终于有一只让它如了愿。从母鸡背上跳下来,那公鸡显得心满意足,它长伸了个懒腰,扇一扇翅膀,还撅着屁股拉了一泡屎……
校长的愤怒是空前的,他几乎没有一点犹豫就往操场冲去。这时候他忘了他是堂堂的校长,停留在他脑海里的唯一念头就是要把鸡撵出去,尤其是那只公鸡,绝不能让它再在校园里那样昂首那样阔步。他迅跑着嘴里吆喝着手上张扬着赶那鸡,他的头发已经变得很乱,西服领带也到了另外的位置。但鸡似乎并不情愿离开,它们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又干净又亮爽的开阔地带,它们刚踱了一会儿步,它们还准备躺下来舒舒服服地晒个太阳,这件美妙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却有一个人要它们出去!它们跑起来,绕着圈子。到了后来,它们甚至展了翅膀连跑带飞,嘴了还欢快地咯咯咯叫。它们把这当了游戏,当了舞蹈,在干净亮爽的操场上,它们旋转着它们的快乐。
来了!在校长撵着公鸡转圈的时候,一个老师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上校长,抓住他,告诉了他一句话,来了来了!领导的车子已经到达校门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