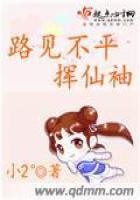晓明“借”到刑警大队,一“借”就是大半年,并且似乎没有了回来的趋势。一个派出所,长时间只有3个民警,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应付的。不要说公休假,就是周末星期天,也不得不时常放弃休息。戴斌是内勤,兼搞户籍,什么报表、资料、汇总,一大堆,每月再不跑也得跑区公安局各业务科室十来趟。而所长呢,是派出所的“当家人”,门户立着,更是不可能没有应酬。区公安局的,乡政府的,其他一些部门单位的,各种工作会、座谈会、联席会,会议不断,即便是他想留在所里帮大家一下也很难。
力不从心呐!遇上案子,我只好单独带上联防队员。我知道一个民警,单独带着联防队员去处警和取证,严格说来是有悖法律规定的。在法制科审批治安案件时,面对调查笔录中取证人的签名,我会反复斟酌揣度,生怕名不是真正的民警签的。如今我才知道,我当初在强调“依法行政”的时候忽视了基层派出所无法逃避的现实。案子来了,你不能不办。办的过程中,没有警力,你还不得不单枪匹马地顶着。上面发现了,挨骂的是你;出问题了,受处理的依然是你。打落了牙齿,你不能展示给人家看,你只能和着咸酸苦涩的泪往肚子里咽。
接近年底,《重庆公安报》的编辑李正权来长寿看他的联系单位付何派出所,同时也顺道来罗围看望我。我和他是在《重庆晚报》一年一度的作者联谊会上认识的。一百多名作者,穿警服的就那么两三个人,次数多了,我和他自然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到派出所,他打了不少电话来,勉励我,也多次提到要来看我。咫尺天涯,忙碌和紧张的工作阻碍着彼此的脚步,我没有机会到重庆拜望他,他也没有机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终于,他来了。
政治处张主任陪他来我办公室坐了坐,晚上一块儿回城里吃饭。正好副局长朱志全、徐鲜华,以及行管科的杨梅副科长也在。
吃饭间,朱副局长问起我们所的近况,问起打击任务是否完成,我说:“可以高兴地告诉领导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不但如此,我们派出所还获得了当地政府、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我讲的是实话,那时候,乡政府已评选我们所为“群众放心站所”。同时,还推荐我们所为区“精神文明单位”,只等区政府精神文明办公室来验收。在区政法委组织的综合治理民意测评中,我们所的群众满意率是百分之百。
听了我的回答,两位副局长都很满意,都要求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我这人直言快语的老毛病在领导的赞扬声中又犯了。我转变话题,感慨地说:“不过,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比如,罗国全那个案子,我们要人无人要车无车,能够将案犯捉拿归案,我真不敢相信呐!”
当时,罗国全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末了,我又补充说:“我差不多已有两个月没有休节假日了,我很想在家里呆两天。”
朱志全副局长对此话题非常敏感,毕竟在基层做过民警,走上领导岗位后,又长期分管刑侦。要人无人要车无车,办一个杀人案,及时将案犯捉获,避免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其中的酸甜苦辣,他一定能够理解和体会到。因此,他愣怔了一下,突然提高了声调,带着果敢的口吻说:“远军,我目前只能以我个人的名义告诉你,因为组织还没有研究,借到刑警大队的袁晓明下个星期回来。如果他不能回来,就另外给你们调个年轻民警来。此外,交通工具的事,的确棘手,我尽力而为,看能否找区财政协调一下,解决一辆长安警车……”
我简直是受宠若惊。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借口上“卫生间”,我出门给所长郭洪平打了电话。郭洪平显然也很激动。
他说:“我马上将此消息转告给戴斌。”
袁晓明离开刑警大队没有回罗围,考虑到他家庭的具体困难,组织安排他到城郊的渡舟派出所。我们所调来的是罗培林。
罗培林当过兵,也是从公安员转录过来的,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特别踏实,特别能吃苦。他的到来,解了我们警力不足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