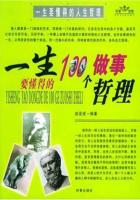他知道自己在飞奔的火车上,但梦里认定乘坐的是一艘跌宕的海船。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坐过任何船了。意外地,他在梦里见到了父亲。
父亲比上次见时更显苍老,坐在床边,抽着烟,说老家要办事,要他务必在清明节前将地里的玉米收割好,免得碍事。他记得父亲是从来不抽烟的,现在,烟气不断喷出,逼仄的船舱拥挤着难闻的焦糊味。他就在这时醒了。
抽烟者是下铺,一个中年男人,刚刚受到乘务员制止,这会儿正烦燥地低声斥责对面的儿子。小男孩躺在铺上,蜷着身子,抽抽咽咽哭个不停。
上车时他已经知道他们是父子,出门去某个地方旅行。看来旅行伊始便有些不顺。他有些纳闷,为什么出门游玩那个男人不带上孩子的母亲。
他回忆自己小时候,总是和母亲在一起时间比较多,并不是因为父亲忙于工作,疏于照顾,而是他自小和父亲稍近距离,就感到透不过气的压抑。熊一样的父亲有着健硕的体魄,棱角锋利的阴絷表情,他怕和父亲面对面。
下铺中年父亲还在吵儿子,小男孩依旧哽着,既不敢大声哭出声,又委屈得停不下来。一直到火车到站。他从上铺爬下,穿好鞋,拎上背包,顿了片刻,趴在那个父亲耳边低语:省省吧,你的儿子早晚有一天会比你更有出息。
火车倒出他们这拨乘客,驾着清冷的寒风又开走了。那对父子惊愕地透过窗口望向他,中年男人眼里夹着敌意和恼怒。
他若无其事转过身,心里盘算,这对相处不恰的父子还要捆绑在一起多少年。他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一直到他上大学,能够名正言顺边打工边读书,不再拿家里一分钱。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五年前,在母亲的葬礼上。他连夜赶回,母亲在桌子上,退缩进一张相框里,黑白分明的颜色使她的容颜比往日更清晰。晦暗幽冷的气息盘旋在屋内的角角落落,明亮的阳光只在门口逗留片刻便折身而去。他转向床边神色木然的父亲,咬牙切齿质问,“李冬生,我妈死了,你为什么不哭!”父亲茫然抬起头,没有料到他会发难,困窘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从不知道父亲李冬生有没有爱过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据说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似乎从未从他那里得到过柔情,也没听过一句可心的话,值父亲心情不好还会遭受一顿殴打,可母亲一生却从没有发过一丝怨言。他们在一起时,家里总是寂静的,很少听到他们相互交流。他不太理解他们那个年代的婚姻。
母亲去世后,他曾劝说父亲到他家里居住,市区怎么也要比县城条件要好,尽管他对父亲心存不满,但那毕竟是他的父亲。父亲先说要考虑考虑,而考虑的结果是,半年后不打招呼便结了婚。
如果不是前几天二叔三番两次打来电话,他再不想回到家乡。他从未想过不许父亲重找幸福,而是他无法接受母亲尸骨未寒,父亲便新婚再娶。后来他还是听媳妇的,寄去一千元贺礼。不过之后便断了往来。
二叔说,小子,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不过这事非你回来不可。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他病了?
不是。大事。你还是回来吧,我的话你爹不听。他这个人,一辈子孤拐惯了。难得听人劝。二叔在电话一端叹气。
小生子,回来吧,再随他们折腾,你爹就要被折腾死了。
到底什么事,二叔。他问。
唉,回来再说,回来再说。
二叔死活不讲,他只好回来。站在十二月的站台上,冷风从四面八方扑来。
父亲住在二叔家,从先前买的那套婚房里被赶了出来。来接他的二叔在路上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父亲竟然是伤在那位新娘身上。母亲去世后,邻居怕老是闷在家里的父亲出事,就带他出去参加一些活动,组织者是中老年婚介中心,一来二去,父亲与其中一个相谈颇投,中心有意撮合,其他人煽风点火,父亲就这样匆匆结了婚,并且卖掉旧居买了套新房。没想到今年那女人与前夫的儿子要结婚,说是母亲出资买的,便强占了去。查查房证,确实是那女人的名字。唉,说理说不过,那女人翻脸不认人,你父亲就这么到我这里了。
他半晌无语。一路思谋,从没想过是这种情况。简直是一场闹剧。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一边心怀兴灾乐祸,一边为房子的事四处奔波,早出晚归。父亲李冬生从不肯走出卧室吃饭,偶尔见到他,总是闪闪烁烁做了错事的表情。
事情进行得还算可以,对方那个儿子人也不算太混,只是穷。自始至终他都没和那个女人见面。他不知道值此波折,父亲还会不会愿意和她过到一起。重新拿回房门钥匙后,他换了把新锁。
簇新的防盗门钥匙摆在李冬生面前,父子俩谁也不说话。
明天我回去。李冬生点点头。
有事打我电话。李冬生认罪似的,再次点头。他发现,五年前还挺拔的李冬生已然是一头白发,邋邋遢遢像大街上没人照料的糟老头。不由一阵心酸。
蓦然他想起下火车前,对那恶狠狠吵儿子中年男人的留言:省省吧,你的儿子早晚有一天会比你更有出息。他从自己身上抽离出去,仿佛看到长大的小男孩,站在那个急燥无情的父亲一旁,强壮、高大、有了扳倒世界的能力。可为什么,他根本没有为童年的伤害感觉到哪怕一点儿安慰?
要不,还是跟我走,以后让我照顾你吧——。他犹豫再三,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