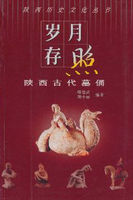以端正风俗为为政之要,在汉代发展出了上述两种形态:一是把“风俗”读为风教风化世俗,强调居上位者应实施教化,以移风易俗,化民有道;一是把“风俗”读为风土民俗,《汉书·五行志》 注“应劭曰:风,土地风俗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着重讨论的乃是社会民俗风情、世俗生活。
但无论如何,辨风正俗、移风易俗仍是风俗论的目的。纠正当世之疵谬,指出向上一路,是所有风俗批评的共同特点。虽因事立言,即事言理,故论旨多歧,然理路脉络,大抵是相似的。
其特色,是主张复古。以一种古今对比的方式,指摘现世流俗之社会风气如何如何恶劣,希望能恢复以往较为淳美的生活。前文所举东方朔、董仲舒之说都是如此。
如此说复古,可能针对一些特定的政策或事例来说,例如该不该举行大赦、要不要恢复肉刑、是否重返封建体制、应不应减税之类。也可能只就其倾向或性质上说。
汉代政治,承秦之后。刑法甚峻,因此从居上位的施政角度看,到底政治是否可以严刑峻法为治,儒家一直非常怀疑;从一般社会风气看,刑戮法治所形成的民情与生活态度,是否真能达到淳美的境界,大家更多意见。因此反映在风俗批评上的,便是主张重德反刑、归本古代圣人的礼乐之教,认为如此才能移风易俗,而使“民德归厚”。如:
△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民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急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尚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匡衡 《上疏言政治得失》)
△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号险陂,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欧以刑罚,终已不改。故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刘向 《说成帝定礼乐》)
△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殴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王吉 《上宣帝疏言得失》)
这类主张尚德缓刑、重礼轻法、尊王贱霸的议论,在汉代可谓俯拾即是。以礼为本,以刑为末;以仁德为本,以法治为末,乃一代之通说。故兴礼乐、复古道、重仁德、贵恭让而成风教,乃与“返本”、“尚质”之说相关联。
所谓尚质,是说世俗太过机巧诈伪侈靡油滑,重利害、善计较、刻薄寡恩、贪财忘义,所以应返归质朴。王吉批评时俗“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寖薄”,即表示他主张文化发展之时代需求是尚质的。
董仲舒论文质相救时,就表达过这种想法,其后如杜饮云“今汉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严安云“政教文质,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皆见本传),都沿用了这个讲法。其说值得注意之处,一是扭转了自荀子以来以礼为文的传统,兴礼乐,跟尚质朴结合了。因为与礼乐相对的,乃是法刑,所以礼乐礼义所代表的文化倾向,是敦厚、恭让,而不再以礼文和材质相对比论。其次,则是礼所关联之德目,已包含了俭朴等,所谓“废奢长俭、表实去伪”,这也是一大变化。依早期批判礼教的思路,礼所代表的正是浮伪修饰,故老庄皆标举俭、朴、实、质以对抗之。荀子论礼,则特重其文饰修伪之义。汉人论风俗、兴礼义,皆本荀子之说而推阐之,却发展出礼即质朴俭啬的新风俗论,实在是思想史上的趣事。
至于返本,则是运用复古道、重仁德、兴礼乐、贵俭尚质诸说,而以一个“本/末”的架构,来呼吁在政治方向上应重本务、轻末作。如杜钦说:“佩玉晏鸣,关雎欢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举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夫君亲寿尊、国家治安,诚臣子之至愿,所当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万物理。”这是戒君王勿贪女色。但此说为何竟牵扯上“正本”呢?显然是用本末说,以君为国家之本,故应重视国君的健康与年寿,君王不好色伐性,国家才能风俗淳美。这就是本末说在风俗批评上的运用之例。
另一种也很常见的运用就是务本兴农说。如贾谊 《说积贮》云:“仓廪实而知礼义。……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今殴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业也。”经济上以农为本务,以工商浮手为末作,认为务农可使风俗敦厚,也是汉代常见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