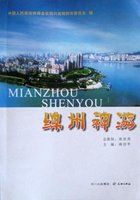不过,假若我们格外重视家庭,把家庭生活视为最主要的生活形态和内容,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脱离生命历程的观点,而改由家居生活方式及其意义的角度去看,究竟我们应该让生活变成什么样。
这方面,《礼记·内则》 是很可参考的。该篇大略可分为四个部分:一内则,二养老,三饮食,四育幼。内则部分,则又可分之为四:一说子与妇事奉父母舅姑的礼节,二为舅姑对待子妇的礼仪,三是家庭通礼,四是夫妇之礼。合并这些礼来看,可以发现它非常重视家庭生活中人与人相对应的关系,希望能营造出一种彼此尊重、相互亲睦,但却各守分位的生活方式。
后世凸显它所代表之生活意义者,莫若清世祖所定的 《内则衍义》 十六卷。此书分为八纲三十二目:孝之道(事舅姑、事父母),敬之道(事夫、勤学、佐忠、赞廉、重贤),教之道(教子、勉学、训忠),礼之道(敬祭祀、肃家政、守贞、殉节、端好尚、崇节约、谨言、慎仪),让之道(崇谦退、和妯娌、睦宗族、待外戚),慈之道(逮下、慈幼、敦仁、爱民、宥过),勤之道(女工、饮食),学之道(好学、著书)。
由此纲目观之,内则已经完全女性化了。生活,绝不如莫洛亚所云,为一社会性的男人之生活,而是完全以家庭为其场域,在家庭中成就其生活之价值与意义。这种生活又被界定为女性的生活。因此全书从“事舅姑”开始,接着谈相夫、教子、主家政、睦亲族之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说此书乃“用以修明阃教”,确实不错。
这本书也可以澄清一些有关中国女性地位的误解,例如大家老是批评中国是父权社会,而女性只立于从属者的地位。这样的批评当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女性地位得看是从什么角度看。社会生活,以男性为主,是毫无疑问的;家庭生活,则由这本书恰可证明它是以女性为主的。
《礼记·内则》 原本并不如此,但在社会实际的家庭生活运作,男性事实上仅成为一种名义上的存在,女性才掌有实质家庭生活的经营权。用今天的情况来比喻,丈夫犹如董事长,名义上公司是他的,家庭以他为家长;妻子却是总经理,家中一切均由她来打理,所谓“肃家政”之意,即是如此。以古代的情况来类拟,则是君与宰相的关系,“相关”之“相”,所指明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而我们别忘了,儒家之学,正是以“相”自许的。《论语·先进》 记载孔子和子路、公西华、曾皙、冉有谈到每个人的志向时,公西华说他的志向很小,只希望在宗庙祭祀或诸侯会见时,能够端正其袍服,站在君王旁边“为小相焉”。后来曾皙私底下问孔子:据公西华所说,好像并不想去主持国政?孔子回答得很好:“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宗庙祭祀和诸侯会见这些事,正是邦国大事,公西华说愿为小相,如果这叫小,还有什么叫做大呢?借用这个比喻,则我们也会发觉儒家对于主持家政的主妇,亦有相同的态度。因为主妇主中馈,而儒家所说的宰相,亦即是在整个国家“调和鼎鼐”的大厨师;主妇肃家政,儒家亦认为此即是为政,《论语·学而》:“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所以,若有人说妇人相夫之道只是小道,非为邦之大道,孔子一定会说:“噢,彼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换言之,依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架构来看,让女性作为家庭生活的主宰者(注意宰相的宰字)或经营者,实不存在限制女性、贬抑女性之问题。反倒是儒家所讲的那一套治国为邦之道,因真正落实之处是在家庭,故原先针对为邦而说的内则礼仪,才会逐渐女性化,成为由女性在家庭中操作的生活经营法则。
在这套生活经营法则中,女性并不只是服务性的,她也常是意义的给出者,例如教子、训忠、爱民、宥过。而且自己必须好学,必须有著作。如此方能点染生活世界,使生活不只是一堆琐屑的柴米油盐与日常起居。
古书中,凡论家居而标举格言,近乎母亲之教子女者,皆属此类,如明周是修 《纲常懿范》 二十卷、清秦坊 《范家集略》 六卷、王士俊 《闲家集》、彭绍谦 《闲家类纂》 二卷、秦爽云 《秦氏闺训新编》 十二卷等都是。
汉魏南北朝所形成的世族门第礼法门风,原本就是这类生活的实践者。唐末世族崩溃以后,一般家族就靠着族规家训来延续这套生活教养与知识。但因男主人往往出外应考、谋官、求职、做生意,所以宗族里主要传承这套生活礼仪以及道德伦理规范的,即是妇女。故宋以后,凡言统宗收族、编撰族谱,必尊欧阳修之谱例,而欧阳修 《泷冈阡表》 中描绘他早岁丧父,由母亲教导他学习父亲的仪范那一幕,正是这个结构中最具解释力的一幅图像。明周是修 《纲常懿范》 自序称“闲居,感其母彭氏教以忠孝之大端”而作此书,即为欧阳修故事的翻版。父亲,都是“不在场”的。这是生活而以家庭为其场域时极可能出现的一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