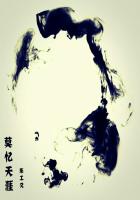婚后不久,我在帕丁顿区买下了老法夸尔先生的诊疗所。有一段时间老法夸尔先生的诊所门庭若市。可是近年来,由于年岁大了,加上遭受圣维特斯舞蹈病的折磨,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们自然而然地信奉一条原则,那就是:医生自己必须身体健康,才能治好别人的病。如果连自己的病都医不好,那人们对他的医术自然要产生怀疑了。所以,我的这位老前辈身体越差,收入也越少,到我买下诊所时,他的年收入已经由一千二百镑减少到三百多镑了。然而,我自信凭自己年纪轻和旺盛的精力,不出几年,诊所在我手中一定会恢复昔日的兴旺。
接管诊所后的三个月里,我一直埋头于工作,几乎没见过老朋友福尔摩斯。因为我太忙,没时间去贝克街,而福尔摩斯除了侦探业务的需要,也很少到别处走动。六月的一天早晨,吃过早点,我正坐在椅子上看《英国医务杂志》,忽听门铃响了,令我吃惊的是跟着传来了我那老朋友高亢而有点刺耳的声音。
“啊,我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大步走进房间说道,“又见到你真高兴,上次“四签名”案件让尊夫人受惊了,想必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吧。”
“谢谢你,我们现在都很好,”我热情地握住他的手答道。
“我也希望,”他坐到摇椅上,接着说,“你尽管你对自己工作非常投入,还没有对我们小小的推理法失去兴趣吧!”
“恰恰相反,”我说,“就在昨天晚上,我还在整理以前做的笔记,把我们破案的成果进行分类。”
“我相信你不会认为资料已经收集够了吧?”
“不,一点也不。我希望这样的事经历得越多越好。”
“譬如说,今天就去如何?”
“可以,只要你愿意,咱们今天就去。”
“像伯明翰这么远的地方也愿去吗?”
“如果你同意,我当然愿去。”
“那么你的诊所怎么办?”
“我的邻居出门时,我曾替他照料一切。他总想着要报答报答我呢。”
“哈!这可再好不过了!”福尔摩斯往椅背上一靠,眯起眼睛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我发现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夏天患感冒挺烦人的。”
“上星期我得了重感冒,三天没出门。不过,我想我现在已经全好了。”
“确实如此,你看起来挺结实。”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我生过病的呢?”
“我的老伙计,你是知道我的办法的。”
“那么,又是用你的推理了?”
“完全正确。”
“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从你的拖鞋上。”
我低头看了一眼脚上的那双新漆皮拖鞋,“你究竟是怎么……”没等我说完福尔摩斯就先开口了。
“你的拖鞋是新的,买来还不过几星期,可是冲着我这边的鞋底已经烧焦了。起初我以为是打湿了以后在火上烘干时烧坏的。可是鞋面上那个写着店员代号的圆形小纸片还在。如果鞋子沾过水,纸片早该掉了,所以你一定是坐着伸腿烤火时把鞋底烤焦了。如果不是因为生病,即使是在这样潮湿的六月天,你也不会轻易去烤火的。”
“就像福尔摩斯的其它推理一样,事情一说穿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他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了我的想法,略带讽刺意味地笑了起来。
“恐怕我这么一解释,就泄露了天机,”他说道,“只讲结果不讲原因给人留下的印象反而更深。那么,你是打算去伯明翰了?”
“当然了。是件什么案子?”
“等上了火车我再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的委托人还在外面的四轮马车里等着呢。你能马上就走吗?”
“稍等片刻,”我匆匆忙忙地给邻居留了张便条,跑到楼上把事情向我妻子解释了一下,随后在门外的石阶上追上了福尔摩斯。
“你的邻居也是医生,”福尔摩斯冲隔壁门上的黄铜门牌点了一下头说道。
“不错,他和我一样买了个诊所。”
“这个诊所早就有了吗?”
“对,房子建成的时候,两个诊所就都成立了。”
“啊!那么,你这边的生意比他的要好些了。”
“我想是这样。可是你怎么知道?”
“从台阶看出来的,我的朋友。你家的台阶比他家的多磨掉了三英寸。
马车上的这位先生就是我的委托人霍尔·派克罗夫特先生。我来给你介绍。
喂,车夫,把马赶快点,我们的时间刚够赶上火车的。”
我坐在派克罗夫特先生对面,这位年轻人身材魁梧、气度不凡,表情诚恳坦率,唇上的小黄胡子有点卷曲,头戴一顶发亮的大礼帽,身着一套整洁而朴素的黑衣服,一眼就能看出他是那种聪明伶俐的城市青年。他们通常被称为“伦敦佬”,我国一流的义勇军团的成员就是来自于他们。英伦三岛上这类人中涌现出的优秀体育健将和运动员比其它各阶层都多。他那红润的圆脸自然地带着愉快的表情,可是嘴角下垂,似乎沉浸于半喜半悲之中。然而,直到坐进了开往伯明翰的列车头等车厢,我才知道了他碰到的麻烦事,他就是为这才来找福尔摩斯的。
“我们得足足坐七十分钟的火车,”福尔摩斯说道,“霍尔·派克罗夫特先生,请你把给我谈过的那些妙趣横生的经历,一字不漏地讲给我的朋友听,可能的话,讲得越详细越好。再听一遍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的叙述对我也有帮助。华生,这个案子后面可能隐藏着某种阴谋,也可能没有。不过,至少具有你我都感兴趣的不寻常性和荒诞性。好了,派克罗夫特先生,我不妨碍你了。”
我们年轻的旅伴望着我,眼里闪着光。
“这件事最糟的是,”他说道,“我在里面充当了十足的傻瓜角色。当然,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我也没看出来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不过,如果我真的丢掉这个差事,结果换来一场空,那我该有多傻啊。华生先生,我不擅长讲故事,不过我遇到的这件事是这样的:
“我过去曾受雇于德雷珀广场旁的考克森和伍德豪斯商行,可是今年春天的早些时候,商行由于受到委内瑞拉公债案的牵连,损失惨重。这事你一定还记得。商行倒闭的时候,连我在内的二十七名雇员当然全都失业了。我在那儿干了五年,老考克森给了我一份评价颇高的鉴定书。我四处求职,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到处碰壁。我在考克森商行时周薪为三英镑,我大约一共存了70镑。没有收入,仅靠这一点积蓄维持生活,钱花得很快。最后终于到了几乎连给登招聘广告的公司写求职信的信封和邮票都买不起的地步。我跑了一家又一家公司、商行,靴子都磨破了,可还是毫无希望。
“我终于打听到龙巴德街的一家大证券商行——英森和威廉斯商行还缺个人手。我敢说,你对伦敦东部的情况可能不很熟,但我可以告诉你,这家商行大概是伦敦最富有的一家了。这家公司规定,所有的应征者必须以信函的方式求职。我把鉴定书连同申请表一起寄了去,可是并没对此抱多大希望。
不料竟然收到了回信,让我下星期一到公司去,并写明如果我的外表符合条件的话,立即就可以开始工作。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筛选的,有人说就是经理把手伸到一堆申请书里,信手拈了一份。不管怎么样,这次我很幸运,所以我从来也没像这样高兴过。开始的薪水是一周一英镑,工作和我在考克森商行干过的一样。
“现在我就来说说这件事的古怪之处。我的寓所在汉普斯特德附近波特巷17号。收到任用通知的当晚,我正坐在椅子上抽烟,房东太太拿着一张名片进来了,名片上印着“财务代理人阿瑟·平纳”。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找我干什么。不过,我当然还是让她请那人进来。来人中等身材、黑眼睛、黑头发,黑色的络腮胡须,鼻子有些发亮。他走路快捷,说话急促,似乎是个懂得爱惜时间的人。
“我想,您就是霍尔·派克罗夫特先生吧?”他问道。
“是的,先生,”我说着递给他一把椅子。
“以前在考克森和伍德豪斯商行做过事?”
“是这样,先生。”
“刚被莫森商行录用为办事员?”
“的确如此。”
“啊,”他说道,“事情是这样,我听说你是理财的好手,表现不俗。
你还记得考克森的经理帕克吧,他对你褒奖有加。”
“听他这么说,我当然很高兴。我在业务上一向精明强干,可做梦也没想到城里会有人这样赞扬我。
“你的记忆力不错吧?”他问道。
“还可以,”我谦逊地答道。
“你失业后,还注意交易行情吗?”
“注意。我每天早上都要看证券交易所的价格表。”
“真是个有心人!”他大声嚷道,“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兴旺发达的机会!你不反对我考考你吧?请告诉我埃尔郡股票价格是多少?”
“一百零五镑至一百零五镑五先令。”
“新西兰统一公债呢?”
“一百零四镑。”
“英国布罗肯·希尔恩股票呢?”
“七镑至七镑六先令。”
“棒极了!”他举起手叫道,“这和我了解的一模一样。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在莫森商行当个办事员太委屈你了!”
“你想想看,他当时欣喜若狂的样子让我多么惊讶。“啊,”我说道,“别人可不像你这样看我,平纳先生。我谋到这个职位不容易,对此我已经非常高兴了。”
“什么话,年轻人,你本该大有作为,干这事是大材小用。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看重你的才华,和你的才干相比,我将给你的职务和薪水还是很低的,不过和莫森商行相比,差别可就大了。请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去莫森商行工作?”
“下星期一。”
“哈,哈!我想我应该打个赌,你根本不会去那儿。”
“不去莫森商行?”
“对呀,先生。到那天你将成为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有一百三十四家分公司分布在法国城乡,除此之外在布鲁塞尔和圣雷莫还各有一家分公司。”
“我大吃一惊,说道,“我从没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名字。”
“这很有可能,公司一直都在静悄悄地运转。这家公司是由私人集资的,生意兴隆,所以根本不需要进行大肆宣传。我兄弟哈里·平纳是创始人,现在任总经理,并且是董事会成员之一。他知道我在这儿交游甚广,托我物色一个精明能干而又薪金不高的人,一个干劲十足而又听话的小伙子。帕克谈到了你,于是我今晚就亲自来看看。一开始我们只能给你为数极少的五百英镑。”
“一年五百镑!”我大声叫道。
“这还只是初期的薪金,另外,你还可以从你的代销商完成的营业额中提取百分之一的佣金。相信我,这笔收入将会超过你的薪金数。”
“可是我对五金一无所知啊。”
“什么话,我的朋友,你懂会计呀。”
“我脑袋里嗡嗡作响,几乎要坐不稳了。可是突然我感到了一点可疑之处。
“我不得不坦率地告诉你,”我说道,“莫森商行一年只给我二百镑,可是他们靠得住。说实话,我对你们的公司确实知道得太少了……”
“好,精明,精明!”他如获至宝地大声叫道,“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你不会轻易被人说服,另外,你说的也很有道理。看,这是一张一百镑的钞票,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合作,就把它装进口袋作为预付的薪水吧。”
“这样太好了,”我说,“我什么时候上班?”
“明天下午一点在伯明翰,”他说,“我口袋里有张条子,你拿着它到科波莱森街126号乙公司的临时办公室去找我兄弟。当然你的事必须由他点头才行,不过这在我们之间不成问题。”
“老实说,平纳先生,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才好。”我说道。
“别客气,我的朋友。这只不过是你该拿的。可是还有一两件小事——只不过是个手续问题,我必须向你交待清楚。你旁边有张纸,请在纸上写上:我完全乐愿担任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经理,年薪不少于五百镑。”
“我照他说的写了,然后他把这张纸放进了口袋。
“还有一件小事,”他说,“你打算如何处理莫森商行这一边呢?”
“我一高兴就把莫森商行的事全忘光了。“我写信去辞职,”我说道。
“恰恰相反,我不希望你这么做。为了你的事,我和莫森商行的经理发生过争执。我去向他打听你的事时,他态度粗鲁,指责我要把你从他们商行挖走等等。最后,我忍不住动了气,说:“如果你想把有才干的人留住,就该给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他说:“他会愿意要我们的低薪,也不去拿你们的高薪。”我说:“咱们来赌五个金镑,如果他受聘于我,你就永远也收不到他的回信了。”他说:“行!是我们把他从贫民窟里搭救出来的,他不会就这样轻易离开我们的。”这是他的原话。
“这个无礼的家伙!”我叫起来,“我们连面都没见过,我为什么要替他着想呢?如果不想让我写信给他,我当然不写了。”
“好!一言为定!”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道,“好,我很高兴帮兄弟物色到了你这么精明能干的人。这是预付的一百镑,这是信。请把地址写下来,科波莱森街126号乙,记住约定的时间是明天下午一点钟。晚安,祝你走运!”
“这就是我所记得的在我们俩之间发生的一切。华生医生,你可以想象,我遇上了这样的好事,该有多高兴啊,我兴奋得半个晚上没有合眼。第二天我坐火车去了伯明翰,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赴约。我把行李放在新大街的一家旅馆里,然后按那人留给我的地址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