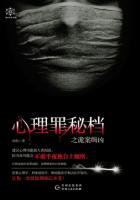“那个小个子男人回答说,“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位。他满足了我们要求的所有条件。我回想不出有哪个人的头发比他的更漂亮。”他退后一步,把头一歪,盯着我的头发看了又看,看得我很不好意思。突然,他一个箭步蹿过来拉住我的手,热烈祝贺我申请成功。
“如果再迟疑不决就太不像话了,”他说道,“不过,我这样慎而又慎,我想你是不会介意的。”他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痛得我大叫大喊,他才松开手。接着他对我说,“你眼泪都出来了。我觉得一切都称心如意。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啊。我们上过当,两次被带假发的糊弄了,一次被染发的给骗了。我想给你们讲一讲有关鞋蜡的故事,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会感到恶心的。”说完他走到窗口声嘶力竭地喊道——已经有人补缺了。窗下传来一阵大失所望的叹息声,人们成群结队地向四面八方散去。他们走了以后,只剩下我自己和那位总管是长着红头发的人了。刚才那些红头发男人已经无影无踪。
“那个小个子男人说,“我是邓肯·罗斯先生。我们这位高贵的施主设立了巨额基金,领取养老金的人很多,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威尔逊先生,你是否已经成婚了?你有家吗?”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
“他的脸马上沉了下来。
“哎呀呀,”他严肃地说,“这可非同小可!你的回答让我好不遗憾。
设立这笔基金是用来维护和繁衍越来越多的红发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竟然还是个光棍儿,真是可悲可叹。”
“福尔摩斯先生,听了这话,我的脸立刻就挂不住了。当时我想这个职位算是泡汤了。他在那里掂量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那没有什么关系。
“换了别人的话,”他说,“有这么个污点可能就完蛋了。可是,您的头发长得这么出众,我们就对您通融一下而不苛求了。您什么时候能够到职?”
“哎,这可有点叫我犯难,因为我开了个铺子。”我说道。
“文森特·斯鲍尔丁说,“威尔逊先生,这个您不用操心,我可以替您照管生意。”
“上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问道。
“上午十点到下午二点。”
“福尔摩斯先生,当铺的生意大多在晚上,特别是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晚上,因为过了这两天就是发薪水的日子了。看来我上午多挣几英镑一点不影响生意。我心里也清楚我的伙计是个挺不错的人,要是有什么事的话,他都会照料好的。“啊,这一点不碍事,”我说道,“薪水是多少?”“每周四英镑。”
“做什么哪?”
“纯粹挂个名而已。”
“纯粹挂个名?这是什么意思?”
“唔,在上班时间,你必须从始至终呆在办公室里,至少也得呆在楼里。如果你擅离职守,那你就永远失去了这个职位。对于这一点遗嘱上说得一清二楚。在上班这段时间里,只要你离开一下办公室,就是违约。”
“每天上班总共才四个小时,”我说,“我不会离开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邓肯·罗斯先生说,“即使是生病、有事或者什么其他的理由,都不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守在那儿,不然的活,你的饭碗就丢了。
“干什么呢?”
“抄写《大英百科全书》。办公室里有这个版本的第一卷。你必须自备墨水、笔和吸墨纸,我们只提供这张桌子和这把椅子。你明天能来上班吗?”
“当然可以。”我回答说。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我再一次祝贺您荣获这一要职。再见。”他向我鞠躬致意,随即我离开了办公室,和我的伙计一块回家了。我真是太走运了,我简直都乐颠了。
“咳,我一整天都在思量着这件事。到了晚上,我的情绪又低落下来,我总觉得这件事不对头,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大阴谋,可是我猜想不出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真是不可思议呀!有谁会立下这么一份遗嘱?抄写《大英百科全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怎么会支付那么多的钱让人做这类简简单单的事?文森特·斯鲍尔丁千方百计地来宽慰我,不过,就寝时,我自己已经想通了。无论如何,我决心要看个究竟,于是,我花掉了一个便士,买了一瓶墨水、一根羽毛笔和七张大裁纸。第二天早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我就到教皇院去了。
“哎呀,叫我又惊又喜的是,一切都很顺利。桌子已经为我摆好了,邓肯·罗斯先生在那儿照料着我,以便我顺利开始工作。他让我从字母A开始抄写,然后就走了,可是他不时地进来看看我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下午二点钟他和我道别,并且对我大加称赞,说我抄写得又快又好。我离开办公室后,他就把门锁上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每天上午十点到办公室上班,下午二点离开,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工作着。到了星期六那天,这位主管走了进来,撂下四个英镑的金币作为我一周工作的报酬。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如此,再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仍然如此。后来,邓肯·罗斯先生到办公室来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他每天上午只来一次;又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压根儿就不来了。当然啦,我不能肯定他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还是不敢离开办公室,一会儿都不敢离开。
我不愿冒这个险而失去它。这个职位是个美差,对我再合适不过了。
“八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由于我非常勤奋,我已经抄完了“男修道院院长”、“射箭运动”、“盔甲”、“建筑学”和“雅典人”等词条,并且希望很快就能开始抄写字母B开头的词条。我抄写的东西差不多堆满了一书架,买这些纸花去了我不少的钱。可是,这一切突然间就结束了。”
“结束了?”
“是的,先生。就是今天上午结束的。今天上午十点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可是我发现房门紧闭,而且还上了锁。在门板上,我发现了一张用图钉钉着的方形小卡片。这张卡片就在这儿,你们自己看看吧。”
他举起那张卡片。卡片是白色的,有便条纸那么大。上面这样写着:
红发会业已解散。
一八九○年十月九日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看了看这张简短的通告,又看了看满面愁容的威尔逊。这件事可真是滑稽可笑,逗得我们两个人什么都顾不上了,情不自禁地放声大笑起来。
我们的这位委托人满脸涨得通红,气急败坏的嚷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如果你们只会取笑我的话,我可以另请高明。”
威尔逊说完就想从椅子上站起来,福尔摩斯一把将他按住,并且大声地对他说:“别急,别急。我说什么都不会放过您的案子。这个案子实在是太不同寻常了,使我们感到耳目一新。请您别见怪,这件事确实有点太滑稽了。
请问,您发现了门上钉着的卡片以后,您采取了什么措施?”
“先生,我当时惊呆了,已经不知所措。后来我向往在办公楼附近的人们打听,可是他们似乎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最后,我去找房东。他住在一楼,是个会计。找问他能不能告诉我红发会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是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团体。接着,我问他邓肯·罗斯先生是什么人。他回答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说,“哦,就是住在4号的那位先生。”
“谁,就是那个红头发的男的?”
“是的。”
“那位房东说,“噢,他叫威廉·莫里斯,是个律师。他的新居还没有搞好,所以暂住我的房子。他昨天就搬走了。”
“我在哪儿才能找到他呢?”
“啊,在他办公的新地方。他确实把他的地址告诉过我。对,爱得华国王街17号,就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
“福尔摩斯先生,于是,我立即动身去那里。我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那儿原来是个护膝制造厂。我一打听,厂里谁都没有听说过名叫威廉·莫里斯的人,也没有听说过名叫邓肯·罗斯的人。”
“那您怎么办呢?”福尔摩斯问道。
“我回家了。我家在萨克斯一科伯格广场附近。回到家后,我就征求我的伙计的意见,可是他根本就帮不上忙;他只是说,如果我耐心等待的话,也许会收到来信,从中得到一点儿消息。福尔摩斯先生,他这话可不中听,我不想把这么好一个职位给白丢了。我听人们说您足智多谋,而且愿意为那些不知如何是好的穷人出谋划策,于是,我马上就到您这儿来了。”福尔摩斯先生说:“您做得对。这个案件非同小可,我很乐意接手。根据您刚才对我所说的情况来看,这件事可能很严重,比乍看起来严重得多。”
“真够严重的啦!”杰贝兹·威尔逊先生说道,“您看,我每个星期少了四英镑啊!”
福尔摩斯接着说:“就您本人来说,我认为您不应该对这个非同寻常的红发会有什么怨言。在我看来,情况恰恰相反,您白白赚了三十多英镑,且不说在抄写以字母A开头的那些词条的过程中,您还增长了不少知识。所以说,您并没有吃什么亏。”
“我是没吃亏。可是,先生,我想找到这伙人,弄清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这样开玩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对我——开了个玩笑的话。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他们花去了三十二英镑啊。”
“我们会竭尽全力替您弄清这些疑点的。可是,威尔逊先生,我得先问您一两个问题。您的那个伙计最先叫您注意到了那个广告,他在您那儿干多久了?”
“当时他在我那儿差不多一个月了。”
“他是怎么来的?”
“看了我登的一个广告他就来了。”
“只有他一个人来谋职吗?”
“不,有十多个人呢。”
“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
“因为他挺灵巧的,工钱要的也不多。”
“实际上,他只领一半工资。”
“是的。”
“这个文森特·斯鲍尔丁长什么模样?”
“小小的个头,墩墩实实,动作非常麻利。他年龄三十开外,可是脸上没长一根胡子。前额上有一块白白的被硫酸烧伤的伤疤。”
福尔摩斯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兴奋,在椅子上挺了挺身子,然后他说:
“这些我都想到了。不知您注意到没有,他耳朵上还扎了两个戴耳环的耳朵眼儿?”
“是的,先生。他告诉我那是一个吉普赛人给他扎的,他当时还是个小伙子。”
“哼!”福尔摩斯说着就陷入了沉思,然后他问道:“他还在您那儿吗?”
“噢,是的,先生。我刚刚从他那儿来的。”
“还有,您不在的时候,您的生意一直由他照管吗?”
“先生,我对这个可毫无怨言,上午本来就没什么生意。”
“好了,威尔逊先生,关于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我将非常愉快地在一两天之内告诉您。今天是星期六,我希望到下星期一我们就能作出结论了。”
我们的这位来客走了之后,福尔摩斯对我说道:“哎,华生,依你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坦率的回答说:“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我胸中无数。”福尔摩斯接着说:“一般而言,事情越是稀奇古怪,真相大白以后,就越不那么高深莫测。一张普普通通的脸最难以辨认,同样,侦破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犯罪也是件挺让人头痛的事。但是,我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处理这件事。”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道。
他回答道:“抽烟。解决这个问题得抽足三袋烟。同时,请你在五十分钟之内不要跟我说话。”他在椅子上蜷缩起身子,他瘦削的双膝几乎都碰着了他那鹰钩鼻子。他双眼紧闭,静静地坐在那里,嘴里还叼着一只黑陶烟斗,看上去就像某种珍禽异鸟长长的尖嘴。我当时认定,他已经睡着了,我自己也打起瞌睡来。就在这时,他忽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随即把烟斗放在壁炉架上。
“萨拉沙特今天下午在圣詹姆斯礼堂演出,”他说道,“华生,你看如何?你能离开你的患者几个小时吗?”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可做。我的工作从来就不需要我时时刻刻守在那里的。”
“那么,你就戴上帽子跟我走一趟吧。我打算先到市区,顺路我们可以吃顿午饭,我注意到节目单上德国音乐很多。德国音乐更合我的胃口,意大利音乐和法国音乐没有德国音乐那么动听。德国音乐听了发人深省,我正想内省一番呢。走吧!”
我们乘地铁到奥尔德斯盖特,接着步行一小段路就来到了萨克斯-科伯格广场。今天上午我们听到的那个奇特故事就发生在这儿。这里是一片破破烂烂的穷街陋巷。虽然狭小破败,但是门面还算讲究。四排灰暗的两层砖房前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四周围着铁栏杆。院子里有一块杂草丛生的草坪和几簇月桂树丛,月桂树的花已经谢了。尽管小院里烟雾弥漫,一片狼藉,这些植物却顽强地生长着。在街拐角处,一所房子上挂了三个镀金的圆球和一块棕色木牌,牌子上写着“杰贝兹·威尔逊”几个白字。这个招牌表明,我们那位红头发的委托人就在这儿营业。歇洛克·福尔摩斯在房前停下脚步,眯起双眼,目光炯炯有神,歪着头把房子仔仔细细察看了一遍。他随即漫步来到街上,然后又返回那个街拐角,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房子。后来他回到那家当铺坐落的地方,用手杖使劲朝人行道敲打了两三下,接着他走到当铺门口敲门。门立即就开了。开门的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胡子刮得光光的,他请福尔摩斯进去。
“不啦,谢谢。”福尔摩斯说道,“我只想劳驾您告诉我从这里到特兰德怎么走。”
“到第三个路口往右拐,第四个路口再往左拐,”这个伙计马上答道,随即关上了门。
我们离开当铺的时候,福尔摩斯带着评价的口吻说:“真是个精明的小伙子。依我看,他在伦敦算得上是第四个最精明的人。在胆量方面,我不能肯定他是不是数第三。我以前对他就有所了解。”
我说:“很显然,在这个玄妙的红发会事件中,威尔逊先生的这个伙计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敢肯定、你去问路无非是为了看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