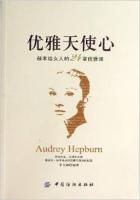不知是咋的了,前后不到半年的光阴,村子陆续无常了三位老人……最先归真的是走路如行云流水的草上飞——外号叫老铁头的马彦林。为他送行的那一天,野麦子淌整个庄上的男女老少都加入了送葬的队伍……
我也是其中的送行者。母亲对我说:“拉麦昨,我的娃呀,你也随大人到坟上送埋体吧!不管谁无常了都要送一送,哪个人都有这一天!迟早都要去见主见圣呢。”
“好,好,我知道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说过:‘不管是在队伍里还是村上死了人,都要开个追悼会,用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呢。’”
“哎,我的好娃呀,你懂事了,将来长大成人肯定有出息哩。”
也就是从这天起,我便永远地记住了母亲说的话。哪个人都有这一天,送别人等于送自己。
还没过几天呢,庄南头赵占科的父亲又无常了。赵把势和我父亲都是同一个滩里的牧羊人。我的父亲在我跟前的叮咛同母亲是一样的:“拉麦昨去送一送你姑爷,到坟上添几把黄土也算是行善积德呀!”
“爹您给我说一说这赵姑爷的来历吧。”
父亲听了我的恳求意味深长地讲道:“这一家人没有几个亲人。在兵荒马乱的那个岁月,赵老爷子还年轻就给马匪抓去当了勤务兵。有一回在马鸿逵‘将军第’门口站岗的时候,望见马屎肚子屁股后头随一大帮使唤丫头,从此,他就动了心思:我那独根儿子将来要能娶上这种水灵的女娃该有多美……没想到以后的一天夜里,他真的贼胆包天下手了……乘夜黑人都睡下的时候,翻进马府的后院抢走了他白天看准的那个丫头……连背带拖费了不少的周折逃出了银川城……直奔东山上来了——就是现在的野麦子淌。可是,这个苦命的女子不装人,不生养娃娃,他的儿子赵占科对他爹说再给他重找一个婆姨。老汉一想也对呀,儿子要传宗接代啊,不能断了香火!”
可是话说回来,光想有啥用,家里穷,日子苦,哪来的钱给他娶婆姨,没办法,又从海子井庄子上找了一个疯丫头当了媳妇……结果,这个疯婆姨就生下了两个娃娃,还是疯子,没有一个是精灵的。唉,穷命啊!真个是麻袋换草袋——一代(袋)不如一代(袋)了……
赵老爷子头七祭日刚过完,庄子上的马彦生又无常了……这老爷子更要去送行了……为啥这样说呢?就因他生前在月儿弯羊场上是个看守羊圈的老人。在羊场上,他肩负着两种使命:一、给我父亲和马保山大爹两个牧工做饭。二、放羊羔并照顾一些淘汰下来的老病残的大羊。
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常常跑到月儿弯羊圈上,最爱吃他的羊奶子锅盔(馍馍)。还有羊奶子泡黄米干饭和大头揪面……这东西太香了……如果几天吃不上羊奶,一想起来就流口水……村上大多数的人可没有这个口福呀!这一点好处,我不能不说在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最为了不起的幸福!
在那个艰辛的岁月中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喝到羊奶的……
马彦生爷爷平时最爱抽烟。有一回,我发现他睡觉的地方比父亲和马保山大爹的那头高出了许多,大约一尺厚。我很好奇,顺手揭起沙毡一看才明白:原来毡子底下全铺满了香烟盒……什么黄金叶,长城,三门峡,恒大……应有尽有呀!我的主啊,这简直不可思议!
后来,我从大人那里得知老人临终前留下的一段情节,听起来让人感伤!
在他快要不行的最后日子里,家里人把老人送到了北边三十里外的马家滩石油医院去看病。大夫诊断后,对他的儿子马永山说道:“老人家得的是肺癌,已经是晚期了……你们是山里人,条件太差了,已经是晚期了……就把他送回去吧。有可能的话尽量让他吃点好的……他活不了几天了。”
没想到大夫的这番话让老爷子听到了,他慢慢地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对大夫说道:“你们这算是啥大夫呀,我来看病,你们让我回家,药也不开,针也不打……”
大夫一听老爷子说出了这般的话,一把将马永山拉到病房门外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安慰他老人家了——你就破费一下给他买上几条好一点的香烟,让他再好好地抽上几天吧……从X光片上看,他的肺部已没有一点清晰可见的了,一片漆黑。就跟煤炭一样黑,你可以回了,就按我说的方子最后安慰一下他吧。”
马永山将老人拉回来后果真按大夫的话去做了……老人在一个主麻的好日子里安祥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人世!
刚开始,在我充满童真的眼睛里,觉得这老人的归真与老大夫的手段太残忍了一点:明明知道老爷子得病的根源与他一辈子抽烟有着直接的关系,却还雪上加霜——让病人继续吸烟。这不是坑人吗?这和提刀杀人有啥区别呢!
在以后的岁月中,随着我的逐渐长大成人,每每回想起这件往事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这其中蕴涵的人生哲理呀!
为了摆脱孤独与烦闷,整天待在羊场上,除了看圈、做饭、放羊之外,剩下的光阴那就只有连续不断地抽烟了……不知送走了多少个寂寞难熬的日子……最终是香烟成灰泪始干了。
难怪庄上的人们送给老人一生最形象不过的称呼——“烟三爷”!这个雅俗共赏的大号真是名副其实呀!
因老人在兄弟八人中排行为三,且一辈子嗜好吸烟,才得这一尊贵的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