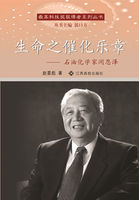所谓文人的笔锋,所谓时代的利刃,所谓幸福的猪或痛苦的苏格拉底,也许只是一份无可奈何却享受其中的挣扎。
黄金时代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爱情,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艺术家、小说家们通常都承载着全世界的孤独。“一个终生与贫穷为伍的人,如果不能改变,依旧要与贫穷为伍,那么我亦坦然。”这是最诚实也是最欢欣的话语。
萧红在东渡日本时曾给萧军写信,她言语不通,就那么孤身一人在异乡的土地上,却在信中说,这就是她的“黄金时代”。令我特别感动的,不仅是因为她在那样的环境说出那样的话,还因为她自己过人的敏锐。当时她在物质上已是非常匮乏与艰难,但在心情这样痛苦的时刻,居然能够看出自己处的是一个黄金时代,虽然“是在笼子里度过的”。作为一个作家能够看出自己当时的所谓“幸福”,看出时代的某种深邃,这确实符合某种艺术沉溺的洞见力。
人若是久久沉溺在某种事物里,是会闪闪发光熠熠生辉的,“因为如此艰难,才有沉溺的必要。”
想起前段时间在西藏山南见到的朝圣者。这些朝拜者在寺庙前的广场上磕头,他们有些是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五体投地,一步一拜,一路磕头去大昭寺。严寒的长途跋涉使得他们有不同程度的伤,但与头顶和地面多次强烈碰撞而留下的疤痕相比,都不值一提——他们大多用拜垫,双手绑有自制的松木板,因不同的发愿做相同的动作。广场上是低沉的诵经声和木板接触广场地面的嗒嗒声以及四肢和身体向前匍匐的摩擦声。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羊卓雍湖、日喀则、定日、绒布寺,就这样,一步步而来……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唯有梦魇者才能进入浮世绘和童话的秘境。
患精神分裂症的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二、洛神的溺毙
“我爱这清明的孤独,我怕这喧嚣的寂寞。”
“我们永远没有黄金时代,就像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才发现可怜兮兮的青春有多么珍贵。虽然青春很糟糕,肮脏、自慰、背叛、苦痛和忧郁,但也止不住我们流泪地怀念。”
在如今这个年代,文艺和刻奇相连,人们仿佛要将每一分每一秒的剩余价值都压榨殆尽。“金钱买不到幸福,但确实带来了一种更令人愉悦的痛苦形式。”喜剧演员米利根说的话,正是对现实的一种简洁描述。
我有一位和萧红一样,同样是生于东北的朋友,因为从小在老工业区长大,他童年最多的梦境就是工厂废墟。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描述他的梦:锅炉是造梦的永动机,它的内部是个空旷的剧院,蒸腾着巨大的云朵。钢铁和管道是梦工厂巨人的骨架和血管,药剂师提炼毒药,密室墙上开满瑰丽的霉菌,妖异诡谲。香薰是化肥的味道。池子里漂浮着斑斓的油彩,水花就像画里的睡莲池。废渣堆积如山在夜色中如宝石般闪闪发光。
我曾惊讶于这样的想象和光怪陆离,却无端发现,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也再不屑于谈论这些“幼稚”“无聊”的童年记忆。他说,漫步于周遭人流,所感触到的,只是无尽的孤独感。真是应了那句话:懂得越多越像孤儿,走得越远越觉得世界本就是孤儿院。
其实,孤独未必不是件好事,没有它做药引,旅行成不了心病良方,最多只能算片阿司匹林。马尔克斯已经逝去,孤独的时代和霍乱的爱情却将一直继续。仍然没有人给上校写信,将军依旧会囿于迷宫。光合作用与字里行间,当年的流行成了今时的经典,这是时间酝酿出的魔幻现实主义。
夏秋相交的季节,暂时忘却萧红的年代,村上春树的“钝感力”和“小确幸”负责构成双螺旋链式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曲折向上,老话说得可真是形象生动。
想来真理也并不抽象,它就落脚于每一个生命的生老病死,每一株草木的荣枯青黄。那些大道理讲不通之处、庸常视角以外的盲点,才是彷徨、困惑暌违已久的焦灼地。
讲述文学、讲述作家故事的影像作品继续从制片厂滚滚流出,电影的确不该是课堂,也不该是播报剧,它向来是一个骨子里的狂热分子,它可能是社会的痛感神经,是时代的评述达人,迎合甚至引导着思想的每一次潮流。
然而,也正是它,一次次将一代人共同的话题推向前台,使得传统的个人阅读和创作逐渐让位给一种集体性的大众消费行为。
人们曾经因为学会了“听”和“读”而忘记了“看”,现在又重拾“看”的经验,且更适应于现代的感觉。即使本雅明、霍米?巴巴们会拉上法兰克福主义者同仁,一直像失忆人般絮絮叨叨下去:在机械复制时代凋零的,正是艺术作品的光晕。君不见,你的同桌我的前排他的后座,类型化的青春已然快被炒煳。沉溺于趣味中的情绪调料显然已经不足以做怀旧的资本。屏蔽麦克卢汉、波兹曼和让?鲍德里亚的长篇大论,年轻的人们也在追寻娱乐和感官刺激的旅程上孜孜不倦。
而对于褪去所饰演人物外衣的明星、演员和偶像,人们不过是一次次地造神,再一次次地伺机砸碎。风起时,极尽捧杀鼓吹炒作包装之能事;风去时,狠为毁谤贬低落井下石之踩踏,从没有平和客观的心态。不是人们不知,盲从跟风者虽有,但大多数看客和制造者们实在都很有兴趣参与一拨拨热闹的狂欢。水上狐尾藻,尘世乌托邦,有人攫足了利益,有人排遣了无聊,这是庶民的胜利与悲哀。
审丑,消费,热腾的鸡零狗碎。猎奇,八卦,廉价的插科打诨。观念的水位不断召唤新的标尺。寻找耶稣与等待戈多之间,生活这张显卡,已经有太多待修的物理坏道。在全民舆论爆炸的信息年代,面对扑面而来的聒噪,既喜且忧。
喜的是,乡愁和美一次次被知识分子们重提,以美育代宗教,未尝不是一种心灵的富足。即使是最潦草的秋之怀古,也莫不象征着回归。忧的是,太多纷至沓来的所谓“宁静”,或许只不过是为了趋时。急进的节奏注定承载不下千古岁月、一湖诗酒,却需要一个精致的粉饰和慰藉。
乡愁原是一种高尚的痛楚感,美本身也自有一份凛然。而在热闹的结构和架空盛宴里,每个赴宴者都在认真敷衍,不亦乐乎。于是,编程在左,边城在右,怀古的记忆就此脱臼。
我想我们既是牺牲者,也是刽子手。
那么,用文学和艺术来悬壶济世吗?不,请别误会,我猜想其实鲁迅也并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只是,有时,像那个年代的人们一样,做些有聊而“无用”的事,不让热闹仅仅沦为狂欢,这点还是值得争取的。就像民谣歌手唱的: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轻松,愿意感动孤独,不再忐忑。
某天,想象一块挂满一百首诗的绿地、一方聚集上百位歌者的山岩吧,如同心脏般的正弦波律动会与整个世界产生共鸣。
秋天确实易使人触景生情、感时伤怀,却也能令人思绪清明,在沉静中观照历史与当下,发现鸟兽鱼虫和生命中奢侈而奇异的美。公元806年,有一个叫刘禹锡的人在纸上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竹杖芒鞋轻胜马,也许一不留神,森林中的主唱已经变成一些不知名的虫儿,湖面水鸟的碎步会踩出一长串简洁的省略号,连绵的茶园里会有翻炒的茶香。
你会发现,仍然有用三十年剪报固定时光留存记忆的人,仍然有饮湖上初晴后雨而醉酒书画的人,仍然有独自漫步于巧克绿与植物链间一卷《本草》寻访花香的人,正是这些可爱的人,滋润着庸常的生活,使珍贵的孤独变得丰沛。
此时,在街上晒太阳的宰予们,就像土豆从土里长出来,风一吹都跳起了舞。这便是了,年年会有秋天,沂水温润清暖,沂雨台上秋风成阵。守山林的人还未到来时,那些“斥乎齐、逐乎宋卫而困于陈蔡之间”的梦,也一直保存在理想的国度。
武陵少年未老,是谁说,黄金时代不再。仔细听,有人欲复古书写,令诗文参差如雨下。雨尽,我知远方有来信将至,宜用想念的念,念之。
屏里吴山梦自到,或许,纸上早有诸字远行。那种红楼一样的情怀,虽死亦不息。
三、尾声
少年时的萧红是一个在落寞中长大的孩子。即便这样,她的生活里依旧充满了欢声和笑语。早晨她在呼兰河边看着薄雾渐渐地被吹散,在火红的烈日之夏,她看着那些在田间劳动的农民,看着他们被阳光炙烤着的、火红的后背,那是一种真切的活着的意义。在夜幕四合,家家户户等待着升起袅袅炊烟的时候,她会趴在窗前,看着远去的人们和他们被夕阳拖得长长的、斜斜的影子。
而今,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有不少红男绿女,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却是寂寞的。
文学和艺术未必毁于商业,却可能毁于不负责任的历史书写。如此喧嚣的年代,又有几人肯耐着性子去理解写字者的“饥饿”呢?我想,只有卡夫卡小说《饥饿艺术家》的开头可聊以祭奠溺毙的“洛神”:“饥饿表演近几十年来明显地被冷落了。早些时候,大家饶有兴致地自发举办这类大型表演,收入也还不错。可是今天,这些,都已毫无可能。”
文字之美,精神之渊,到底哪个才是黄金时代,这之中,必有其真,亦必有其假,又或许,根本就没有真假。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在花盆架上?——萧红《呼兰河传?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