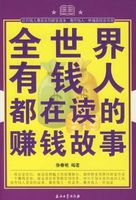其实,“老赵”不仅仅是一个人名,更是一个符号。他成了箭扣长城的一张名片,而他真实的名字却很少有人能叫得出来,但那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你只要走到西栅子村口,说要找老赵,谁都晓得是找赵福清的。老赵的名声让村里人妒忌。在西栅子,老赵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不大不小的致富奇迹,一个乌鸡变凤凰的奇迹。这个致富方式被村子里的乡亲们广为复制,长城边的老百姓盘活了老祖宗留下的物质遗产,破天荒地摆脱了一穷二白的面貌。这样的实践成果,不知是否能为所有长城沿线的千百万急于脱贫致富的农民树立一个样板?
近年来开始盛行的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山村、自然风光、人文遗址和当地民风民俗活动为吸引、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探险、回归自然等为目的的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又为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广大农民的解困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使广大农民在现有基础上增强“造血功能”,靠自身力量改变现状,减少国家对农村的扶持资金,从根本上摆脱农村、农民的落后面貌,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自题
我自己也记不清楚这已是第几次来到怀柔的西栅子村了,但最近的一次也应该有两年的间隔。因为长城,让我三番五次地走进这个原本陌生的小山村。
北京境内的慕田峪长城从东边的怀柔一直向昌平和延庆两地延伸,来到西栅子村一带,因山势陡峭,高低错落,铤而走险,又因有一处地形犹如满月之弓,被称为“箭扣”,于是,箭扣长城声名在外,而西栅子村却默默无闻。在离它几十里开外的怀柔县城里,想找辆出租小四轮去西栅子村,竟无人知晓。究其原因,也许是京郊地图上没有西栅子村的名称。这不,找了好几张各类地图,最接近西栅子村方位的地名,也只是它所在的八道河子乡了。
群山环绕,巨龙飞渡,西栅子村蜗居在山谷里,人不走到跟前,是看不清其真面目的。虽是众山环抱,空气清新,但西栅子村的海拔并不低。这里的乡亲们世代与群山为伴,与长城为邻。祖祖辈辈藏于山中。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真应验了那句“桃花园中,不知有汉”的古文意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攀爬京郊的野长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所谓“野长城”,指的就是那些从古至今残存下来却又从未修复、从未开放游览、素面朝天地静卧在崇山峻岭之中的长城遗址。一批又一批热衷户外运动探险、又厌倦了拥挤的居庸关、八达岭等地的京城长城迷,开始转战司马台、金山岭、黄花城、慕田峪和箭扣一带的长城,或寻觅历史,或解读古建筑艺术,或寻求惊险刺激。如此一来,搅动了西栅子村平静的生活,这里常年闭塞的老乡终于有机会接触到外乡来客。一拨又一拨北京以及外省各地的“超级驴友”接踵而至,一遍遍地踩踏着大小山头,惊醒了沉睡千年的古老长城,也叩动了贫困无助的乡亲们的思绪。
外乡来客与本地百姓的时空对撞,产生的是惊世火花,而不是相互排斥。在经历了最初一段相互揣测的时期之后,没有人会怀疑,这新的一轮乡村旅游方式将会改变西栅子村的历史陈旧面貌,乡村百姓们的贫困日子发生了转机。在这个世道变迁的过程中,人们不能不异口同声地提起一个人——老赵。
老赵,真名叫赵福清,一个热情、爽快、憨厚、本分的庄稼人,没见过多大世面,祖祖辈辈居住在深山里,以种地为生。当初他看见那些“长城好汉”们在山沟里像没头苍蝇似地乱蹿而又找不着北,于心不忍,就义务充当起向导。帮他们带路,背包,介绍景点,敦促保护长城,还从家里拿出水和干粮,资助那些给养不足的登山客。
说起老赵与登山客、摄影人的关系,人们对老赵的热心肠总是赞不绝口。多年前的一个深秋,老赵夫妇发现有几位摄影人夜宿在长城上,当时正刮着呼啸的北风,待在家里还冻得直跺脚,更何况是在高海拔的山上。老赵夫妇背起几件大衣,提上壶开水,连夜上山去“慰劳”他们。见风大低温,两口子干脆动员他们下山,把他们接到家里,腾出了空余的房间和床铺,让大家舒舒服服过了一夜。
还有一年初冬,山里的气温已经很低了,晚上十点多,有两个人惊惶失措地跑到老赵家求救,说他们的一对德国朋友白天上了长城,一直未归,怕是迷路了,求老赵上山帮忙寻找。老赵二话没说,抓起一件大衣就出发了。他焦急地跑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忽然隐约发现在海拔近千米的“鹰飞倒仰”处有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光在晃动,于是,他抄近路直奔上去,见到那对德国夫妇时,他们已经冻得瑟瑟发抖,正拿着手电不停地胡乱划圈发出求救信号。见老赵上来,因语言不通,还以为是来打劫的,不管老赵如何劝说也不肯下山。直到老赵热心地把大衣披在了那位夫人的身上,又背上夫妇俩沉重的摄影包,吃力地用手比划着下山的意思,这对德国夫妇才明白了老赵的用意,深一脚浅一脚地互相搀扶跟着老赵下了山,到家已是凌晨时分了。
这件事在驴友圈中迅速传播,人生地疏的驴友们此时更希望老赵的帮助能成为一种常态。而自从有了初始的经历,老赵也开始琢磨着如何换一种活法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山沟里的土地因为缺水,只能种一些产量低的高粱、玉米和土豆。老赵祖祖辈辈种地,却从未有“温饱”的感觉,紧巴巴的日子过了一代又一代。村子离怀柔城有七十多里的山路,直到今天,副食品、生活用品等还要去城里采购,要解决温饱,要致富,靠那十几亩薄田是没有什么指望的。
因应这股社会潮流,老赵做起了旅游致富的美梦。在驴友们的策划和帮助下,他把自家的院子修整一新,腾出几间空房作为接待用房,添置了被褥、床单及炊具。摄影发烧友们也争先恐后地帮着老赵解决实际困难,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人送来冰箱,有人拉来抽油烟机、搬来自家的彩电,合计着帮老赵家里装上了电话,以便随时能了解箭扣长城的天气情况。很快,这个供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就餐、住宿的“影友之家”建立起来了,正式对外打出了旅游接待的招牌。
老赵如同“天降大任于斯人”,从此就以长城旅游接待员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
天长日久,老赵的名声渐渐在京城热衷乡村旅游和长城摄影的人群当中传开了,人们来到箭扣长城,首先就想到找老赵,好像找到老赵,就找到了救命稻草,找到了依靠。于是,“老赵”成了一个符号,成为箭扣长城的另一张名片,而他真实的名字却很少有人能叫得出来,但那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你只要走到西栅子村口,说要找老赵,谁都晓得是找赵福清的。老赵的名声让村里人妒忌。
老赵与游客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靠,相互帮助的关系。由于有了老赵的存在,众多的登长城者再也不会无目的地在山头上乱跑乱蹿了。每每有让老赵充当上山向导的时候,老赵都身体力行,或背包,或带路,或宣讲长城知识,长此以往,老赵和他的客人们都清醒地认识到,长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可随意糟蹋和损毁,而登长城是为了更充分地理解这份丰厚的物质遗产对我们后世具有多么不可或缺的历史价值。
前些年,我也属于疯狂的“暴走一族”,混迹在京郊、河北一带的长城,流连忘返。屡屡登上箭扣高峰后,多番落脚在老赵的家里,在那里,感觉像家、像休闲的会所、像平静的港湾。不知是哪位热心的驴友给他的家起了一个名字,叫“赵氏山居”,还煞有介事地在门前雕刻了一块牌匾。一根高高的旗杆上,挂着一面“赵”氏黄旗,远远的就能看见。于是,各路人马自然而然把“赵氏山居”看做是乡村旅社、驴友驿站、影人之家、影视创作基地……
走进赵家的院子,东西两排房子的房檐上一年四季总是挂满了黄澄澄的干玉米和红辣椒,院子当中是一个高高的葡萄架,爬满了瓜秧。院子的南面是吃饭和休息用的石板桌与长条木凳,遮阳的棚顶外头悬挂了几串大红灯笼,整体气氛十分温馨,称它为“驴友驿站”绝对名副其实。当人们在峻峭的长城上奔跑了一天或数天后,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困乏,带着仍未散去的惊魂迈进这个像家一样的小院的那一瞬间,劳累不知不觉已经挥发了大半,同时也将平时在都市生活中积压的郁闷、紧张无拘无束地释放出来。这就是“赵氏山居”带给人们的惊喜。
在接待正房的屋里,是两排整齐的大通铺,足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同时入住。一面墙上贴满了“驴友”及“好汉”们的留言和签名。一眼扫过去,有些名字似曾相识,更多的是从未谋面,但却笃定是志同道合的长城“大侠”、铁杆“驴友”们。而在另一面墙上,则贴满了登山者和摄影发烧友们留下的各类长城照片,不知道他们是否想通过此面不同寻常的墙壁,抒发自己的长城情怀,或是向更多的“驴友”和朋友展示自己的摄影才华。老赵的家,就如同一个长城的文化艺术俱乐部,在这里能与各式各样的长城爱好者相遇,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当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不拘一格。
回首老赵一家下决心“改弦更张”,摈弃传统的单一农业生产方式,创办乡村旅游,依靠自身力量提高生活质量的实践,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如今,老赵家的旅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的家境已远不是“温饱”,简直就是一路小跑奔小康了。不久前,他和老伴合计着用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资金,又增盖了一个有着七八间房的大院,连同原来的院子,旅游接待能力最高时竟达到70人。现在,每逢周末,各处打来订房、订餐的电话响个不停,有些甚至远在河北、山东、山西的,一些熟人还指定要自己曾住过的,或者能烧上火炕的房间。人们的心思都不约而同地飞往“赵氏山居”,自然,老赵就成为了他们的贴心人。
在西栅子村,老赵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不大不小的致富奇迹,一个乌鸡变凤凰的奇迹。这一致富方式被村子里的乡亲们广为复制,西栅子村民俗旅游接待户的辐射面不断扩大,已由最初的一两户发展到二三十户。全村年创旅游综合收入七八十万元。往日贫穷、寂寞的小山村,如今成了怀柔乃至京城一个名声在外的乡村旅游接待基地。长城边的老百姓盘活了老祖宗留下的物质遗产,破天荒地摆脱了一穷二白的面貌。这样的实践成果,不知是否能为所有长城沿线的千百万急于脱贫致富的农民树立一个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