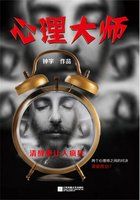我把我的那条红色格子连衣裙送给了雅葛布的妹妹,回酒泉基地以后,我大病一场,终于无法回上海上学,爸爸要送我回去养病,我不答应,外婆替我在上海办了休学手续,我在酒泉基地医院里病恹恹地度过了一年时光。
十八岁时,我终于带着一脸被灼伤般的黝黑皮肤回到了上海,我象极了一个从西北来到大城市的女孩,我沉默寡言,我以一种自惩般的心态埋头读书,直到后来,我考进了西北理工学院,我选择了航天工程,我要到丝绸之路上的那个地方寻找雅葛布,他那灿烂拙嫩的笑容永远无法在我心里泯灭,他是我的雅葛布,永远的雅葛布。
窑洞外透进了一线光亮,天色微明,海运却还是坐在帐篷里听着我的故事,雅葛布的故事。他不断伸手替我擦去眼泪,直到我说完后,一切都陷入了沉寂。老农起床了,他看见炕头没有海运,并不声张,轻手轻脚地拉开窑洞门,然后把门带上,出去了。
黑夜过去了,我看见海运有些疲倦的眼睛看着我,视线里竟然充满慈爱。我闭上眼睛,倒在海运的怀抱里昏然睡去,那一个清晨,我在陕西的一个破陋的农家窑洞里熟睡无梦。
七
海运已经等不及我们把西安的景点全部游完,他说他要去看看雅葛布,那个在我心灵里永驻的男孩。
于是,我们当天就坐上去往兰州的火车,然后又转车去酒泉。
火车进入戈壁的时候,正是一个下午时分,太阳象一个中年男人一样充满温厚的热情,这热情却带着一丝疲倦,照着我缺少睡眠的苍白面孔。海运和我一样缺乏睡眠,他的脸色与我一样散淡中带着潮动,因为那一夜的倾诉他认识了我,认识了我的雅葛布。
戈壁滩依然如过去一样荒芜苍凉,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耐旱的植物,却终究掩盖不住裸露的黄色泥土。山头一个接一个退却着向后闪去,午后的风缓慢行走着,吹掠而过的姿态懒散平稳,土路边秃头般的山坡更是寂静地站着,毫无生气的存活。连太阳和风都是平庸的,我却依然在寻找一种超乎凡俗的情感,他不叫白马王子,他不叫哈姆雷特,他也不叫梁山伯或者许仙董永牛郎焦仲卿,他叫雅葛布,犹如在戈壁滩里建立起来的一份崇敬,他已经成了我十七岁之后的爱情信念,无法更改。
下了火车,我们在龟裂而开的黄色土路上颠簸着前行,细嫩柔弱的绿草象巨人背脊上的体毛,枯燥而稀疏。很奇怪,为什么越是广袤的土地,显现的越加是一种苍凉,好似只能通过这种荒芜才能表达他无尽的包容。那么海运呢?他到底又是怎样一个人?在整个旅途中,我们不期而遇,我一直以我坦然无遮的神秘感向海运表达着一点不羁,我的心里永存着雅葛布,可是海运却象这荒蛮的土地一样强悍而极其包容,他陪伴着我,竭尽旅途所达。雅葛布是戈壁滩上的一颗石子,顽强却对自己不明所以,而海运,却是一片清醒的荒漠,旷达而难以掌控。
我一边走着,一边胡思乱想,然后,我竟然在路边的小土包上看见那种红色刺毛般的无名小花,雅葛布给我留下的唯一礼物。
我快步到那个土堆般的山包边,抓住一根盘究在黄土中的老树跟,我想攀上去采那朵花,那朵举眉开放毫不起眼的小花,即便被我采摘而下,她也依然不会枯败,她会永远象一颗坚硬的刺毛果子那样保持她鲜红的外表和倔强干燥的心。可是当我采下她来时,我就会产生一点奇怪的臆想,好似我又挽留住了雅葛布远离的一点点脚步。
海运看我停下来,他便也停了下来,他不明白我要干什么,待我象一只笨拙的熊一样攀爬着去采那朵花时,他才哈哈笑着走过来把我整个地抱起来,我吊着老树根不肯放手,我说我要把那朵花采下来,一定要采下来。
海运笑着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够不上,我来采好不好?
然后,我松手,站在一边看着他抓住那颗几乎有些枯死的老树根。老树根嘎吱作响,在烈日当空的午后低声吟唱着,调子沉弥而充满苦难。我看见海运吊住树根的手臂凸现出鼓胀的红色肌肉,它与那棵老树根一样看上去具有一种挣扎出强烈苍劲感的唯美。我就那样看着海运吊在树根上的身体猛然一跃,另一只手,抓住了刺毛花的花梗,他小心翼翼地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掐下硬挺而细瘦的花,回过头对我露出一个灿烂明媚的笑。然后,我看到老树根嘎然断裂,山坡上的黄土和石块随着老树的拔根而起在一片泥沙滚动声中倾倒而下,土路边腾起一股巨大的尘土。当飞扬的尘土落定时,我终于看到,海运坐在泥石堆中象一尊刚出土的兵马俑,他看着我微笑着,土黄色的面容上只有一双眼睛闪烁着狡黠顽皮的光,笑容把他的灰头土脸揉成一张多皱的纸,他举起右手冲我说:露西,你看!
那朵红色的刺毛花握在他的手中完好无损,然后,我看见他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我。他把花插在我旅行包背带上,然后拍拍自己身上的尘土向前走去。
我忽然想起在临潼兵马俑二号坑里看到的那个断臂英雄,站在战马边对周遭的一切熟视无睹不屑一顾的样子。那种眼神和此时的海运极其相象,我看到海运灰白的脸上有汗水滴落而下,在他裸露的肩膀和脖子上开拓出一条条泥垢的水流。因为从土堆上跌落下来,所以他走路的姿势有些踉跄,但他依然裹着满身的灰土走着,毅然决然,犹如断臂英雄漠视自己的残缺,依然奔赴战场一样。
我被海运激起了一种莫名的勇气,他让我忘记了疲惫和困顿,我紧追着海运而上,我们向着戈壁滩纵深处走去,去看望那个埋葬在大漠边缘的戈壁滩里的少年,一个叫雅葛布的少年。
雅葛布的墓碑矗立在一片沙砾中,满目的沙尘几乎掩盖了它,它却落寞无争,满含着沉默的呼吁,象对着苍天仰笑的枯死植物,决绝坚毅。海运和我一起在那片土地上,无声地看着寥落的天,苍茫的地,无边无际的荒芜,站立良久。
我把那朵海运采下的红色刺毛花插在雅葛布的墓碑前,风吹着小花,那忧伤的身姿在风里翩然起舞,狂乱中充满绝然。
雅葛布,我来看你了,在我二十二岁的这个夏天,我用这朵红色的小花为你点燃一盏无形的灯火,这一路,你走得可好?
……
一千五百年前,丝绸之路繁华昌盛,那里坐落着许多富饶的村庄。那里水土丰沃,人杰地灵,驼铃的叮当声响彻整个西北辽阔的天空。人们泽水而居,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沿袭至千年之后的今天,雅葛布的家乡依然沉浸在过往的安详中亘古不变,犹如一个无知的老人,对自然的侵蚀听凭摆布、无能为力。
那条通往隔世的道路已经被风沙阻挡,可依然阻挡不住人们回忆和向往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