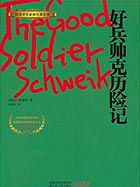话说听见门被推开,莫香春出来一看,原来是潘大炮、老白鹤、二滚、铁锤火急急进来。“老秦呢?咋不去开会?”为首的潘大炮横冲直撞。
心情刚好些的莫香春知他们来者不善,便没好声气:“病了,正请郭大夫看呢!”“病了?真病假病?”潘大炮一步跨进屋里,果见郭大夫手牵药箱背带站在床前,忙打招呼:“郭大夫在这儿?”郭大夫本瞧不起他,却不得不勉强应声:“潘队长也有意思,假病还用找我?”手指噤若寒蝉的秦耀先:“我这不刚给他看罢。”不知高低的二滚一步进来,厉声叫他:“你知道啥?”指着秦耀先:“他是投机倒把分子,我们是来抓他去斗争的,你少在这儿打岔!”
见郭大夫无端受委屈,莫香春喊叫二滚:“你这孩子,咋对郭大夫这么说话?”将郭大夫轻轻一推:“对不起,你快走。”郭大夫也知自己在这儿不妥,只好背起药箱慢慢走了。老白鹤、铁锤蜂拥进屋,潘大炮见自己人多势众,更对秦耀先肆无忌惮:“起来,开会去!”莫香春抢着过来,挡在他面前:“你没听郭大夫亲口说他病得厉害?”潘大炮恶狠狠道:“病死也得去开会。”秦耀先知再说无用,要以昨晚给他的好处求他手下留情:“队长,昨晚……昨晚我不还……”故意停了不说,由他去想。潘大炮知他意思,却佯作不知:“现在你说啥都没用。”扭头给二滚、铁锤使个眼色,两人齐挤到秦耀先床头,厉声叫他:“快起来,再不起来,我们就动手拽了!”
万般无奈,秦耀先只好把郭大夫给的、放在床头的药一把抓起,颤抖着递到潘大炮面前:“队长,你就可怜可怜我吧,让我出身汗,明天好出工。”“嗨!他还想耍赖。”潘大炮指着他叫二滚:“莫理他,装死卖活。”二滚会意,再不吭声,一把掀起秦耀先捂紧的被子,将他一拽:“你给我起来!”秦耀先浑身无力,上半身顿时被拽出床沿。莫香春早气得说不出话,一声不吭,扑上来阻拦,老白鹤却迎面一挡:“反抗是没有用的!”潘大炮听见,像注了强心剂,叫他和铁锤:“你们去把老秦架起走!”老白鹤、铁锤忙与二滚一起,将没穿外衣的秦耀先活生生从床上拽起,拖着便走。“你们是土匪!”莫香春叫着要扑过去阻拦,潘大炮将他一搡,可怜莫香春往后一阵踉跄,“砰!”驼背恰好撞到床头缸盖,直觉锥扎般疼,“哎哟”一声,跌坐地上,失声痛哭。
文欣答应了春妞,不告诉别人她亲了自己,转身要走,春妞还真像大人关照孩子,把他那补丁摞补丁的没膝棉袄扯扯,才依依不舍放他出门。踩着淡淡月光,迎着徐徐凉风,想到卧病在床的父亲,文欣越走越快,只几户人家的距离,很快将到门前,忽听一声声大呼小叫夹杂气喘吁吁的呻吟,心头一紧,撵去看,顿时一惊:潘大炮他们抓犯人般,正将秦耀先连推带搡朝门前大路上拽。更令他不能容忍的是,二滚、铁锤也在其中。
文欣知道他们的企图,气冲斗牛,大叫一声:“不许欺负我爸爸!”扑了上去。紧紧架着秦耀先胳膊的潘大炮忙将在前面拽秦耀先的二滚一拽,指着饿狼般扑来的文欣叫他:“给我揍他!”二滚最好表现,饿狼般迎上文欣,将他拦腰一抱:“你个投机倒把的兔崽子!”文欣气得再无话说,挥拳直捶他脸颊,二滚“哎哟”一声,一个用力,文欣便被摔倒地上。“妈的二滚!”文欣大骂,一骨碌爬起来,跑到门前的碾盘下,抱起半截石头要砸二滚,二滚怕横,“妈呀”一声,抱头去撵已将秦耀先拽到大路上的潘大炮他们。文欣拔腿要追,忽听屋里微弱叫他:“文欣,文欣。”猝然停步细听,原来是莫香春的声音,“砰”地扔了石头,跑进屋里,只见莫香春背靠破缸,头发散乱,坐在地上,床上是秦耀先被拽起时留下的零乱。文欣像亲眼看见父亲被拽起的凄惨情景,心如刀绞,撕心裂肺般叫莫香春:“妈!”扑过去要扶她起来,莫香春却指着秦耀先床头,有气无力地叫他:“快!快把袄子给你爸送去。”
秦耀先无力行走,却经不得潘大炮他们如狼似虎般连推带搡,很快便到了大仓库里。多少年了,秦庄人都没见过这阵势。哪还听蒋家朝拿文作武地念文件,目光齐射向被潘大炮他们押解而来、正瑟瑟发抖站在当中的秦耀先。蒋家朝只好放下文件,潘大炮正要叫他,老白鹤却抢到前面,指着秦耀先大声叫他:“蒋同志,这就是我们村的投机倒把分子秦耀先!”蒋家朝满脸鄙夷,瞅着狼狈不堪的秦耀先,正要发问,被潘大炮挡在背后的二滚却跑到他面前,指着老白鹤挡住的铁锤叫他:“蒋同志,这个投机倒把分子是我跟铁锤帮忙抓来的!”“好好!”蒋家朝冷冷应了,潘大炮却将他轻轻一拽,小声说:“快到后面去,别在这儿碍事。”
“嗨!要埋没我俩功劳。”二滚心里不服,正要分辩,但想到他还攥着自己偷豆角的把柄,只好忍气吞声,站到他身后。蒋家朝这才顾得上打量秦耀先:虽满嘴胡茬,一脸病容,骨瘦如柴,疲惫无力,却掩不住温文尔雅、非同凡俗的气度。心里掂量:怪不得你目中无人,原来是条搁到浅滩上的“龙”。冷冷问他:“你就是秦耀先?”“是的。”秦耀先颤抖着答了。蒋家朝像他的主宰:“你可知我是谁?”秦耀先小心翼翼:“你大概是四清工作队的蒋同志吧?”蒋家朝冷若冰霜:“既然知道,我来你不欢迎,我开会你不参加,是何道理?”秦耀先愁眉苦脸:“我病了。”蒋家朝像审犯人:“真病假病?”秦耀先无力地指着潘大炮对他说:“队长他们去的时候大夫还在,不信你问。”潘大炮不待蒋家朝问便对他说:“莫听他的,我们去时人家郭大夫正背药箱要走,肯定是他没病!”
明知他胡说,秦耀先再不吱声,一边的老白鹤见了问蒋家朝:
“咋样?他没话说了吧?”蒋家朝问秦耀先:“怎么不说话?”秦耀先不知从哪儿来了力气,抬步便到跟众人一样正紧张望他的柴平生面前,扑通一跪:“柴支书,我秦耀先是啥人,求您作个证!”说罢,泪如雨下。柴平生忙过来弯腰扶他:“秦先生,莫这样。”秦耀先突然挥动双拳,痛心疾首:“可他们要要我的命,我有理说不清啦柴支书!”柴平生用力拽他:“说得清,你起来,有我呢!”秦耀先像看见一线光明,用衣袖抹了眼泪起来。柴平生不敢松手,扶着他叫判官也似瞅着他俩的蒋家朝:“蒋同志,秦耀先他身上发烫,是真有病,不信你来看。”蒋家朝头扭一旁,不理他,柴平生只好央求:“我看还是让他回去休息吧!”蒋家朝冷冷说他:“柴支书,这可是阶级立场问题啊!”
柴平生正要问他,乍听门外哭叫声由远而近:“爸爸,爸爸!”秦耀先忙对他说:“是我家文欣。”刚说罢,便听背后屋门砰的一响。人们循声一望,原来是二滚把门闩了,还撅着屁股紧紧抵着。门外的文欣只好哭喊:“爸,给你袄子!爸,我给你送袄子来了!”紧闭的屋门被捶得咚咚直响。柴平生跟二滚商量:“把门打开。”二滚还没反应,潘大炮便问他:“你刚才没见那小子厉害?”“何必跟个孩子一般见识?”柴平生指着浑身打颤的秦耀先说,“他再不能受凉了。”潘大炮不好再辩。二滚年少,却善察言观色,见潘大炮都不说了,便要开门,忽听沉重一声“慢!”扭头一看,是蒋家朝,二滚顿时不知那门开是不开。伴着门外文欣那一声比一声凄厉的叫喊和咚咚捶门声,二滚望了蒋家朝,又望柴平生。柴平生知他为难,便要与蒋家朝商量。正要开口,扶着的秦耀先却没了骨头似的,扑通倒在地上。老犟头他们看见,“呼隆”围上来,柴平生忙蹲下抱住秦耀先大叫:“秦先生,秦先生!”秦耀先半天才喘过气来,竭力而叫:“水……水……”柴平生摸他额头,不由大叫:“呀!烫手!”命潘大炮:“快!跟我一道送人。”
会议无终而散,柴平生跟潘大炮把秦耀先送回家便回去了,不说莫春香如何深夜又请郭大夫给秦耀先治病,只说大仓库里只剩潘大炮、仇仁海、蒋家朝、老白鹤他们四个,因为没达到预期目的,除不知底细的老白鹤外,其余三人都不痛快。见蒋家朝神情沉重,潘大炮掏出香烟抽一支递给他,蒋家朝缓缓接了,潘大炮又擦着火柴,给他点燃。抽口香烟,蒋家朝果然轻松了许多,夹香烟的右手朝另外三人轻轻一抬:“来,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被柴平生救回来的秦耀先服了药,喝了水,好一阵才见好转。莫香春忙凑近他:“好点儿了吧?”秦耀先无奈地望她:“嗯。”莫香春稍微放心,“唉……”重重一叹又问他,“你说他们咋恁心狠?今晚要不是柴支书,指不定要把你咋的。”秦耀先知这次运动自己在劫难逃,却怕说破她又担心,便小声叫她:“早点睡吧。”
柴平生回家,家人早睡了。摸黑在神柜右角拿到老伴为方便他回来点灯而专门放的火柴,把灯点了,端着来到既是他看书办公又是招待客人住宿的西厢房后半间屋里,把灯搁到床头旧书桌上,蹲在床前,缓缓趴下,探身床底,自一堆各种破旧鞋子后面拖出一只尺把宽、两尺多长的陈旧小木箱搁到桌上,两手相互拍了灰尘,稳稳坐上桌前的旧木靠椅,从蓝市布上衣口袋里掏出钥匙,小心打开小木箱,在一摞或许连他自己都说不出名堂的旧文件底下拿出一本没有封面的笔记本,轻轻盖了小木箱推开,把灯挪到面前,放下笔记本,翻开,将笔记本空白页的中缝轻轻按了,拔下挂在上衣口袋里的黑杆钢笔,又开始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写日记。
“×年×月×日,星期三,晴。
“怎能这么对待一个贫农出身、颇有文化素质的农民?赶集买卖只是为养家糊口,供孩子读书。又没捣腾国家计划物资,怎能算投机倒把?”
“蒋初来乍到,却抓住秦不放,是忘了县、社两级派他进驻秦庄的初衷,还是另有缘由——故意转移四清运动的方向,尚要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蒋家朝与潘大炮他们商议罢回艳二嫂家,刚到屋旁,与将要满月的两个狗崽卧在柴堆当头的黑牡丹当歹人来了,呜的一声一跃而起,“汪汪”直叫。虽与它熟了,但蒋家朝仍害怕它,脚步骤停,不知所措,忽见屋里还有灯光,便知艳二嫂又在纳鞋底等他,想叫她出来给自己解围,又怕惊动邻居,只好小声叫:“黑牡丹,是我。”岂料黑牡丹却不认他,带着一身柴屑叫得更紧,大有若他再叫,便要朝他一扑而来的架势。蒋家朝再不敢叫,也不敢动,只好被钉钉住般站着,一任黑牡丹对他狂叫。
正危急中,乍见门前现出一片光亮,接着便是一个俏丽的身影。蒋家朝像遇救星,忙小声叫:“艳二嫂,快来,是我。”艳二嫂听见声音,急奔过去小声呵斥:“黑牡丹,要死,你不认人!”黑牡丹果然不敢再叫,冲她摇头摆尾了,跑回窝里躺下,护它的孩子。“你也是,”蒋家朝这才匆匆过来,埋怨艳二嫂,“听到狗叫,就当出来,愣等到它叫得全村皆知。”艳二嫂反指责他:“我倒说你不是吧!乡下夜里,但有风吹草动,狗便叫唤。听到狗叫我就出来,那万一不是你呢?”
刚说罢,神情已经轻松的蒋家朝来到面前,瞅了四下无人,上前将她拦腰一抱,便要亲热。艳二嫂玉手一伸,堵了他嘴,小声提醒:“说是夜里,却四处有眼,你都不怕别人看见?”蒋家朝这才心虚,遂松了手,艳二嫂看见,却将他那白净的脸轻轻一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