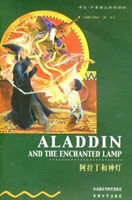话说陈香娅故作生气:“你品学兼优,人人皆知。你哥哥备受公社领导器重,今年的升学率又是百分之九十,你要不能读高中,恐怕全校就没一个能读高中的了。”文欣问她:“那假如我不能读高中呢?”陈香娅拿手绢的手死死抵住他:“我决不后悔!”文欣像被蛇咬,竭力躲避:“不!我……我不能要。”陈香娅小声威胁:“你再不要我就大声叫了啊!”文欣一怔,悄悄扭头望她,只见她皮肤白皙,鼻梁隆起,眼窝微陷,目光平静,这一切与她刚说的话简直判若两人。文欣这才感觉到她潜藏的力量,再不敢推辞,接了手绢,塞进裤兜。
典礼繁琐到近中午时才结束。同学们搬起各自的凳子,像一群被关得太久的小鸟,叽叽喳喳,你碰我撞着回各自教室。陈香娅紧跟文欣,不知又要说什么,拎着板凳的春妞忽斜刺过来,像没看见陈香娅,冷冷叫文欣:“回去时一道儿啊!”文欣刚答应了,乍见正被教师们撤除着的主席台前的一棵树下,卜凡芝正笑着向他招手:“秦文欣,过来一下。”文欣感觉喜从天降,正要答应,春妞、陈香娅不约而同叫他:“快!卜校长叫你。”“啊,我知道。”文欣忙把板凳、笔记本递给春妞,“帮我带进教室。”春妞感到无上光荣:“好!”伸手去接,陈香娅却一把抢过,小声叫文欣:“怕是通知你被高中录取了呢!快去。”文欣扭头正要说她,乍见春妞瞪她一眼,恨恨而去,到嘴边的话也未出口。
文欣走进卜凡芝那明显打着时代特色的乡镇中学校长办公室里,本来坐在桌前的卜凡芝看见,像接待贵客般慌忙站起,指着桌那头的一只方凳,微笑着叫文欣:“快请坐。”文欣的心扑扑直跳:“该不会真像陈香娅说的吧!”谨慎坐下,卜凡芝这才也坐了,望着文欣,脸上那每一颗麻粒都像嵌满了慈祥:“告诉我,秦文欣,初中毕业了有什么打算?”文欣一怔,遂又暗暗提醒自己:“别慌,卜校长考验你呢!”顿时充满自信,脱口而答:“就像杨书记刚才作的报告,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时刻听从党安排。”“好!真不愧是秦文欣!”卜凡芝脸上慈祥顿消,突然换上庄重的校长神情,“现在我以个人名义跟你谈话,请你无愧于我的谈话好吗?”文欣像被一下子推入飞速旋转的陀螺,头晕目眩:“校长,您放心,我会的。”
与其他教师一道撤罢主席台,汉伟没和其他教师一道回办公室,而是独自回到办公楼侧的自己寝室里,轻轻关了门,在床头桌上的烟盒里抽一支香烟点燃,一头倒在枕上。卜凡芝昨晚跟他的单独谈话随口中吐出的袅袅烟雾翩翩浮现:“秦老师,你弟弟确实是棵好苗,这样对他既残忍,也不公平。”
想到魏莲的屡屡告诫和并不富裕的家庭现状,汉伟故作不忍:“谁说不是呢?可家里困难,我也是万般无奈呀!”卜凡芝明知他说谎,但不便戳穿,只好冷若冰霜:“秦老师,你知道吗?你给我出了个天大的难题,鉴于与你是同事和凭我的良心,我只好最后对你说,为了你弟弟的将来,你现在改变决定还不迟。”汉伟却像被捉赃的小偷,缓缓低头:“那就请你尊重一回我个人的意见。”
袅袅烟雾正紧紧缠绕汉伟的缕缕思绪,屋门忽然被“嘭”地推开,汉伟条件反射似的坐起,立时愣了,文欣像一尊冷酷的雕塑立在门口。“你!”汉伟第一次显出惊慌,“进来咋不敲门?”文欣行尸般到他面前,直直望他,直望得他浑身打战。文欣突然泪如雨下:“哥,你刚当教师时,不就在饭桌上说我一定能读到高中么?”“是呀!我是说过。”汉伟平生第一次感觉语言匮乏:“只是,只是现今升学靠‘推荐选拔’,我们村潘、仇势大,他们不同意,我有啥办法?”“哥!”文欣顿感无助,突然扑通一跪,声泪俱下,“我要读书,请你求求他们好吗?”
汉伟一怔,遂站起来扶他:“你别这样,快起来。”文欣扭身挣脱:“不!哥,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这样被人看见不好。”汉伟又扶他,但隐忍不满,“你起来,听我说。”文欣像看见一线希望,这才站起来,嘤嘤抽泣。“我不好求他们,你知道吗文欣?”汉伟扶着他,颇显无奈,“我毕竟才参加工作,为你这事我已经求了不少人,若再求,别人还说我‘斗私批修’不彻底,那我今后还咋进步?我不能进步,你还有啥前途了呢?”
听他说得真切,文欣泪眼朦胧望着他:“可是,哥,你知道吗?我立誓将来当一名作家、记者或编辑,可现在连高中都读不到,那你说我的理想……”文欣再说不下去,又揉着眼睛嘤嘤而哭。
汉伟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伸手给他擦眼泪:“文欣,你听我说,读不到高中,咱想办法工作不行?”“工作?”文欣一惊,因为在他心里,汉伟不仅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而且是他牢固的靠山,只当他无法让自己读高中,颇感内疚,另外给他安排了工作,毕竟父亲去世,母亲无力,自己的命运就全掌握在他这个唯一的哥哥手里。便停了啼哭,满怀希望地望着他。“是的,工作。”汉伟拉他,“来,坐下我跟你说。”文欣顺从他坐上床沿。
典礼结束后的教室一片杂乱。同学们各自捡着一应学习用品,塞进书包,匆匆离开这闹腾了两年的教室,各自回家。二滚挎好书包,叫正默默朝门口走的木根:“喂!到操场上打最后一回球再走行吗?”木根冷冷回头望他:“天热,我不打。”遂见铁锤在捡东西,叫二滚:“你叫铁锤去就是。”二滚不敢勉强木根,只好问铁锤:“搞吧?”铁锤与木根相反,不敢违他,爽快答应:“搞!”二滚像怕操场被人抢占了,拔腿就走,正捡文欣东西的春妞叫他:“二滚哥。”二滚猝然停步。春妞叫他:“你见到文欣就说我把他的东西带走了啊!”“好!”二滚迫不及待答应着走了。春妞捡罢东西,拎着两个鼓鼓的书包出门,乍见陈香娅站在院里的一棵刺槐树下,对着办公室门口发愣。不由脸一沉,到她身边:“等秦文欣?”陈香娅知她跟文欣要好,对自己不满,仍扭头对她微笑:“嗯。”春妞最受不了她这种神情,冷冷问她:“秦文欣家里很穷,你知道吗?”陈香娅却不理她,回头仍望办公室门口。春妞自觉没趣,悻悻走了。
文欣无力地走出汉伟寝室,耳边交替响起卜凡芝、汉伟的声音:“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嫂子说,明春我们公社的三线建设是参加凤尾山国家机械厂扩建,每个大队只去三名工人,每人除队里按一级劳力记工分外,国家每月还发几十元的补助费,这其实不就是工人吗?你嫂子说,只要潘、仇两家不让你读高中,她就想办法把你弄去。”“可是,”文欣心里问自己,“那我自幼的理想呢?”
文欣一路头重脚轻,走着想着,朝教室去,早被陈香娅看见,她迎了上去,春风般热情:“秦文欣,卜校长是通知你读高中吗?”“不!”文欣一反常态,正要对她说出失望的结果,却鬼使神差道,“我要到教室里去拿东西。”陈香娅俄罗斯少女般的脸略微一沉:“你的东西春妞早带走了。”“啊!”文欣冷漠应了,像她并不存在似的,径直向校门外走去。陈香娅见他这般神情,颇显奇怪,撵上他:“你怎么了?”文欣不答。直到校门外路边的树下,才想起该与陈香娅告别,停步望着满脸疑云跟上来的陈香娅。陈香娅正要开口,文欣忽然掏出她给的手绢递给她:“还给你。”陈香娅秀眉微蹙:“秦文欣,你这是干什么?”“对不起,陈香娅,”文欣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不能读高中了。”
陈香娅一愣,不知所措,春妞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一下子挤到他们之间,一把抓过文欣手里的手绢塞给陈香娅:“还不明白?他读不到高中,不好意思要你的东西。”随手拉起文欣,像叫小弟弟般:“走,我们回家。”文欣回头望泥塑木雕般的陈香娅,抹了眼泪,跟春妞走了。直到要拐上回家的路,陈香娅忽然从背后赶上来,把春妞刚给的手绢又一把塞进文欣的衣兜,扭头就走。文欣、春妞回头望她,陈香娅却头也不回,沿来路而去。
星星满天,南风徐徐,荷叶满塘,蛙鸣阵阵。伴着这夏夜的美好,“师爷”夫妇在门前的堰塘埂上吃晚饭,本就惬意、一边抱着孩子的魏莲与他们亲切交谈,更为他们的荷塘晚餐平添了一道舒心的风味。
阮淑琴嚼着菜对魏莲不无羡慕:“这下可好,你们家又添一个硬劳力。”“我下的就是这步棋。”魏莲不无得意地说了,又恨恨道,“想要我供他读高中,做梦!”阮淑琴惊讶:“想不到汉伟这次还听你的。”魏莲不解:“是的,这我也没想到。”“师爷”问他:“听说你明年要让文欣到凤尾山做工?”魏莲冷冷一笑:“哼!免得他在家里我不待见。”“可你想过吗?”“师爷”提醒她,“那可是国家建设工地呀!文欣又聪明能干,要是在那儿混出个名堂,你可后悔不及啊!”“就凭他?”魏莲不屑一顾,“钱无钱,人无人,凭啥?”
“师爷”当即无语,阮淑琴又羡慕魏莲:“这下好了,文欣做工给你挣工分,他妈给你带孩子做家务,汉伟教书给你拿工资,你一家再没吃闲饭的了。”
魏莲不知要开口说什么,堰塘里陡起一阵蛙鸣,“咕咕哇!咕咕哇!”魏莲只好闭嘴,将怀中熟睡的孩子往起一搂。
不说文欣毕业后怎样在生产队里度过半年时光,只说眨眼就辞旧迎新,冬去春来。春节过后,乍暖还寒,几辆卡车载着平原公社上凤尾山工地的民工,驶出平原公社大门,驶出平原街,驶上公路,驶进沿途老态龙钟的墙壁上“农业学大寨”一类颇具时代特色的白石灰标语和被风吹得“噼啪”作响的残存的大字报,向北疾驶。
眼见离家越来越远,越来越荒凉,与文欣并排坐的二滚哪顾耳边风呼呼作响,寒冷刺骨,陡地站起,开口就骂:“妈的!这哪是出工?简直就是充军发配。”同车二湾大队一个认得他的中年男人不由笑他:“不好好搞吗?要是考上高中不就不受这份罪了。”二滚知他取笑自己,又开口骂:“妈的!还不是因为老子造反斗了‘走资派’,这啥鸡巴大革命,简直害死人!”那中年男人却不知趣,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指着冷漠地坐在背包上的文欣问他:“你还怨当年斗了‘走资派’,那他呢?他可是董坡中学的明星,他哥哥又是学校里的教师,咋也没上到高中?”“这……这……”二滚扭头望身边的文欣,无话可答。靠车头坐的有着果实般成熟的二十五六年岁、有着倩女般靓丽的容貌和男人般刚毅气质的胥秀琳念他跟自己是一个大队的,忙给他解围:“哎呀,其实能不能读到高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志气,不是说有志者事竟成吗?”
“对对!”那中年男人连连答应,再不为难二滚。因为他知道,胥秀琳是刚被提拔起来的秦庄大队妇联主任,在近几年的“三线建设工地”上,是全公社出名的“铁姑娘队”队长。这次上凤尾山工地,又是公社主管三线建设的党委副书记、凤尾山工地平原公社指挥长李康实点名要她担任平原公社的妇女团长。
车上又恢复了平静,卡车继续吃力而笨重地行驶。靠车厢站的二滚被呼呼寒风吹得浑身冰凉,只好默默坐下。望着卡车碾轧着的越来越陌生的地形,想着二滚他们关于升高中的争论,文欣心里难受,不由探头眺望尘土飞扬的车后,心里默念:“别了,家乡;别了,卜校长;别了,我的学生时代;别了,春妞、陈香娅……”一想到陈香娅,像被蝎子蜇了,手倏地伸进裤兜,触到一块软绵,又触电般抽出来,因为那是毕业离校那天陈香娅撵着塞给他的手绢。他既怕弄脏了,又怕引起伤心。
卡车越走越慢,越走越不安分,时而昂头,时而竖尾,时而稳稳当当,时而把人猛地抛起又重重跌下。大地也变了样,时高时低,时宽时窄。天有时低得伸手可触,地有时让人一如走进画苑诗境。但无论卡车走到哪儿,总有山鹰像热情的“向导”,在车前方低空盘旋。倘你极目远眺,则群山无际,起伏连绵,恰像一篇冗长的盲文。
刚坐下的二滚把这一切瞅了半天,忽然又呼地站起,背靠车厢,指着前面大叫:“进山了!啊!进山了!”大山回应:“进山了!啊!进山了!”
不知爬了多少道坡,拐了多少道弯,过了多少条溪流,钻过多少个悬崖,卡车像一个个精疲力竭的汉子,终于相继喘着粗气,在一片四面环山的洼地停下,司机们相继跳下驾驶室,“啪!”打开车厢板,车上陡起一片嘈杂。人们争抢着各自的行李,像一个个逃兵,跳下限制他们自由太久的车厢。文欣他们这辆车的年轻司机则走过车前,捡起一块卵石,向前猛跑几步,抬手一甩,那卵石“当”地落进远处清澈见底的小河,溅起一片晶莹水珠,纷纷洒落。
文欣、二滚拎着行李,随同伴们朝工棚走去。面对陌生的环境,文欣恍若隔世,左顾右盼。但见这里群山环抱,只有一个入口,中间是宽阔的盆地,盆地前面的群山呈扇状分布,若把这些连起来看,恰像一只正展翅的凤凰。“啊!怪不得叫凤尾山。”文欣正暗自感慨,乍听前面的二滚说:“可到宿舍了!”文欣抬头一望,面前果然房屋林立,高低分明。高的是新建的一幢幢楼房,低的是刚搭起的一片片油毛毡工棚。相比之下,恰像刚发迹的富翁与乞丐站在一起。文欣、二滚,还有那一群群互不相识的同事,带着各自沉重而破旧的行李,相继钻进一个个低矮的油毛毡工棚。山中的暮色在他们身后徐徐落下。
“嗒嗒嘀!”一夜转瞬即逝,嘹亮的起床号声唤醒山中寒冷的清晨。没什么初来乍到的休息,文欣和那漫山遍野的同事们,便开始了凤尾山工地的“军事化生活”——县为师,公社为团,几个大队为一个连,上下班、工间休息,均以号为令。上下班、到食堂打饭,一应排队。不信你看:伴随起床号响和连队干部们一声声“起床喽!起床喽”的吆喝,一片片油毛毡竞相睁开一双双苦涩的眼睛,接着一阵拿洗漱用具、拿碗筷的乒乓响声过后,像宿舍一样,用油毛毡搭起的一座座食堂门前,排起一条条巨龙般的打饭队伍,伴随那一排排敞开的窗口里的炊事员麻利递来饭菜时的声声喊叫“下一个”,巨龙般的打饭队伍迅速缩短。
文欣终于靠近窗口,接过炊事员递的饭菜,慌忙离队,跌撞着回到一片地铺、电灯亮堂的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