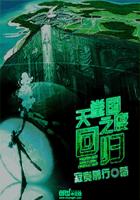此时,我的嗓音不仅恢复了,并且变得更加动听与洪亮。克劳辛先生是那位诗人的哥哥,在一个合唱团当声乐教师。他知道我会唱歌,便介绍我到团里唱歌,并说现在通过合唱可以更好地练声,也为了以后能得到登台亮相的机会打下基础,兴许到时能在台上唱上一两段。一个新的可能实现我最大梦想的途径呈现在眼前,我立刻从舞蹈团转到了合唱团,真的就时常登台露脸。我出演的剧目有《罗伯家的城堡》和《约翰尼·蒙特福肯》。剧里的牧羊人、水手或类似这样的角色都扮演过,我从不错过任何机会。 剧院是我的一切,是我全部的世界,那里有我的生活和梦想。这样一来,我把学习拉丁文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更何况好多人在我面前说过,不会拉丁文一样可以唱好歌,照样能成为伟大的歌唱家。主要是这个原因,我开始厌倦拉丁文,有事没事找个理由就不去上课,逃课泡在乐池里。古德伯格知道以后极其生气,我因此遭到了人生第一次严厉的训斥。我实在是羞惭万分、愧疚难当。我听到古德伯格的话震惊的程度,相信罪犯在听到自己被判了死刑都不及我。他让我停止演出,我做不到,我不用学拉丁文了。
我发现自己是那么依赖别人的仁爱和良善;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都没准备过;我对前景失去信心,悲伤难过的时候,也会认真地考虑自己未来的日子,但通常都是转念之间的事。我还是个孩子,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不知忧愁。
上流社会里也开始有人关心我这个穷小子,她们是丹麦著名政治家克里斯蒂安·科伯乔森和她的女儿范·德·玛斯夫人。范·德·玛斯夫人当时是卡罗琳王妃的女侍臣。她们知道我的情况对我十分同情,欢迎我去他们家。夏天到了,科伯乔森夫人常去诗人拉北克夫妇的希尔庄园度假。她带我去拜访他们,我到他家后很快被让进客厅。拉北克从没和我说过话,不过有一次在花园里他朝我走来,像是要对我说点什么,但刚一走近,看了看我,突然转身又走了。但她的夫人就不同了,她是个活泼、可亲的妇人,她经常和我聊天。我那时开始学习写点东西了,她很乐意我读给她听。一次,她刚听完前面几幕就喊道:“天哪,欧伦斯柴格尔和英格曼的作品中的片段都在这里出现了,你这是抄的!”“对啊,但他们写得真精彩!”我非常坦白地承认了,并继续读下去。一天,我要去看望科伯乔森夫人,她抱来一大束玫瑰花:“带上这个,诗人把这束娇艳的玫瑰花送给科伯乔森夫人,夫人会非常高兴的。”虽然她是半开玩笑地说出来的,但我还是身心愉悦,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第一次听到别人称呼我是诗人。我意识到我将全部心思用来写诗。以前从玩木偶剧院改成玩其他玩意儿是小孩子的游戏,但现在这个转变是郑重而认真的——它是我生存的目标。
一天,我穿着爱德华·科伯乔森送的蓝色外套出门。我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衣服很新,纽扣闪闪发光,但就是太肥了,胸部更宽大,我又没钱改,只能就这样穿出去。为了穿出门更合体,我把领子上的纽扣都系紧了,但胸部还是有点像袋鼠的育儿袋,我把一大捆旧海报塞进胸部和外套之间。当我出现在科伯乔森夫人和拉北克夫人面前时,她们奇怪地看着我的胸部,直截了当地问我往胸部放了什么。看我不吱声,她们说,天气好热,该把外套解开。我不会那样做,不能让那捆海报露出来。除了两位夫人以外,希勒议员也常在那儿消夏。他那时还是个学生,他虽然年轻,却因为解答了巴格森之谜而名声大噪。他是个多才的人,我在皇家剧院看过他的悲剧《朝圣者》。他还写了一些诗,《丹麦的神话》这本书也是他写的。他是个热情、有点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很乐意与他交谈,也非常高兴有他这么个朋友,他总是不露声色地关注着。当有人拿我开涮时,他是少数几个跟我说真话的人之一。他还能看到我身上除了滑稽、单纯的天性以外的潜质。
我的剧本
我得到一个后来出名的绰号“老是好奇的小家伙”,它是女演员安德森夫人给我取的。安德森夫人也住在希尔庄园,她是拉北克夫人最喜欢的女演员。我认为这个绰号取得名副其实,我的好奇常常惹来人们的哄笑,而我从笑声里只听出了赞许。我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他第一次见到我是在一个沙龙里,人们为了开心,让我背一段自己的诗作。我诗中率真的语言无意识地流露出内心的沉重,本是准备嘲弄的人们变成了深深的同情与思索。
有一位值得我敬重的老夫人,她是已故的知名人士厄本·尤根森的母亲。她的家就像我的避难所,她的家让我毕生难忘。她是位极有才华的知识女性,但那属于过去的岁月,她生活在回忆当中。她给我讲述她的家事,她父亲做过查封官,与霍尔堡是朋友。他们俩不论是在屋子里,还是散步,只谈一个话题“政治”。一天,她的母亲在纺车边上想加入他们的谈论。“纺车吱吱叫了。” 霍尔堡说,母亲不认为风趣的老绅士这是玩笑话,而不原谅他。老夫人那时很小,总是奚落瑞瑟尔的诗人韦塞尔也常来她家,他的描写火的可怕故事路人皆知。他把自己的鞋和丝袜让给穷人穿着,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回家。
她每天都读古典名著,看完书后,就和我谈他们对景致的描写、人物刻画的技巧和他们崇高的思想。所以,她很难理解更为现代的浪漫主义诗歌,也不去欣赏。她和天下的母亲们一样思念自己的孩子,她被流放的儿子,在战时曾以岛国国王的身份出现在冰岛,就像童话一样。她时常以热烈的感情谈起儿子,回忆他儿时的举止行为,她分析认为他坚强的性格在孩童时就已显露无遗,这也是他为什么再也不能回丹麦的原因之一。老夫人的整个人生、思想和阅历都震撼着我的心灵,深深地吸引着我向她靠近。而对她来说,我只是个单纯的能使她愉悦的孩子,她喜欢的伴。我把自己写的悲剧《森林里的教堂》,还有一些最初的诗作读给她听。一天听后,她表情郑重地说:“你是个诗人,或许能和欧伦施格尔一样伟大!唉——再过十年,那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但不要忘了我,要记住我啊。”我的眼泪瞬时就流淌了出来。她的话里有我不明白的,也有一些高贵的东西在里边。在被她的话迷住时,我也疑惑着。我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名诗人,像欧伦施格尔一样伟大的诗人。
“真的,你还是要去上学。”她说,“但是,也许你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条条马路通罗马。”
“你得去上学。”这是一句每天都能听到几遍的话,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对我说这句话,上学是如何好,对我的人生是多重要。人们鼓励我上学,好多人因我不上学,表现出怒其不争的神色而责骂我。我这样的年纪,上学是本分,不上学又能干什么?再说,我也知道那是绝对必要的。可是我让自己活着已经够费劲儿的了,没人具体帮助我,上学的事情变得困难了,总得想个法子。我忽然眼前一亮,有了好主意:写剧本,交给皇家剧院。戏要是上演,钱就来了,上学就不会有问题。我照着罗森吉尔德的一篇德语短篇小说《信鸽》,写了一出悲剧。我请古德伯格看看这篇无韵诗体的悲剧,他读了认为练练语言还好,坚决不同意我把这样的剧本交给剧院。无奈,我又写了一出戏,以我自己的故事为蓝本,不对他说作者是谁。起名叫《威森博格的强盗》,这是一出“爱国主义的悲剧”。我写得很快,不到两星期就完稿了,但因没人帮我,单词的拼写基本上没有一个对的。我没有署名把它交到剧院。但是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送过我玫瑰花的汤德·伦德小姐,她是我在家乡行坚信礼时唯一对我表示友好的人。我到哥本哈根去时看过她,在她家给我引见了一个人,她也对科伯乔森母女满怀同情地谈过我的状况。由于我不想让人认出我的字体,她花钱请人帮我修改成更易读的文本并寄了出去。在焦虑的期待中等了六个星期,剧本退了回来。退稿信上说,这种连最起码的基础教育都欠缺的剧本以后就不要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