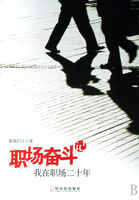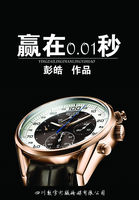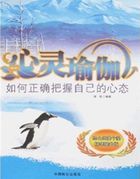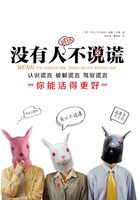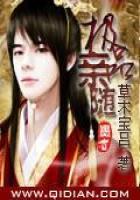4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已经陷入了怎样的境地,这种情况有如沙尘暴刮进了北京城。但是,普遍荒漠化的时世,并不能排除个别作家凭借自身独特的精神关怀和天赋品质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另类,成为沙漠里一棵葱翠的橄榄。
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是一种呻吟和呐喊,尽管它也可以是一种歌咏、一种娱乐,甚至一种笑料。作为呻吟的文学是病人的职业,而且,这种病还不是经常在人民医院门诊部看到的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皮肤感染。可以这么说,文学所具有的深度与作家所患有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他的病不应该是青霉素、红汞水等药物所能够救治的,他的呻吟必须是从内心最本质的地方发出来的,不然就被视为矫情的作秀。为此,他的病灶还不能在肌肤、手足,甚至还不能在血气,而必须在脏腑之内、骨髓之中,甚至形骸之外。也就是说,他的病必须是致命的,他已经病入膏肓,阻碍到身心的运行,毒化了生存的体验。这样,文学才能成为神奇的药石,才能妙手回春。
然而,在当代中国,你很难找到这样的病人,人们都似乎活得很健康、很正常,红光满面。即便有病的人也喜欢装出一副健康的样子,把呻吟变成唱歌,因为人总是有病,病死了也就算了。他们当中,有的人目前活得左右逢源、志得意满,在滚滚尘埃中呼吸顺畅、心跳均衡;有的人活得困窘、尴尬、狼狈,踉踉跄跄,气喘吁吁,但他们内心渴望有一天成为一个左右逢源、志得意满的人。尽管遭际不同,住的房子、睡的床都不一样,但他们却做着同样的梦,因为这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最好的风光景色了。应当说,这一切都是无可厚非的,穷的时候渴望温饱,温饱之后希望位列中产阶级,跻身中产阶级之后又想要晋级贵族阶层,在这条路上,人们才刚刚举步,远没有走到尽头。因此,他们没有面对“末日的审判”。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学,只能是流水落花的日常生活抒情,以及婆婆妈妈或泼妇骂街的社会批判。我们理应满足于此,不应该有更多的期待。因为,即使有另外气象的文学出现,我们也不一定能看明白它真正的意思。
世界文学史上有一些作家因为病情的严重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托尔斯泰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诚心希望做一个好人,但在当时俄国的社会风尚中,这种愿望并没有得到支持。当他追求美好的事物时,他感到孤单无靠;当他透露出想做一个行为高尚的人时,遇到的却是鄙视和嘲弄;而当他沉溺浸淫于物欲的逸乐之中时,却得到赞扬和夸奖。他的姑妈总是鼓动他找个有夫之妇私通,希望他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娶一个非常有钱的女人为妻,并通过陪嫁拥有尽可能多的土地和奴隶——这是她所能够想象的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在这种风尚训导下,托尔斯泰伯爵生活腐化、对爱情不忠、偷鸡摸狗、通奸、酗酒、赌博、撒谎、斗殴、杀人,因此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重和羡慕。在这种生活中泡了十年之后,他开始写作。作品对美好事物和善良愿望的冷漠和蔑视,又为他赢来众人的激赏,他很快就声名鹊起,体会到以少量劳动换来大笔金钱和隆重荣光的乐趣。尽管自得之余也有惶惑的时候,但从欧洲流行过来的进步观念告诉他:怎么叫先进就怎么过吧,一切都会在发展中见分晓的。直到又过了十五年之后,他出现了奇怪的病情。
“开始我发现自己有这么几分钟晕头转向。生活停止了,似乎不知道我该怎么生活,该干什么。我手足无措,情绪消沉,但几分钟过去以后,我照过我的日子。后来这几分钟的晕头转向以同样的表现形式屡屡出现,越来越频繁。”(托尔斯泰《忏悔录》)一个问题闪电似的不断向他袭来:“你在萨马省将要得到六千亩地、三百匹马,那很好,以后呢?”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强迫他摆脱原来的生活,甚至还要摆脱自己的生命,直到知天命的五十岁那年,他都还想着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独宿,脱了衣服把带子拿到房间外面,免得把自己吊死在衣橱的横梁上。出去打猎也不敢带火枪,免得经不起诱惑轻易把自己毙掉。
这个时期的托尔斯泰健壮如牛,家庭美满,财源广进,威望崇高,几乎成了俄国幸福生活的典范,不知有多少人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他这样的人。但是,他在原来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他的灵魂染上致命的病毒。正是这场无药可治的病,成就了作为《复活》《天国在我心中》作者的托尔斯泰。
比托尔斯泰稍早一些岁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当上帝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倒下,欧洲的精神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作为一切价值和规范的最后基石已经抽空,辉煌的太阳坍塌成可怕的黑洞,人们一时找不到可以补天的岩石。在小心翼翼地绕开这个黑洞之后,他们的生活仍然可以继续,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怎么也绕不过去,在这里停了下来。他敏感的心灵洞察到一个恐怖的事实: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包括杀人、放火等原来不可饶恕的行为,而那些坚持道德情操的人便成了可笑的白痴,这个世界也将沦为群魔乱舞的地狱。这个发现令他感到末日的惊惶,于是,他和尼采一起成为这场精神危机的受难者。
在中国作家中,不能说没有病人,但病得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严重的患者却很难找。鲁迅算是中国作家中病得最深的人了。和鲁迅同时代生活的中国人有几万万,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也数不胜数,但他们都没有鲁迅那么深邃的关怀。在民族危亡、战乱绵绵的时代,人们只想到要驱除外敌,实现独立和平;在专制黑暗、人性桎梏的时代,人们只想到要建立共和,实现自由;在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时代,人们只想到要发展经济,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但鲁迅犀利的目光穿越了这一切,他看到了别的,以及别的后面的别的。从国家、民族、社会、阶级到人性和必有一死的宿命,鲁迅深感人生问题的重重不尽,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因此,他心事浩茫,百感交集,任何表面的荣华都欺瞒不了他,他也不会因为某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得到暂且的解决,就以为万事大吉,因而得意忘形,露出妩媚的笑容。他笔力的透彻和文气的磅礴由此而来。倘若没有在娜拉出走关门声中问一个“以后呢?”鲁迅跟那个时代的作家不会有那么大的区别,但他在“以后”之后还层层追问。
5
找不着身负沉疴的病人,是因为中国当代生活健康状况良好,还是因为人们都像当年的蔡桓公那样病入骨髓而不自知,仍然以健康者自居?倘若是后者,病情反而是更为严重——真的是病入膏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