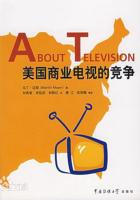由于古代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梦的认识还不可能达到潜意识观这样高度的抽象。但是,中国学者早就把梦作为一种独特认识的对象,很早就出现了潜意识概念的萌芽。特别是到宋明时代,在“醒制卧逸”、“梦之精神”和“神蛰”、“神藏”、“志隐”一类的思想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潜意识概念的雏形。
2梦的原因和机制
人为什么会做梦,这是历来人们要回答但又众说不一的问题。人的梦,不管梦象多么虚幻离奇,但总有它产生的原因;而这种原因绝对不能离开做梦者本身。在中国古代,人们先是分别从生理病理和精神心理这两个方面去寻找梦因。
(1)梦的生理病理原因和机制
中国传统医学非常重视梦的生理基础,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医学家就从生理病理方面探索了梦的原因和机制。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黄帝内经》一书中。
《黄帝内经》释梦的主要观点是:梦是人心身交互作用的结果。梦对人的身体状况来说,主要反映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反映生理机能状况,如“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二是反映本能欲望,如“客于阴器,则梦接内”;三是反映病邪致病的位置,如“客于肝,则梦见山林树木”;四是反映脏器的盛衰,如“肝气盛,则梦怒”;五是反映病症轻重,恶梦往往是重病的先兆,如“少气之厥,令人妄梦”。
《黄帝内经》中《灵枢·淫邪发梦》中对梦的产生及其各种梦象作了考察,认为人在睡眠中,“正邪从外袭内”,不但可以影响人的五脏,而且可以影响人的六腑。这些影响必然使人的脏腑发生各种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出来就是脏象。“脏象”的含义既是指藏于人躯壳之内、具有一定形态的内脏组织器官,又包括了这些内脏器官生理活动的功能现象。“象”是“脏”(藏)的外在反映,“脏”(藏)是“象”的内在本质。“脏象”是人体系统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体。《内经》认为,脏象的变化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脏气有余,属于人体机能亢进的表现;另一种是脏气不足,属于人体机能衰弱的表现。有余和不足又有内外之分。无论如何,脏象的变化都对梦象产生影响。
这种“淫邪发梦”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第一,它证明了睡眠过程中的外部刺激,可以诱发睡者产生梦象。第二,它论证了睡眠中梦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第三,它阐明了睡眠中的梦象活动是人的精神失去控制状态下的产物。此外,它试图根据梦的内容而确定身体患病部位,在实践中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淫邪发梦”注重脏象同梦的关系,在古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对梦同大脑的关系则长期无人过问。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医学临床经验的不断丰富,人们越来越重视脑的地位和功能。清乾嘉时期医学家王清任撰写了《医林改错》一书,第一次把梦同脑髓联系起来。他在《脑髓篇》中写道:“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梦多是由于“脑为邪热所扰”的观点。这种梦因说,从它致梦的外部条件看,仍是“淫邪发梦”说的继续。生活或医学临床中,因病确会致梦,但健康人同样会做梦,只是不像由疾病所致的恶梦。惊梦、怪梦印象深而醒后易忘而已。所以健康人似乎少梦,但确实有梦,那是什么原因呢?王清任自然是难以弄清,他只好笼统地说:“夜睡梦多,是脑为邪热所致。”在中国古代史上,把梦作为人脑活动的产物,王清任是第一个,他打破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心卧则梦”的传统观念,这一点超过了前人。
东汉后期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梦列》中把梦分为十类,其中“感梦”、“时梦”、“病梦”主要是生理病理原因所致。“感梦”即“感气之梦”。阴雨、阳旱、大寒、大风之类在人睡眠中刺激人体使人有所感,感而即产生厌迷、乱离、怨悲、飘飞等梦境或梦象。“时梦”注重四时节气自然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梦象,肯定了时象对梦象的影响,“病梦”肯定病会致梦,不同的病有不同的梦,这同《内经》论脏气盛衰虚实之梦,实际上是一致的。
东晋时张湛所注的《列子》一书,从哲学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感变”这一概念,肯定了梦有“所起者”和梦之“所由然”,并揭示了梦寐中外感和内感的联系。他认为无论是醒觉还是睡梦,人的精神活动都是一种“感变”,即由感而变、由变而生,所以都有原因可寻。懂得了这一点,不论是什么恶梦、怪梦、惊梦都没有什么可怕。从一体之“通于天地、应于物类”看,睡梦来自外感;从“一体之盈虚消息”看,睡梦又来自内感。“饥梦取,饱梦与”、“病则梦医”。“感变”不仅对于梦的生理病理原因进行了集中概括,而且把睡梦放在人与大自然的大系统中去考察,承认人同天地自然间有一种交感关系。
(2)梦的精神心理原因和机制
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注意梦的精神心理原因的,不是某些方面的科学家,而是周王身边的占梦官。占梦官把梦分为六种,即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占梦官认为“六梦”有吉有凶,并以“日月星辰”占其吉凶。“六梦”的划分,首先根据的是梦的内容及其心理特征。这里我们不是说周正的占梦官已经自觉地探讨了梦的精神心理原因,而是说他们在占梦过程中已经接触到问题的这个重要方面。因为占梦者要追求应验,而要能够应验,就不能不注意到各种梦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原因。
战国时慎到曾说:“昼无事者夜不梦。”《云笈七签·养性延命论》引《慎子》佚文。“昼无事者”就是说白天没有某种活动所产生的印象,或对某种活动没有感受,就没有相应的心理活动,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梦境、梦象。反过来说,“昼有事”者,即对某种事情在白天有所见闻并有深刻的感受,夜间就会反映在梦中,可见白天的心理活动在夜间会一定程度地转化为梦象活动。这种体验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体验?
东汉的王符在《潜夫论·梦列》中谈到“精梦”、“想梦”、“性梦”时,就曾指出这三种梦不是外界因素所诱发,而主要是精神心理因素所致。王符解释道:孔子生于乱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此谓精梦也。”所以,孔子崇拜周公,整天想着复礼以匡救天下。“人有思,即梦其到;有忧,即梦其事。此谓想梦也。”什么是“想”呢?“昼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也。“人之心情,好恶不同,或以此言,或以此凶……此谓性梦也。”这里讲的“性”虽涉及到梦者的心理状况,但主要不是讲梦因,而是讲梦者对梦的态度。
然而,由于人在白天所思、所想、所念者,可以是从前所闻所见之事,也可以是从前未闻未见之事。因而梦象既可以真实地再现所闻所见之事,也可以虚幻地显示未闻未见之事。总之,“精念存想”主要是精神心理因素所致。
梦象中人往往会变成鱼、鸟等动物,或者一会儿是鱼,一会儿又是鸟,过一会儿又是蝴蝶。东晋张湛在其《列子注》中说:“此情化往复也。”众所周知,庄子曾说他“梦为蝴蝶”,但事实上终庄子一生也从未变成过蝴蝶,这就要从他的精神心理因素中去寻找他的蝴蝶梦的梦因了。庄子追求一种“无待”的自由,“逍遥游”是他的理想境界,梦为蝴蝶正是他精神心理的活动,他羡慕蝴蝶的自由,想像着像它那样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这种梦象就是情化往复所致。
梦象虽然是“情化”所致,然而并不是任何“情化”都可以见之于梦象。由“情化”转变为梦象,这种感情必须是强烈的、持续的、不变的。北宋李觏在其《潜书》中所说“心溺”则梦和明陈士元在其《梦占逸旨》中所说“情溢”则梦,都是强调“情化”必须有一定的深度和强度。
清代康熙年间,熊伯龙在其《无何集·梦辨》中提出“忧乐于心”则梦的命题。从他所举梦例来看,梦是“忧乐存心所致”,说的是有的梦是“乐之存心所致”,有的梦则是“忧之存心所致”,前者当属于喜梦,后者则属惧梦。这说明,不同的精神心理状态产生不同的梦象。
当然中国古代由于对人的心理矛盾重视不够,对梦的心理分析一般比较简单,很少有对复杂梦例的分析。
总之,做梦既有生理病理原因,又有精神心理原因,中国古代学者早就有所认识。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种梦因只是分别平行地被探索。直到西晋有一个名叫乐广的人提出了“想”和“因”两个范畴,才开始从理论上说明二者的关系和联系。明代王廷相继续把两种梦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着名的“因衍”概念,把中国古代对梦因的认识提高到最高水平。
二、中国古代占梦活动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宗教史上,一方面有道教、佛教等一些有组织的宗教,同时又有许多非组织的世俗迷信。占梦就是一种占卜迷信,主要是根据梦象来预卜梦者在未来的凶吉。中国古代道教、佛教等宗教无不把占梦作为一种神学工具,用以证明灵魂不灭和鬼神的存在。在古代哲学史上,神道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又常常借用梦的迷信否定精神对物质的依赖关系。
由于梦是人们自身的一种体验,占梦正是以这种自我体验作为沟通神人、预示吉凶的中介。因此,较之其他占卜活动,占梦更具有一种神秘性和诱惑力。在所有占卜术中,以占梦最为发达,因此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众占非一,而梦为大”的说法。
占梦最初起源于原始先民幼稚的梦魂观念,以为做梦是灵魂离身而外游,而灵魂外游又为鬼神所指使,由此梦被归结为鬼神对梦者的启示,于是出现了梦兆迷信,进而根据梦象体察神意,预卜吉凶。
可以说,梦魂观念是梦兆迷信的思想基础,但它本身并不等于梦兆迷信。只有把梦魂观念同鬼神观念联系起来,并已把梦看成是神灵或鬼魂对梦者的启示,才能出现梦兆迷信。
中国古代的占梦始于何时,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材料缺乏,已难以考证。仅根据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提到占梦最早的人物是黄帝,其中记载:“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醒后黄帝自我分析为:“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黄帝“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力牧两位名臣。转引自《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黄帝时代的占梦活动仅系远古的传说,因为那时我国有没有文字都大成问题,即使有文字也是比甲骨文还要早的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怎么可能运用析文解字来占梦呢?显然,黄帝占梦系后人附会之说。不过,那时是否还有其他方式的占梦,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在中国历史上,从殷人开始,梦和占梦才有了可靠的记载。甲骨卜辞中有关殷王占梦的记载很多。而且殷王总是问太卜,其梦有祸没有祸?其梦有灾没有灾?这说明,殷王对其梦的吉凶非常关心。也说明,占梦在殷王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知为什么,殷王的鬼梦特别多。在殷人看来,殷王之所以做梦,主要是殷人先公先王或先妣在作祟。因此,每当殷王夜有异梦,总是占问是不是来自某一位先祖。经过占问,如果认定是某一先祖作祟,必定要举行隆重祭祀。殷王多鬼梦和怕鬼梦,与此相联系,占梦时多着眼于梦的消极方面的预卜,凡殷王遇鬼梦总是问有没有祸乱,有没有灾孽。其他梦景、梦象一般也是这样占问。“有没有喜幸”的占问从未见过一例。大概由于这个缘故,殷王尽管无事不占,并设有太卜专管占卜之事,但占梦在整个占卜中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占卜活动主要是占龟,占梦只是占龟的一部分。
甲骨卜辞综观殷墟甲骨文的占梦卜辞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殷人视梦为接受先人信息的重要场所,先人信息的发出者是先王、先公、先妣,占梦是对梦中所得先人信息的解读;占梦是现实行为的依据。梦在殷人心目中是最高级的知觉方式,而占梦则是他们与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们的某种神秘力量交流的基本语言。谁能掌握这种语言,谁就拥有政权,这就是殷人的占梦观念。
周人是十分看重梦与占梦的,凡遇国家大事都须占梦而定。周人占卜某事吉凶时是占梦、占龟、占易三者相参。据《周礼·春官》记载,总占卜官为太卜,执掌有关占梦、占龟、占易的“三梦之法”、“三兆之法”、“三易之法”,并以“三梦”、“三兆”、“三易”之占的结果观国家的吉凶。“吉则为,否则止”,并对凶兆采取补救措施,周王在太卜之下设有专职的占梦官,执掌占梦之事。
周人重视占梦是有其渊源的,据说周文王和武王在灭殷之前都做过不少吉梦,预示着天命周人取代殷商。《帝王世纪》说周文王曾梦见“日月着其身”。日月是帝王的象征,这显然是说周文王受命于天。这样的梦,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虚构。但周王对梦的态度,似比殷王更为认真和恭敬,占梦在周人政治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占为吉梦,更要向上帝神明膜拜,以感谢上天的保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