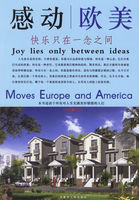拉瓦锡最重要的发现是燃烧原理,这是他对化学研究的第二大贡献。伟大的科学家描述了最重要的气体:氧、氮和氢的作用。之所以能够有此发现,是因为他第一次准确地识别出了氧气的作用。事实上,科学家确认燃烧是氧化的化学反应,即燃烧是物质同某种气体的一种结合。拉瓦锡为这种气体确立了名称,即氧气,事实上就是“成酸元素”的意思。
拉瓦锡最终排除了当时流行极广的关于“燃素”的错误看法。按照那种理论,在燃烧期间,任何被燃烧的物质同一种被称为“燃素”的物质相分离。“燃素”被认为是整个燃烧过程的主导者。
拉瓦锡还识别出了氮气。这种气体早在1772年就被发现了,但却被冠以一个错误的名称——“废气”(意思是“用过的气”,也就是没有燃素的气,因此不会再被用作燃烧的气)。拉瓦锡则发现这种“气体”实际上是由一种被称为氮的气体构成的,因为它“无活力”(来源于希腊语azofe)。后来,他又识别出了氢气,这个名称的意思是“成水的元素”。拉瓦锡还研究过生命的过程。他认为,从化学的观点看,物质燃烧和动物的呼吸同属于空气中氧所参与的氧化作用。
1772年秋天,拉瓦锡照习惯称量了定量的红磷,使之燃烧、冷却后又称量灰烬(五氧化二磷,P2O5)的质量,发现质量竟然增加了!他又燃烧硫黄,同样发现灰烬的质量大于硫黄的质量。他想这一定是什么气体被白磷和硫黄吸收了。于是他又改进实验的方法:将白磷放入一个钟罩,钟罩里留有一部分空气,钟罩里的空气用管子连接一个水银柱(注:测定空气的压力)。加热到40℃时白磷就迅速燃烧,水银柱上升。拉瓦锡还发现“1盎司的白磷大约可得到27盎司的白色灰烬(P2O5)。增加的重量和所消耗的1/5容积的空气重量基本接近”。
拉瓦锡的发现和当时的燃素学说是相悖的。燃素学说认为燃烧是分解过程,燃烧产物应该比可燃物质量轻。他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交给法国科学院。从此他做了很多实验来证明燃素说的错误。在1773年2月,他在实验记录本上写道:“我所做的实验使物理和化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将新化学命名为“反燃素化学”。
1775年,拉瓦锡对氧气进行研究。他发现燃烧时增加的质量恰好是氧气减少的质量。以前认为可燃物燃烧时吸收了一部分空气,实际上是吸收了氧气,与氧气化合,这就是彻底推翻了燃素说的燃烧学说。
1777年,拉瓦锡批判燃素学说:“化学家从燃素说只能得出模糊的要素,它非常不确定,因此可以用来任意地解释各种事物。有时这一要素是有重量的,有时又没有重量;有时它是自由之火,有时又说它与土素相化合成火;有时说它能通过容器壁的微孔,有时又说它不能透过;它能同时用来解释碱性和非碱性、透明性和非透明性以及有色和无色。它真是只变色虫,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它的面貌。”
1777年9月5日,拉瓦锡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划时代的《燃烧概论》,系统地阐述了燃烧的氧化学说,将燃素说倒立的化学正立过来。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逐渐扫清了燃素说的影响。化学自此切断与古代炼丹术的联系,揭掉神秘和臆测的面纱,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实验和定量研究。化学由此也进入定量化学(即近代化学)时期。
拉瓦锡对化学的第三大贡献是否定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四元素说和三要素说,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化学元素的概念:“如果元素表示构成物质的最简单组分,那么目前我们可能难以判断什么是元素;如果相反,我们把元素与目前化学分析最后达到的极限概念联系起来,那么,我们现在用任何方法都不能再加以分解的一切物质,对我们来说,就算是元素了。”
在1789年出版的历时4年完成的《化学概要》里,拉瓦锡列出了第一张元素一览表,元素被分为四大类:
(1)简单物质,光、热、氧、氮、氢等物质元素。
(2)简单的非金属物质,硫、磷、碳、盐酸素、氟酸素、硼酸素等,其氧化物为酸。
(3)简单的金属物质,锑、银、铋、钴、铜、锡、铁、锰、汞、钼、镍、金、铂、铅、钨、锌等,被氧化后生成可以中和酸的盐基。
(4)简单物质,石灰、镁土、钡土、铝土、硅土等。
含冤而死
拉瓦锡曾在政界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对此,他曾感到负担过重,曾多次想退出社会活动,回到研究室做一个化学家。然而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当时,法国的国情日趋紧张,举国上下有如旋风般的混乱,处于随时都可能爆发危机的时刻。对于像拉瓦锡这样大有作为、精明达识的科学家的才能也处于严重考验的时期。
这时,似乎百年前波义耳在英国的处境,现在又转移到拉瓦锡所在的法国来了。国情是很相似的。但是这两位科学家的命运却截然相反。波义耳不闻窗外的世间风云,只是一心关在实验室里静静地进行研究。而在同样处境下的拉瓦锡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应当说是一种命运的不幸,而且这种不幸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点,以至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拉瓦锡不论在何处都像是一棵招风的大树,因而每当雷雨一到他便成了最危险的那一棵。最初的一击是来自革命的骁将马拉(J·P·Marat)之手。马拉曾经也想做一名科学家而取得荣誉,并写出了《火焰论》一书,企图作为一种燃烧学说而提交到了科学院。当时作为会长的拉瓦锡对此书进行了尖刻评论,认为并无科学价值而予以否定。可能因此而结下了私怨。马拉首先叫喊要“埋葬这个人民公敌的伪学者!”到了1789年7月,革命的战火终于燃烧起来,整个法国迅速卷入到动乱的旋涡之中。
在这块天地里,科学似乎已经没有容身之所。实际上所有的法国学术界,诸如学会、科学院、度量衡调查会等,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甚至还有一种不正常的说法,认为“学者是人民的公敌,学会是反人民的集团”等。在此情况下,拉瓦锡表现得很勇敢。他作为科学院院士和度量衡调查会的研究员,仍然恪守着自己的职责。他不仅努力于个人的研究工作,还为两个学会的筹款而四处奔走,甚至无偿地把私人财产作为同事们的研究资金。他的决心和气魄,成了法国科学界的柱石和保护者。
但是,意想不到的恶敌却早已潜伏着。他就是化学家佛克罗伊(Fourcroy,1755—1809)。他本人也是科学院的院士,曾经是一位很早就同革命党人的国会有着密切联系、并对科学院进行过迫害的神秘人物。他在危难之际,也曾在多方面受到过拉瓦锡的保护,但是却施展诡计企图解散科学院,直到最后动用国会的暴力而达到了目的。于是,1793年4月,这个从笛卡儿、帕斯卡和海因斯以来具有百余年光荣历史的科学院遭到了破坏(直到1816年巴黎的科学院才又得到重建)。
这时,拉瓦锡通过教育委员会向国民发出呼吁。他指出,教育界的许多元老,曾经为法国的学术繁荣而贡献了毕生精力,然而现在他们的研究机关被剥夺,衣食的来源被切断,宝贵的晚年受到了贫困的威胁,学术处于毁灭的边缘,法国的荣誉被玷污了。如果学术一旦遭到毁灭,恐怕就是再经过半个世纪也难以再得到恢复了。他虽然这样提出了警告,但结果仍然无效。
1793年11月28日,包税组织的28名成员全部被捕入狱,拉瓦锡就是其中的一个,死神越来越向他逼近。不久,度量衡调查会的6名研究员被开除,其中也有拉瓦锡。
学术界震动了。各学会纷纷向国会提出了赦免拉瓦锡和准予他复职的请求,但是,已经被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激进党所控制的国会,对这些请求不但无动于衷,反而还更加严厉了。1794年5月7日开庭审判,结果是把28名包税组织的成员全部处以死刑,并预定在24小时内执行。
佛克罗伊所采取的阴险手段,对于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无疑起了很大作用的。佛克罗伊是巴黎植物园化学研究室的教授,曾长期和拉瓦锡在一起,也为化学理论和化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本是一位知名的学者。但是为什么却会进行这种恶劣的活动,是不是由于长期以来对拉瓦锡的嫉妒呢?后来,当罗伯斯庇尔失败以后,在为拉瓦锡举行的庄重和盛大的追悼会上,这个厚颜无耻的佛克罗伊却又反过来对拉瓦锡表示悼念,还做了歌功颂德的演讲。像这样卑劣的人,在古今的科学家中恐怕也再难找出第二个人了。
拉瓦锡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人们虽然在尽力地挽救,请求赦免,但是遭到了革命法庭副长官考费那尔(J·B·Coffinhal)的拒绝,全部予以驳回。他还宣称,“共和国不需要学者,而只需要为国家而采取的正义行动!”
第二天,5月8日的早晨,就在波拉斯·德·拉·勒沃西奥执行了28个人的死刑。拉瓦锡是第四个登上断头台的。他泰然受刑而死……著名的法籍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瞬间把他的头割下,而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许长不出一个来。”
有一种传说,拉瓦锡和刽子手约定头被砍下后尽可能多眨眼,以此来确定头砍下后是否还有感觉,拉瓦锡一共眨了15次,这是他最后的研究。这一传说不见于正史。
拉瓦锡的一生是令人崇敬的一生,是光芒四射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