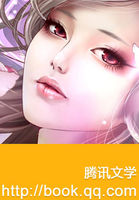夜天题的冷静与寂然让她不得不有了认知,现在的夜天题,让她琢磨不透了!
“喂,喂,你们知不知道皇城出了大事了!”
“哦?什么事,什么事!”酒楼的一角人们蜂拥过去,把说话的人堵在中间。个个伸长了耳朵。
只听得方才那个声音说:“你们听过麦香伊人吗?”
“没有!”众人异口同声。
“麦香伊人啊,就是皇上最新宠的一个妃子,姓麦名伊人!”
“那香字呢?漏掉了!”
那人干咳了一下,道:“香是形容这个妃子身上有异香!”
众人若有所悟的哦了一声,又凑近了头颅急问:“那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啊?”
“这个麦香伊人被处死了,极刑啊,被活活烧死的,皇城里的烽火台上,整个皇城都看到了那熊熊燃烧的惨状!”
人群中一片唏嘘哀叹声,又有更多的人围上去,竖着耳朵听!
人们啊,就是这样,总是让别人的死来为自己无聊平静的生活增加谈资。
“为什么烧死啊?这不是皇帝的宠妃吗?”
那人又压低了声音,“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宠妃早被打入冷宫了,还有啊,京城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据说啊,这个麦香伊人啊,和皇上,是彼岸花命格,相克,你们没听说皇朝这些日子的衰运吗?就是这个人搞的鬼,哎呀,据说这次是因为杀尽宫中的妃子,又企图在祭皇陵准备的酒中下毒和布置炸药,所以皇帝忍无可忍,要除这妖女以后快!”
“哎,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一个人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们离皇城那么远,你从哪听来的?臭小子,不知道就不要乱讲啊!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你们不记得当年有多少人死于那场宫变了吗?老朽记得!”一个老年书生模样的人,舔了舔几乎空无一物的杯子,用手指弹了弹破旧的儒生衣衫,很高兴众人的焦点转移到他身上去了!
一阵更低声音的交头接耳之后,众人似是懂了的纷纷点头,叹道:“我还是支持大皇子!”
夜天题是抱着阮宁波回的客栈厢房。
那个女子自从听完那一席话后,就再也没出声音,就那么呆呆的支着头,望着不知何处的远方。
许是在想皇帝是怎么样的心情举着火把,点燃她身边的枯柴的吧?阴狠决辣还是大义凛然?
在替阮宁波掖被角的时候,夜天题大手抚上女子的发,“不要忘了,你的人,是在这里的!”
阮宁波的眸子依然未动,睫毛眨了眨,垂眉道:“我知道,我想休息了,天题!”
“现在,你,已经回不去了!”
“我知道!”女子淡淡的答,扬起头问:“如果祭皇陵郎东昱回不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夜天题默然,与她相对,半晌,阮宁波道:“我明白了,皇朝的司酒礼仪,我还是知道的!”慢慢慢慢的退进被子里,闭上眼眸的阮宁波轻轻道:“让我静一静吧,天题!”
这个女子何其聪明,她肯定猜得到,郎东昱若是回不来,会有什么后果!而他此刻的沉默,肯定会招致这个女子无比的怨愤。
夜天题没有想到,他为阮宁波留的静思哀伤的空间,这个女子竟全用来逃离他,等到他终于回房时才发现,本应该躺在床上休息的人,象蒸发了一样!
如果阮宁波在躲你,那你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是夜天题寻了两日无果后,得出的结论。
此时距离皇陵祭祀的时间,不过两天而已。
而一直忧心于阮宁波安危的夜天题也不会发现,他的行礼中少了两样东西,一幅画和一张字条,那是在平垠王宫中偷那些裸画时顺手牵羊的。
若我不是皇帝,你会作何选择?
如若你选择回宫,又是为何?
一盏茶的时间。
你还没想出答案吗?
那我来告诉你,我的答案。
不管我是不是皇帝,我都是一个男人,一个普通平凡的男人。
恋上一个叫阮宁波的女子,的男人。
郎东昱。
阮宁波从来没有想到,那幅画中还有这样几行字。
她曾问过那幅画为何那般诡异,郎东垠只是老神在在的说,有两种颜料很特别,用海南珠脂调和色料画的,只有夜间能看见,用沃焦山石磨色画的,则只有在昼间能见。
没有对那幅画做过多的追究,也因为画上并没有落款,所以并没有猜到是郎东垠的画作,现在想来,阮宁波脑海中全是缠着人的锁链,而那个人,是郎东昱。
那个女子心情烦乱的,疯狂赶路,夜天题实在是把她带到了够远的地方,让她想急切奔回去的里程,显得格外漫长!
如果郎东昱不能及时回去祭皇陵大典,那必会有另一皇子代替,当然,郎东垠是不能选择的,那,只有郎若虚!
什么在祭皇陵的酒中下毒,埋藏炸药,听起来荒诞不羁,似乎子无须有,但,任何事不会是空穴来风,如此的说法,让阮宁波在脑海中清晰的下了一条结论,郎东昱那似乎是在梦中说的话,十日之后,等我回来,似乎,不像是梦!
而远在异国的郎东昱,染满奔波之霜的面颊上,因为听到的消息而仰天啼血,纷红的血丝在天空曼舞,落在手中的那把看似墨黑的剑上,一片流光溢彩。
然后倏然消退,象低嚎出的某人名字,短促而堂皇。
“皇上,皇上!”杨勇叫着,扶住郎东昱线一样倒下的身子,声音短促惊偟,“皇上,你真的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