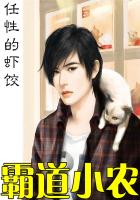临近中午,大儿子听蝈蝈叫的兴致渐渐衰退,二儿子逗蟋蟀也觉得乏味了,可小儿子还没有回来。日薄西山了,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的时候,他才气喘吁吁地走进家门。他满脸汗水,浑身污垢,简直成了一个泥巴人。
“怎么会如此狼狈?我的孩子。”母亲关切地问。
“嗨,这一整天简直是倒霉透了。”小儿子便对母亲诉说他的倒霉事情,“我用您给我的钱租了一根鱼竿,买了一些鱼饵,要去郊外的湖边钓鱼……”
“我不记得你会钓鱼呀?”母亲说。
“是的,我不会。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会钓鱼。”
“学会了吗?”
“没有。我拴好鱼饵,下好竿,可我总是把不准起竿的时机,不是早了就是晚了。好几次,我挑起竿~看,鱼饵都吃光了,该死的鱼却逃跑了。最后一次我把鱼饵全部放上去,要钓一只大鱼。这下子倒真的钓着一只大鱼,可惜我拽不动,结果我被拉下了水,大鱼把鱼竿也拖到湖中央去了。”说到这里的时候,两个哥哥都哈哈大笑起来。
“鱼竿可是租的,你怎么办呢?”
“是呀,我打算下水捉鱼。弄几条大鱼给鱼竿主人,他或许一高兴,就不叫我赔钱了。”
“捉住了吗?”
“摸着不少,可一条也没有捉住。那些鱼都很油滑,刚触到鳞片,它们就像精灵一样溜掉了。”
“我猜想你肯定在浅水里摔过很多跟斗。”
“可不,一尺多长的大鱼在水面掀起浪花,很有冲劲呢。我有好几次被它们掀倒。”
“给我讲讲你跟鱼竿主人交涉的情况吧。”
“我跟他一五一十地说了,请他原谅。可他最后还是让我做了四个钟点的小工,才算了结。”
“人家还是优惠你了呢。”这时候母亲也忍俊不禁了。
“可不是。他说再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仅仅是扫地、倒垃圾、整理货架,还要……”
“肯定是这样,这很公平。不过现在让我关心一下你们兄弟的快乐故事吧——哥哥们用钱去买快乐,但你们买到的是玩物,不是快乐,你们几乎没有什么过程可以回味;弟弟虽然一无所获,但快乐的过程却回味隽永。孩子们记住,快乐是不能购买的,快乐不是玩物,而是丰富的人生体验。”
老人再次笑了,笑得有点甜蜜,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两人恩爱无比的甜蜜日子里。
真正的爱,在自己心间
尹玉生/文
那是一个忙碌的早晨,大约8点半,医院来了一位老人,看上去80多岁,是来给拇指拆线的。他急切地对我说,9点钟他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希望我能照顾一下。
我先请老人坐下,看了看他的病例,心想,如果按照病例,老人应去找另外一位大夫拆线,但至少得等一个小时。出于对老人的尊重,正好我当时又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就来为老人拆线。
我拆开纱布,检查了一下老人手的伤势,知道伤口基本上已经痊愈,便小心翼翼地为老人拆下缝线,并为他敷上一些防止感染的药。
在治疗过程中,我和老人攀谈了几句。我问他是否已经和该为他拆线的大夫约定了时间,老人说没有,他知道那位大夫9点半以后才上班。我好奇地问:“那你还来这么早干什么呢?”老人不好意思地笑道:“我要在9点钟到康复室和我的妻子共进早餐。”
这一定是一对恩爱老夫妻,我心里猜想,话题便转到老人妻子的健康上。老人告诉我,妻子已在康复室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她患了老年痴呆症。
谈话间,我已经为老人包扎完毕。我问道:“如果你去迟了,你妻子是否会生气?”老人解释说:“那倒不会,至少在5年前,她就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5年前就已经不认识你了?你每天早晨还坚持和她一起吃早饭,甚至还不愿意迟到一分钟?”
老人慈善地笑了笑说:“是啊,每天早上9点钟与我的妻子共进早餐,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一次约会,我怎么能失约呢?”
可是她什么都不知道了啊!我几乎脱口而出。
老人再次笑了,笑得有点甜蜜,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两人恩爱无比的甜蜜日子里。老人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她的确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她是谁啊!”
听了老人的话,我突然想掉眼泪,我心中默想:这种爱不正是我及很多人一生都在期望的那种爱吗?真正的爱未必浪漫,但一定是真挚的;真正的爱,在自己心间。
女儿下误才进门,似乎就嗅到了那股菠萝的味道,她很高兴地在家庭联络簿上记上一笔:“……于是我就闻到了一种菠萝的香味,真好啊!”
幸福的味道
流峰/文
屋子里弥漫着刚刷完的油漆味道。老婆要女儿上顶楼的小石屋去睡午觉,可以暂时躲过油漆的味道,留下我们清理善后。
过了一段时间,女儿打电话告诉老婆说她睡不着,于是我奉命上顶楼陪女儿玩耍。女儿和我躺在顶楼的地板上,我才发现很久没有和女儿这样单独躺着聊天了。特别是前一阵子早出晚归,有时候连和女儿说话的机会都不多。
想想没什么话说,于是就问她说:“你觉得自己很幸福吗?”女儿说:“是的。”
我要她举个例子说明什么才是幸福,女儿说:“像现在这样啊!“我再追问:“还有呢?”女儿想了想就笑着说:“还有……不用补习啊!”我又问:“还有呢?”女儿瞪了我一眼说:“你烦不烦?”我自作聪明地替她下了结论说:“大概幸福太多了,就说不完了,对不对?”
果然,女儿开始讲起一些她记忆中很愉快的事,而那些事我并不知道曾发生过。女儿说:“从前啊,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啊,夏天很热,妈妈为了节省能源,就要哥哥和我睡同一问屋子里。哥哥每天就讲一个故事给我听,长的故事要讲两天,短的故事一天可以讲两个。像海星的故事,像吃鼻子的怪物,还有厉鬼的故事……”
哥哥会讲故事给妹妹听?我一直以为哥哥只会欺负妹妹呢!女儿又回忆着另一件事情:“夏天妈妈喜欢用茶叶水来洗草席,所以当我躺在草席上睡觉时,就闻到茶叶的香味,很香呢!”就这样,我们聊了很多从前的小事情,女儿总是记得那些很小的感觉,却都是很幸福的味道。
第二天,老婆买了一个菠萝,把菠萝皮放在电扇前面吹,不久菠萝的味道开始在空气中逐渐散开,和油漆的味道混在一起。女儿下课才进门,似乎就嗅到了那股菠萝的味道,她很高兴地在家庭联络簿上记上一笔:“家里涂满了油漆,可是妈妈准备了菠萝皮,于是我就闻到了一种菠萝的香味,真好啊!”
草席上的茶叶香,漆满油漆屋子里的菠萝香,原来都是幸福的味道,可是也要有一个嗅觉灵敏的鼻子啊!或许女儿算得上是有那种鼻子的人吧?
他说:“看在你没有打麻药的分上,我跑了4条街。”我立刻就满足了,觉得幸福莫过于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刻出现。
在承受痛苦中感受幸福
李轶男/文
我曾有过一次车祸。很多人惊讶我当时的理性和坚强。有朋友问:“你怎么就不哭呢?”我只是笑笑。
其实,在那场浩劫中,我感觉到最多的是朋友给我带来的铺天盖地的幸福。
在被车撞到的那一刹那,我是有知觉的。我想:我完了。后来感觉到没有完是因为疼。火辣辣的疼痛让我渴望抓住点什么,然后,我就真的抓住了。我想,只要活着就好,活着就什么都来得及。
那个夜晚,我身上被安上了好多仪器,我被反复地搬来搬去,直到听身边的朋友说:“没事儿,不过是断了一根骨头。”那一刻我多么欣喜,甚至对着天花板微笑了一下。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比起失去生命,有什么比断一根骨头更幸福的呢?
我一直很害怕疼,小时候甚至因为害怕打针而逃学。但当时,我却坚决地对床边的所有人说:“我要手术,马上。”我固执地相信:将要来临的疼是最幸福的事。
手术之后的那个夜晚,我被告知没有申请过麻药,心里有些惶恐。朋友在电话里问:“想吃什么?”我刁难似的说:“罐头,好多好多的罐头。”我想那是午夜12点,没有罐头可以卖了吧。可当我听到粗糙的玻璃瓶子问快乐的碰撞声时,我幸福得不敢睁开眼。他说:“看在你没有打麻药的分上,我跑了4条街。”我立刻就满足了,觉得幸福莫过于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刻出现!
躺在床上的日子,除了接受探视,我无事可干。直到一个远方的编辑说:
“请你给我写文章,一定要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需要你的文章。”对我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让人喜悦的了。一个人,她还被别人需要着,她该有多幸福啊!而曾经,这种需要被我看来是那么的不值一提。
日子就是这样,当你心里暗示它是灰暗的,它也就灰暗了。可是你这样想:什么事只要努力地解决了,明天,你就仍可以幸福地喝茶、听音乐、写喜欢的文字……这样,你在解决的那一刻就幸福了起来。
这世上只有巨大的痛苦,没有巨大的幸福。但痛苦是可以拆解的,幸福不是。如果把巨大的痛苦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幸福就大于痛苦。
而幸福,就在承受并解决的过程中。
不论我走到哪儿,似乎都有些事物勾起悲痛的回忆——她喜欢的那种香水的芬芳,某种深浅的蓝色,一个爽朗的扑哧笑声。
心上的剪贴簿
芭芭拉·芭托克西/文
去年,在他大学毕业的前一天,爱子安迪和我在一处海滩上散步。在我们的头顶上空,突然有两架海军战斗机掠过。我望了一眼我那高大强壮的儿子。
“你父亲一定会为你而感到非常自豪。”我说。安迪的脸上露出古怪的神情。“今年我常想到爸爸,”他声音哽咽着说,“妈,你知道我难过的是什么吗?
我记不起他的样子了。”
安迪虽然长得像个橄榄球后卫一样的彪形大汉,可是刹那之间,我却蓦地看到他父亲的战斗机在越战中失事坠地时那个怕羞和严肃的4岁孩子。
这时安迪继续说道:“我曾经一再拼命回想,可是总……想不起来。我嫉妒艾莉荪,因为爸爸死的时候她岁数大些,她还记得。”
这种我从未想到的失落感令我惊愕。而我自己的回忆也油然而生。我们结婚那天,约翰身穿海军白礼服的那副神气模样……他在飞行学校毕业那天,我把他的银翼佩在他身上时的那种得意心情……他抱着出世不久的女儿和后来抱着儿子时,那张充满情感的面孔。
我看见安迪骑在约翰肩膀上,约翰则兴高采烈地向着阳光灿烂的加州天空歌唱:“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就在他唱的时候,一只颜色鲜艳的气球恰巧飘过。安迪当时咯咯咯地笑得多么高兴啊!我后来每次一听到那首歌,当时的情景便涌向脑际。可是安迪不记得了。不论他怎样苦加思索,他的爸爸也只不过是个在别人回忆中瞥到的影子。
我又想起最近去世的母亲。不论我走到哪儿,似乎都有些事物勾起悲痛的回忆——她喜欢的那种香水的芬芳,某种深浅的蓝色,一个爽朗的扑哧笑声。不过我有这些回忆多么幸运!现在想起来当然难过,就像约翰死后我对他的回忆那样。可是,我知道创痛会有一天消失,我的心里会有一本珍贵的剪贴簿。我将永远能从回忆中再得到我的母亲和丈夫。
我们有多少次让可以留念的回忆轻易溜走了?其实,我们有办法填满我们心里的剪贴簿,有办法制造和保存我们的回忆,使我们所爱的人永在我们心头。
那晚,妻在我怀中轻轻饮泣,好久之后才说:“对不起……我只是忘情……”
新娘
吴念真/文
蜜月旅行的最后一个夜晚,妻对即将到来的家庭生活似乎有些担忧,毕竟除了我之外,此后她必须和我的母亲、弟妹们一起过日子;而家人对她来说终究不像我这样早已自然且熟悉地相处着。
经过一番抚慰之后,她似乎宽心了些,最后她抬起头问:“我该怎么叫妈妈?”
“我们都叫‘妈’,不过你可以依你熟悉的称呼叫。”
“傻蛋,我当然跟着你叫,”她捶了我一拳说:“不过,我可得先练习练习。”
于是从进浴室开始到入睡前,她便一直轻呼着“妈!”“妈!”……脸上闪耀着欣喜且满足的光彩。
归程中游览车在高速公路上抛了锚,拖延了三四个小时,回到台北已过了晚饭时刻。我提议在外头随便吃些,但她坚持不肯。
“‘妈’一定会等我们。”她很肯定地说着又喃喃念叨:“妈,妈……”一边朝我笑了笑。
进了门,果然如妻所料,妈和弟妹都围桌而静坐候我们吃饭,那时是晚上十点。
妈拉着妻的手,让出自己的位子,而要我坐在几年来一直空着的先父的椅子上,好一会儿妈才含着眼泪低声说:“此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俩了……”
妻和妈彼此微笑相拥,盈盈的泪光在温暖的灯辉下闪烁着。
“我会好好顾着家……”妻轻轻地点头,突然叫了声:“娘……”
那晚,妻在我怀中轻轻饮泣,好久之后才说:“对不起……我只是忘情……”
“我只是突然间觉得,四个人的爱一下子都把我的心填满了,你,妈妈,我爹,还有……我娘……”她闭着眼睛任泪水流着,在我耳边低声说:“啊,傻蛋你不懂啦……”
我懂。
妻五岁时便失去了母亲,二十三年来她是两个妹妹的好母亲,但就没有机会再叫一声娘。她曾告诉过我:“……那时母亲已经昏迷不醒了。父亲抱着我靠近病床时:‘叫娘,乖,叫娘……’,我依稀记得,我好大声好大声地叫了,娘——”
我接过面包,手无力地颤抖着,心里涌动着一种酸楚的感觉,不由想起母亲常说我们是一家人。那句话刻骨铭心,永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