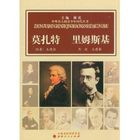收割庄稼的人从麦堆旁站起身来,舒展舒展筋骨,把烟斗弄灭。先前被卸下送去喂料的马匹又被牵回来继续劳动了。苔丝也抓紧时间吃饭叫妹妹把婴儿抱走,自己把衣服系紧,戴上皮手套,接着上午干活继续捆麦子。
直到天黑苔丝跟大伙儿才一起收工。然后他们都坐上借着月光回家去。苔丝的女伴们唱着歌,表现得极富同情心,对于她能重新下地干活表示很高兴,尽管她们也忍不住要恶作剧地唱上几段叙事民谣——关于一个姑娘进入快活的绿树林子,回来的时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生活是公平的;苔丝的遭遇使她成了大家的前车之鉴,可同时也使她在许多人眼里成了村子里最有趣的人物。她们对她的友好使她渐渐地把不愉快的往事抛在脑后,她们的轻松活泼感染了她,她甚至也变得快活起来。
然而,她在道德方面的悲痛慢慢消失了,一个新的悲痛却又滋生出来。回到家里,她悲伤地知道她的孩子下午突然生病了。这婴儿的体质竟然这样弱,本来生病以致健康完全垮掉是完全可能的;可这样的事还是使苔丝感到震惊。
这婴儿的降生是触犯了社会的一个错误,这已经被年轻的母亲所忘记;她由衷盼望娃娃能活下去。可是,事情很快就非常明显了,这个可怜的小生命马上就要被死神带走了,比苔丝最坏的估计还要早。她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万分悲痛,但她之所以悲痛,并不只是因为失去了这个婴儿。还有她的孩子尚未受过洗礼。
苔丝早已处于一种逆来顺受的心情,觉得自己过去犯了错,要是应该被烧死,那就烧死吧,让生命结束吧。和所有的农村姑娘一样,她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圣经》之中;她曾经虔诚地研读过阿荷拉和阿荷利巴的故事,明白应该从中推断出什么结论。然而,当同样的生死问题发生在她的孩子身上时情况就完全一样了。她的小宝贝就要死了,而且他的灵魂尚未得救。
到了夜深人静大家都快睡下的时候,她突然冲下楼来问,去把牧师请来。她的父亲每个礼拜天要去露粒芬酒店痛饮一番,此时刚从那儿回来,对于苔丝使家族蒙羞这件事正极其敏感。他决然说,不能让牧师进门来知道他们家里的秘密;如今,苔丝已经丢脸了,更有必要将事情掩盖起来。他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
全家人都睡下了,苔丝尽管痛苦不堪,也只好睡下。她躺在那儿,每隔一小会儿就要醒来,到了半夜,发现孩子的病情加重了。很显然这小孩正在慢慢死去——安安静静、毫无痛苦地,然而的的确确正在死去。
苔丝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都碎了。时钟敲响了一点,在这庄严的时刻,各种怪异的念头和邪恶的可能性都快速地涌入她的大脑。她幻想着,这小孩既非婚生子又没有受过洗礼,会不会被打到地狱最底层的角落里;她似乎看见大恶魔拿着一柄三尖齿把孩子抛到空中;除了这种画面,她还想象出别的许多离奇可怕的刑罚,然而这些恐怖的画面显得那样生动逼真,苔丝越想越怕,心跳得厉害,冒出的冷汗使睡衣都快湿透了。
婴儿的呼吸比先前更困难了,母亲的心情也更加紧张。一个劲地吻这小家伙却丝毫没有作用,她无法继续躺在床上,心急如焚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哦,仁慈的上帝啊,发发慈悲吧,可怜可怜我不幸的孩子吧!”她哭着说。“把你所有的愤怒都加到我的头上吧,我无怨无悔地接受你的惩罚;但救救这个孩子吧!”
她靠在五斗橱上,哀求了好久,后来猛然跳起身来。
“啊!或许我的宝宝还有救!或许那样做是一样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精神那样振奋,仿佛她的脸在她四周昏暗中闪耀着光芒。
她点起一枝蜡烛,把睡在这同一间屋子里的弟弟妹妹们都叫醒。然后她把脸盆架拉出一点儿,自己站在架子后面,往脸盆里倒出一些水,叫弟弟妹妹们围着脸盆架跪在地上,两手合十,指尖朝上。这些小孩依然睡眼惺忪,但看见姐姐那样子感到敬畏,一双双眼睛都越睁越大,就一动不动地这样跪着。苔丝从床上把那孩子抱起来——。然后将他搁在自己的一条胳膊上,挺直身子站在脸盆旁边。她的大妹妹像教堂执事助理牧师那样把打开的国教祈祷书举在她面前,就这样,苔丝开始为她的孩子施洗礼。
她穿着长长的白睡衣站在那里,看起来特别高大威严,一条粗发辫从脑后直垂到腰间。微弱的烛光掩饰了那些平时在阳光下可能暴露的小缺点,类似疲倦的眼神和胳膊上被麦茬弄出来的划痕。极大的热忱使她那张遭受不幸的脸显得纯洁、美丽,并带上一点几乎是帝后才有的庄严神态。她的弟弟妹妹跪在周围,红红的眼睛困倦地眨动着,瞅着她做准备工作,心里觉得十分纳闷,不过这会儿他们昏昏欲睡,毫无精神,所以好奇心无法积极活动。
他们当中最受感动的一个说:
“你真的要为他施洗礼给他起名字吗,苔丝?”
苔丝严肃地作了肯定回答。
“你准备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苔丝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在她给孩子施洗礼的过程中,《创世记》里的一个词使她想到了一个名字,于是她宣布:
“悲哀,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你施洗礼。”
说完以后她开始洒水,屋子里悄然无声。
“说‘阿门’,孩子们。”
弟弟妹妹们很乖地用尖细的嗓音一起说“阿门!”
苔丝接着说:
“我们接受这孩子”——还有其他一些话——“让我们给他划个十字。”
说到这她把手浸入水里,然后激动地用食指为那孩子划了一个很大的十字,同时嘴里又开始念叨那些在施洗礼时人们通常会说的话。随后,她按常规念起主祷文来,她的弟弟妹妹则用蚊子一样的声音含糊地跟着她说,直到最后才像教堂执事那样提高嗓门,再次用尖细的嗓音一起说:“阿门!”
接着,对于这场圣礼的功效信心十足的苔丝以由衷的热忱进行感恩祈祷时,嗓音大方、高昂。信仰上帝所带来的狂喜甚至使她有了神的感觉,她的脸上闪射着光芒,两颊泛着红晕,瞳孔里倒映出的烛光像钻石一样发亮。弟弟妹妹们呆呆地望着她,敬畏之情越来越强烈。此刻苔丝不再像是姐姐,而是一个威严的令人畏惧的庞然大物——是一个与他们毫无相同之处的神。
可怜的“悲哀”与世俗、罪恶和魔鬼的斗争注定只能取得短暂的胜利。天刚刚亮,他的呼吸就停止了。苔丝的弟弟妹妹醒来以后伤心痛哭,要姐姐再生一个漂亮的小孩。
苔丝在给婴儿施洗礼之后内心相当平静,孩子死了,她依旧很平静。说实话,天亮以后,她觉得自己昨天晚上为这孩子的灵魂担惊受怕得有点儿太过分了。无论理由是否充分,此刻她心里是踏实的;她认为:要是上帝不认可昨天晚上她为孩子施的洗礼,那么,因此而失去的天堂——她就认为没有什么价值。
“悲哀”这个来得意外的婴儿就这样离开人世了。他是个不请自来的家伙,他不知道“年”和“世纪”是什么;对于他来说,他存活在世上的几天便是永恒,一间茅屋就是全宇宙,婴儿时期就是整个一生,吃奶的本能就是人类的所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