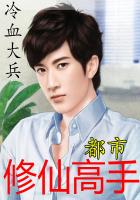就这样她经过一个又一个农场朝玛丽安写信约她会面的地方走去;因为听说那里非常艰苦,让人受不了,所以她决定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在那儿干活。在途中她不断地询问经过的每一个农场,是否有比较轻松的活儿让她做,在觉得没有希望时她又问是否有稍微重一些的活儿,到了后来,直至她最不喜欢的繁重的粗活——在农田里干活——她都一一问遍了。庄稼地里的活儿实在是太累人了,她是决不愿意主动要求去做的。
第二天傍晚苔丝来到一片高低起伏的白垩质高地。上面散布着众多半球形的古坟,好似多乳房的西布莉在那儿仰卧。
这里的空气干燥寒冷,可跑大车的路在雨后不过几小时就被风吹得尘土飞扬,白茫茫一片。树木很少,或者说一棵都没有;那些本来可以在树篱间生长起来的都被佃户——无情地弯下来并编扎成树篱的一部分。前方不远不近的地方她可以看见巴尔贝洛和奈脱柯訇的山顶,从高处看过去,它们显得低矮和谦逊,尽管苔丝在孩童时代从布雷克摩谷那一边望去它们是高耸入云的城堡。往南面,在许多英里以外,她能看见似光洁的镜子表面的一片水域,那是英吉利海峡的一部分,远离英国海岸靠近法国。
在她面前,在一块稍呈凹陷的地面上,是一个残破不全的村庄。玛丽安目前就住在这儿。看起来她好像是注定了要到此地来。周围坚硬的土地再明白不过地显示,这里的活儿肯定是最艰苦的。没办法,是停止奔波歇一歇的时候了,苔丝决定留下来,这会儿天开始下雨了。村口有一座小屋,它的三角墙突出到大路上来,苔丝没去借宿,站到那堵三角墙边上躲雨,一边望着夜幕降临。
“谁会知道我是安吉尔·克莱尔太太呀!”她说。
苔丝倚在三角墙上,背和肩膀觉得暖和,于是她发现,原来这家的壁炉是紧靠着这堵墙的,炉内的热量透过砖墙传到外面。她把双手贴在墙上取暖,又把被雨淋湿了的红红的面颊也贴在让她感到舒服的墙上。这堵墙成了她唯一的朋友。她真想在这儿站整整一个晚上。
苔丝能听见屋里的人谈话的声音,还有他们的餐盘碰出的声音。但是在村里的小道上却空无一人。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向她走近,傍晚虽然很冷,这个女人却穿着夏天的花布裙服,戴着遮阳帽。这会不会是玛丽安;待到她走近了,苔丝认出这的确正是玛丽安。这姑娘比以前长得更结实了,脸也更红了,但是明显地穿得不如以前。要是从前,不管是在哪个阶段,苔丝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跟玛丽安打招呼,可是此刻她觉得太孤独了,玛丽安向她致意她就马上迎了上去。
“苔丝——克莱尔太太——情况真的这么糟糕吗,我的宝贝?为什么你那漂亮的脸包成这个样子?是谁打了你吗?不是他吧?”
“不,不,不是!我这样包起来是免得无赖来惹我,玛丽安。”
说完她厌恶地把那条会引起别人胡乱猜测的手帕扯了下来。
“你没有用领子。”(在乳牛场苔丝习惯于戴一只小的白领子。)
“我知道,玛丽安。”
“你在路上弄丢了吧。”
“没有丢。事实上这会儿我根本不在乎外貌怎么样,所以我就没戴。”
“你的结婚戒指呢?”
“我随身带着它呢,我把它穿在一条缎带上挂在颈子上。我不想让人家想到我嫁给了某某人,让人家知道我结了婚又看到我眼下过的这种日子,真是很难堪的。”
玛丽安点头表示同情。
“可是做为一个上等人的妻子;你现在过着这种日子,真是不公平啊!”
“哦,这是公平的,很公平,这是由于我的过错。”
“你没有过错,亲爱的;这我能肯定。他也没什么过错。问题一定出在跟你们两人都不相干的什么事情上。”
“玛丽安,亲爱的玛丽安,不要再问了好不好?我的丈夫去了国外,给我的钱又都用完了,所以我得像从前那样干活糊口。你跟以前一样叫我苔丝。他们这儿要雇人吗?”
“哦,要的,他们一直都要雇人。这是一个穷地方,来的人很少他们只种一些小麦和芜菁甘蓝。尽管我自己在这儿干活,但是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来到这里真是很可惜的。”
“可是以前你也跟我一样是一个挤牛奶好手。”
“不错,可是自从我染上喝酒以后我就不挤牛奶了。啊!喝酒现在成了唯一使我快乐的事情了。你要是被雇用了,你就要去耙地。那就是我现在干的活儿,你一定不会喜欢的。”
“哦,不管干什么都行!你去帮我说说好不好?”
“你最好自己去对他们说。”
“好吧。喏,玛丽安,记住——如果我被雇用了,留在这儿干活,我们一点儿都不要谈起他。不能让他的名字受到玷污。”
玛丽安虽然跟苔丝相比显得心粗,但却值得信赖,她答应了苔丝对她的要求。
“今天晚上发工资,”她说,“要是你跟我一起去,你马上就可以问问他们雇不雇你了。你现在不快活我心里也很难过。不过这是暂时的,我知道。要是他在这儿你就不会这样,哪怕他不给你钱,哪怕他让你辛苦地干活。”
“说得不错,我就不会这样子。”
她们一起向前面走,很快就到了农庄主的屋子。这座屋子周围看不见一棵树;在这个季节,这地方一点儿绿草地也没有,只有被编筑得没有高低的树篱把休耕地和芜菁甘蓝地分割成一大片一大片的。
苔丝等在门外,待到一群干活的人领过工资以后,玛丽安才为她作了介绍。农庄主好像不在家,今天晚上是他妻子主事。得知苔丝愿意留下并一直干到圣母领报节,女主人表示愿意雇用她。现在这时节很少有女性主动来要求干活,而对于那些不分男女一样干的活儿,雇用女工当然便宜。
签了协议书以后,苔丝回到先前在三角墙边取暖的那所小屋,在这户人家找到了借宿的地方。这虽然简陋,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将给苔丝提供一个冬天的栖身之所。
当天晚上她就立刻写信给父母,把新地址通知他们,以便克莱尔有信可以转来。但是她仍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目前的困境:那会引起父母对她的丈夫的不满。
玛丽安说弗林科姆梣是一个穷地方,这话一点不错。在这块土地上,唯一一个胖胖的东西就是玛丽安自己,而她是外来的,并不是本地的。这个弗林科姆梣农庄也是属于外地的地主出租的类型。
然而苔丝还是在这块土地上留了下来。现在的安吉尔·克莱尔太太是相当有忍耐力了,这种忍耐力支撑着她。
苔丝和她的同伴开始动手耙地,这块种有芜菁甘蓝的地是有一百多英亩,是这里地势最高的一块地。每一块芜菁甘蓝块根的上面一半都已经被牲畜吃得干干净净,现在这两个女子正在用一种带钩的耙子把埋在地里的那一半块根耙出来,也喂给牲畜吃。绿叶统统被牲畜吃掉了,所以整块地呈一片没有生机的黄褐色,好比一张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巴的脸,从下巴到脑门子,只剩下那么一张皮。天上呢,也是那么一片,好比没有五官的一张白色脸皮。就这样,上下两张脸整天对峙着,褐色的脸仰视着白脸,在它们之间,只有这两个女子在褐色的脸皮上爬动,像两只昆虫。
没有一个人走过来关注;两人的动作是呆板的,机械的。她们套着一条粗布工作围单——褐色,带着袖子,背后有钮扣一直扣到底好使里面的裙服不被风吹起——脚下露着高度够到踝部的短统靴,手上戴着连护臂的黄色羊皮手套。她们头上的风帽有一块起遮蔽作用的布向下披着,使她们低垂着的脑袋现出沉思的凝固,让人看了会想起早期意大利画家作品中的那两位马利亚。
时间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过去,她们并不意识到自己在这一片景色中的这种孤苦无助的形象,也没有抱怨这样的命运对于她们来说是否合理。即使是在这样的处境,她们也还是有可能在梦想中过日子。下午天又下起雨来,可是如果不干活她们就得不到工钱,所以她们还是继续干。雨水在半空中就被怒号的狂风吹得横向飞来,直戳在她们身上像是玻璃碎片;两人站在雨里慢慢地干活,感觉到雨水从外到里,一点一点的湿透了全身,直到铅灰色的天光越来越弱,才收工回家——这是需要毅力,甚至勇气的一天。
但是,这两位姑娘对于被雨淋湿的感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强烈。她们都还年轻,干活的时候正回忆着两人一起在陶勃赛乳牛场生活和恋爱的时光,谈着使人快乐的那片绿色田野,苔丝本来不想和玛丽安谈起那个在法律上是(可以说在实际上不是)她丈夫的人,然而这个话题有抵挡不住的诱惑力,玛丽安开了头,她便不由自主地跟她一同谈论起来。于是,尽管风帽上那块起遮蔽作用的布被雨淋湿后又被风吹起,打得她们的脸生疼,这整整一个下午她们的身体很累,而精神上却生活在对于一片青绿、阳光明媚、充满浪漫气氛的陶勃赛乳牛场的美好回忆之中。
“天气晴朗的时候你还能看到离弗鲁姆谷几英里的一座山,”玛丽安说。
“啊!是吗?”苔丝说,忽然觉得这个地方还有她不曾想到过的这么一个好处。
随着下午的时间慢慢过去,玛丽安便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用白色碎布塞着瓶口的一品脱容量的酒瓶,请苔丝喝酒。她只啜了一小口。随后玛丽安自己大喝起来。
玛丽安说,“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喝酒成了我唯一的安慰,你瞧我失去了他,你得到了他;也许你不喝酒照样可以得到安慰。”
苔丝心里觉得自己的损失跟玛丽安是一样的,不过,同时她也想到自己是安吉尔的妻子,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就这一点使她同意了玛丽安所说的这种区别。
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里,苔丝在早晨的霜冻和下午的暴雨中辛苦地劳作。除了耙芜菁甘蓝块根,她们还用钩镰把甘蓝块根上的泥土和须根削去,然后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备将来使用。在这个又雨又冰冻的季节干这种活的艰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苔丝仍怀着希望。她始终认为,宽宏大量是安吉尔性格中主要的一点,她相信克莱尔迟早会来与她团聚。
玛丽安喝够了酒变得很兴奋,便从地里找出一些白色燧石,还尖声大笑,苔丝却总是板着面孔,很少言笑。她们常常将视线越过田野投向弗鲁姆谷绵延的远处,尽管她们看不见它;凝眸注视着遮蔽了弗鲁姆谷的灰色雾霭,她们会想起在那儿度过的往日时光。
“啊,”玛丽安说,“我多么想再有一两个我们过去的伙伴到这里来啊!那样的话我们就能每天把陶勃赛带到这儿,带到地里来,这样就好像几乎把往昔整个儿带了过来!”在这样说的时候玛丽安的眼睛湿润了,嗓音也柔和。“我要写信给伊丝·休特,”她说。
对于这个提议苔丝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过了两三天以后,玛丽安告诉她伊丝有了回信,答应在能够来的时候就来。
这是一个多年不遇冬季。它不慌不忙地、悄悄地来临,犹如一个棋手一步一步走棋子。一天早晨,那几棵孤单的大树和树篱间的带刺小灌木好像换上了一层动物的皮。每一根树枝上都覆盖了一层白绒,就像长出了一层毛,使它比平时粗了三倍。整个灌木和整棵大树都好像用白色线条勾画出的一幅幅醒目的素描。晶化了的空气使挂在各角落蜘蛛网显现出来——像白色毛绒构成的亮圈。
这个潮湿冰冻的季节过去之后,是一段干燥、严寒的日子。奇怪的鸟儿开始从北极后面悄悄地来到弗林科姆梣高地。这些干瘪瘦削、鬼怪似的鸟儿眼睛里含着惊恐的神情。它们的眼睛在人类到不了的北极地区,在那种人类连体内的血都要被凝固的可怕气温下,曾经看见过多少可怕的大灾难;在一闪而过的极光之下,冰山的崩裂和雪山的滑动;以及陆地和海洋位置的大变动。它们的目光看见灾难情景时所现出的那种惊慌恐惧的神色仍然保留着。它们无动于衷、一声不吭地呆在这里,用注意力关心着两个姑娘手持钩镰在地上耙弄的微不足道的动作,目的是想发现这样那样的它们能当作食物来饱餐的东西。
有一天,在这片空旷高地上空气潮湿了,但并没有下雨;空气更冷了,也没有霜冻。这样的天气使她们两人的眼珠受到刺激,使她们的额头感到疼痛,还使她们的骨头都感到刺痛她们知道这种情况意味着就要下雪了;果然晚上就下起雪来。苔丝在夜里醒来,听见茅草屋顶上的噪声响得四面八方的闹心。早晨,当她点了灯准备起床的时候,发现从窗户的一条缝隙刮进屋里的雪以及从烟囱里刮进来,铺在地上有鞋底那么厚,一走动就留下了脚印。屋外,大风雪狂飞疾走,以致在厨房里面形成了一片雪雾;不过这时候外面还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
苔丝知道今天不可能继续耙芜菁甘蓝了。待到她在那盏小小的孤灯旁刚吃完早饭,玛丽安来了,告诉她到谷仓去跟其他女工们一起整理麦秆,干到天气转好。于是,当户外的一片漆黑刚一开始转变成杂乱的灰色时,她们便把灯吹灭,穿上最厚的围裙,用羊毛围巾把脖子和前胸围好,动身到谷仓去。她们前倾着身体顶风在大雪弥漫的地里费力地走着,尽量借助于树篱躲避风雪,然而,这会儿树篱也起不了多少作用。空气被灰白的纷纷大雪弄得一片苍白,风又恣意地把雪刮得团团旋转、漫天飞舞,把人带进无色的混沌状态。但是这两个年轻女人心情还算不错,干燥高地上的这种天气本身并不使人垂头丧气。
“哈一哈!只有鸟才知道会有这场雪,”玛丽安说。“肯定不会错,这些鸟儿从北极那边来到这里一路上其实就在这场大风雪的前面。亲爱的,我相信你丈夫这一阵子肯定是在被太阳烤着呢。啊,要是他现在能看见你该有多好!这样的天气一点儿没有损伤你的美貌——其实它使你更加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