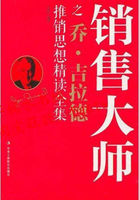“有回你小姨回来告诉我说,她们家那个赵景明,虽然神智不清楚,可身体其实也没什么大碍,就连他离婚, 也是他在清醒时主动的,他妻子不同意,赵景明一生气,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说再不离婚,他就要烧掉房子 ,他妻子这才含泪走了,你小姨说他可能是装病,”高远的母亲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后来我问,你小姨又 不说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名堂,要真是脑子坏了,为什么首先要撵走自己的妻子呢。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古 怪不成?”高远的母亲不亏是当教师的,说什么话到了最后,也不忘概括一下。
高远对这些话嗤之以鼻,不过他母亲又说了一句,让高远对这事也产生了好奇心。
“他们赵家,以前也是这个地方人,既然走了,却为什么还要租到这里来呢?”高远的母亲不再说了,起身出 去涮碗去了。
赵村这个地方高远知道,距离他们这个杨村有四里地,人丁稀少,绿村遍地,鸡犬相闻,环村有个池塘,按说 那里调养环境更好。再一联想到赵克定听到那个碾米厂位置的时候,立即兴奋地叫了起来,“好,凤凰山下, 我就喜欢那里。”这么说,赵克定是有心到这里来的了,他大学毕业后为什么这么久不上班,为什么要服侍他 叔叔,小姨一家人为什么不反对?为什么把赵景明带到这个地方来?一长串的疑问,让高远对赵克定和他的叔 叔赵景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里面,有名堂。
当时,高远更多的感觉是赵克定在追查导致叔叔赵景明变成如今这副模样的原因,如果真如他母亲所说的那样 ,赵景明赶走妻子是有所图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刑警,他可能把自己的后半生都押在追查旧事上面了。
后来的种种事实证明,高远的这种推测是正确的,但是还远远不止于此。
赵克定搬来后的第二天,高远一大早就骑着父亲的摩托车去看他,车前的货架上,放着一只老鸭,这是高远的 老妈买给赵克定煨汤喝的。
那个碾米厂正中的大门却是紧锁着的,高远屋前屋后找了找,也没有发现一个人影。这个赵克定,他明明打电 话说他来了,可是现在人呢?
高远拨通了赵克定的手机,铃声一遍一遍地响着,赵克定终于接听了,“高远,我在山上,采药。你要是着急 的话,就顺着山路找上来。”
采药?高远愣了,采什么药,难道赵克定住在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挖什么药材。
凤凰山虽然距离杨村不远,可高远来的次数并不多。山的东侧以前是采石厂,架了数十台破碎机,成天到晚轰 隆轰隆,现在整个山的东边已经被采得低洼了下去。比山脚还要低洼,从山下看去,山的东边就像是一个竖放 的大海碗,深不见底。
不知为什么,西山那边却一直没动,因此,东西两侧的绝对高度至少也有数千米。现在赵克定在采药,他肯定 是在山的西边。
高远顺着山路慢慢地向上走着,目光不自主地转向左边看了看,心里砰砰地乱跳起来。东边的采石厂当年开山 放炮,每年都要死去数十名工人,那些工人都是年青力壮,有些家属接受不了这样的残酷事实,哭着哭着,就 从西边的山上跳了下去。采石厂后来停厂的主要原因,是有工人说,他们经常能听到山下的哭声。后来又有一 个承包破碎机的老板酒后失足,不慎掉下了悬崖,破碎机就再也没有人承包了。
高远越爬越高,眼见着他已经来到了山腰,可还是没有见到赵克定的身影,他忍不住拿出了手机,正要再打电 话时,忽然听到头顶上方有人在说话。
“杨伯,你的意思是说万物相生相克,找到了这个解毒草,就能顺着摸到那个毒草?”这是赵克定的声音。
“是的,我以前跟在林医生后面学过中草药,虽说早已不给人看病了,可这些东西,我还是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林医生是个神医,经他的手,没有看不好的病人。”高远听到这个声音,倒是一怔,他听出来了,这人是本 村的杨古,一个老光棍。赵克定把杨古找到这里来做什么?
“上来吧,”赵克定显然也看到了高远,在上面招呼道。
高远迅速地顺着斜坡,拉着杂树杆,几个攀纵,来到了赵克定那里。他一眼就看到了杨古手里拿了几根长草, 不由地叫了声,“野艾草?”
杨古诧异地看了一眼高远,很奇怪地说道:“大学生,你也认得这个?”
高远撇撇嘴,没答话。杨古在村子里,算得上是个怪人。他可能长年不洗澡,不管你在什么时候遇到他,都能 闻到他身上有股臭味。更要命的是,这个人喜欢看线装书,说话也是之乎者也的,这样的人在农村,让人讨厌 是显然的。
“大学生,你在我们这里,算是中过举的了。你说说,这个草的别名叫什么?”杨古却浑身不觉高远的冷淡, 继续问道。
高远茫然地摇摇头。
“这个难怪你不知道,是林医生给它取的名字,它又叫死神的请柬。山野之民,遇蚊虫噬咬,苦不得法,以艾 薰之。艾之香,可避邪,可却毒,蛇遇之则避,然万物相生相克,它出现了,那么毒物也就近了。”杨古摇头 晃脑地说着,他本来就是半秃,这一晃脑袋,几根长发就飘落到了前额,杨古伸手一捋,那动作显得十分滑稽 。
林医生,这个名字在杨古嘴里出现了三次了。杨古至少也有60岁开外了,那个林医生估计早死了,把死人吹嘘 得如何如何厉害,别人都没办法,因为死无对证了。
“野艾草边可能会出现毒蛇,毒蟾蜍,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毒草,我没有见到病人,自然也就不清楚他到底被哪 种毒所伤了,”杨苦拿起了放在地上的竹篓,准备背到肩上,可看到赵克定诧异的眼神,他又放下了,“对不 住呀,我忘了,这些天我是属于你的。”
高远根本听不懂杨古的话意,赵克定却笑道:“是这样,我叔叔在县里市里的大医院都看过,身体倒是康复了 ,就是精神不太对,我请了杨伯给我找些偏方。”
听到这话,高远总算是明白了。在乡下寻草药制偏方,这是很多人患了疑难杂症久治不愈后没办法的办法。高 远的母亲就曾经为单位的同事找过草药。
“杨伯,今天就到这里吧,过几天我那个亲戚就会来了,到时候你帮他看一看,”赵克定客气地向杨古说道。
杨古听到这话,很是高兴,本来盛夏的天气,随着日头的升高,在丛林密布的山腰间,人都会觉得气闷。杨古 上了年岁就更是如此了。
杨古背着竹篓走了几步,忽然又说道:“小伙子,这里不错的,不但气候好,还有很多传说,呆在这里,你不 会觉得闷的。”
“传说?什么传说?”赵克定问道。
还没等杨古再说,高远就抢答了,“无外乎是凤凰山的由来呀,什么骑白马的在这里被官兵堵住了之类的。”
杨古缓缓地摇了摇头,“不是,你说的那是明朝,而我刚才提到的传说,是宋朝的。”
看着这个神神叨叨的老头,赵克定和高远相视而笑。
“明天再说吧,找草药的时候无聊,”赵克定向杨古挥了挥手。
“你给了他多少工钱?”高远问道。
“一天四个小时,付60块,”赵克定说着,眉头紧皱,“我总感觉叔叔的事,和这里有着莫大的关系。”
回到了碾米厂厂房,赵克定开了门,高远刚走进去,只觉得一阵清凉扑面而来。原来这屋既高又深,竟然可以 避掉暑气。屋里早被收拾得整齐干净,正屋算是客厅,一张圆桌,四张高腰凳放在桌旁。客厅靠后,有一个长 条木椅。高远啧着嘴,问清了卧室方向,他抬脚向西侧走去,第一间房应该是书房,有书桌,有宽屏液晶电脑 ,甚至还有一个书架,再往里一间,放着一张宽大的床。
“你叔叔来住哪儿?”高远问道。
赵克定指了指东侧。高远正要进去,想了想又缩回了脚。“你那林妹妹呢?今天不在,这只鸭看来你弄不到嘴 了,”高远笑道,“这里这么干净,肯定是她的杰作吧?”
赵克定淡淡地应道,“她呀,去上班了。周末才有空呢。”说着,赵克定接过高远从摩托车前货架那里拿来的 鸭子,走进了东边第一间房,高远跟着走进去,那里赫然是一个厨房,锅碗瓢盆一应俱全,赵克定右手持紧菜 刀,左手掐住鸭翅膀,大拇指和食指扣住鸭脖子,刀刃口对准一划拉,鸭血就汩汩地流到地上的瓷碗里。
“对了,她在哪儿上班?”高远帮不上忙,就忙着用燃汽烧开水,准备烫鸭子。
“公安局,”赵克定头都没抬。
高远一怔。
中午高远在赵克定这里吃过午饭,然后他骑上摩托车回了家。一路上,他想了很多。几年不见,克定表哥的性 情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变得沉默寡言,从前他好像没做过家务活,现在烧洗烹煮,赵克定竟然样样在行 。更让高远吃惊的,是赵克定告诉了他自己到这里来的目的。
“一是替叔叔疗养治病;二是查出导致他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赵克定缓缓地说道,他手上的筷子夹着一个 鸭脖子,却不急着往嘴里送,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高远本来想说查找原因,那是公安局的事,可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随时打电话给我 ”,赵克定爽快地答应了。
可是,高远心里并不平静,他甚至怀疑赵克定和林明媚交往的目的,难道他选中林明媚做女朋友,就是想获得 公安局内部的一些情况?林明媚是公安局档案室管理员。不管什么案子,到最后都得在她那里落户。
回到家里,高远的母亲问了问情况,听到高远说赵克定自己做饭洗衣,她愣了愣,这才答道:“你小姨打了电 话过来,说让我不要管他,她都管不了啦。这孩子,怎么城府这么深呀,唉。”
高远正准备睡一个午觉,好好休息一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外面人声嘈杂,高远忙从床上爬起来,从 楼上的窗户向下看去,只见一个又一个村民向村东边跑去,一边跑一边嚷,“出事了,出事了。”
高远下了楼,跑着跑了出去。他还没来到村东,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了,那个给赵克定挖草药的杨苦死了。
“娘的,他说这几天有了活做,有钱了,让我陪他一道去集镇上买台空调扇回来,还让我吃过午饭来叫他,我 一来,门是虚掩着的,我还以为他热,故意这样做的,我一推门进来,发现他,他就这样了,”村民杨祥春说 道,“快报警呀,我,我,我可真倒霉呀。”
有人拨打了电话,屋里的人一拨一拨地出去,又一拨一拨地进来。杨苦的房子只有一间,农村那种柴灶放在外 间,中间放了张小桌子,桌子过去,就是床,床边还有一个床头柜,柜上放着一个结满灰尘的电风扇。杨苦呈 睡姿躺在床上,他的手脚被尼龙绳紧紧地捆着,系在了床脚上。这副情形,杨苦应该死于谋杀,可令进屋的高 远奇怪的是杨苦的脸,那张脸上还有笑容。
镇上的派出所很快有干警赶到,他们所做的,只是疏散了围观的群众,然后打电话向县刑警队汇报。
“克定哥,杨苦死了,”在回家的路上,高远给赵克定打了个电话。
“哦?你现在能到我这里来一趟吗?”赵克定问道。
高远很惊诧,因为赵克定听到杨苦的死,丝毫不觉得意外,他的语气中,甚至有一种早在他意料之中的感觉。
“这么说,你并不清楚他是怎么死的?”赵克定问道。
高远点点头,他刚才把车骑得飞快,午后路面炙烤得火一般热,他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呢。
“那个杨祥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赵克定又问道。
“他,和杨苦一样,也是五保户,但他比杨苦勤快,手头也活络些,他说是杨苦让他午饭后去自己那里,和自 己一道去买空调扇的。”高远答道。
“嗯,这么说就很有意思了,我预付了他五百块钱,一个空调扇近四百块,杨祥春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赵克定若有所思。
“怎么叫有意思呢?”高远有些不高兴了。
“是这样,他是被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了,关键在于,他今天早上还和我一起去了凤凰山,杀他的人,把一切 都拿捏得很准呢,”赵克定说话的时候,眯起了眼睛,“高远,你不是说你愿意帮我吗?这样,很快就会有刑 警赶过来,你务必帮我弄清楚杨苦的死因,还有,捆他手脚的绳子是哪里来的,对了,还有一条,帮我打听一 下什么是死神的请柬。”
“死神的请柬?”高远觉得这话很熟悉,很快他就想起来了,杨苦早晨的时候手里捏了几根长长的野艾草,并 把野艾草称为死神的请柬。
杨苦把这个称为死神的请柬,是因为他的老师林医生这样教他的。
高远的眼里闪烁着光芒,难道杨苦早上说的话,是有所指?
高远的神情被赵克定看在眼里,后者拍了拍高远的肩膀道:“高远,你真是越来越成熟了。对,死神的请柬, 既然是死神的请柬,拿到请柬的人则会死掉,对吗?还有,他说这里有宋朝的传说,我想,都是值得查下去的 线索。”
“克定哥哥,你找杨苦替你采药,是早有打算,还是临时打听到的?”高远听到赵克定的分析,忽然联想到了 赵克定的角色也是很可疑,于是这样试探道。
“高远,你在怀疑我?”赵克定敏感地意识到高远在想什么,“是的,我找他是有意的,不过我没有想到他会 死。实话告诉你吧,我找他,是因为我叔叔赵景明和齐定出事后,公安局进行了调查,档案中记载了这样的一 段话,在高邦银从看守所被提走之前,他先后和我叔叔以及齐定分别交谈过。有干警回忆说,齐定和我叔叔就 是从谈话之后,怀疑都有些奇怪,甚至有点精神恍惚。”
“什么意思?”高远听不懂赵克定的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