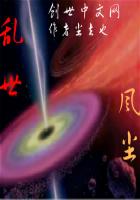插队以后才明白,夜间点灯在乡间被认作奢侈,尤其当点灯不为吃饭不为喂猪也不为赶蚊子,光为看书的时候。
自然还有我们的灯亮,不是乡间家家都用的墨水瓶般的小油盏,它冒着小黑焰柱的如豆火苗造成的光晕,恰能节俭地罩住小方罩。知青使用的是其时煤油灯的最新产品(此后看来也是末代产品,因为再也没看见它进化),那种有着长颈圆肚玻璃罩的高足灯。也不过就是指甲大的一瓣火苗,透过玻璃罩射出来,不知怎地就纯净绵长。它的光亮,照村里女人带点夸张的说法,竟是能够生产队里开大会。
既然被认定是一种浪费,那么分享或利用我们的灯亮,便是一种理所当然。每晚那一圈光晕下总是紧挤着好几个戴头巾的脑袋,那是一些埋头针线的女人,平时没有机会在灯火下干活,现在个个都奋勇得很。她们巨大肥硕身影后的半明半暗处,也有人,她们的男人或孩子,跟着女人来蹭光亮的,快活而安静地靠墙席地而坐,用草把垫着屁股。门口和窗口也有人,欲进不得的亢奋得两眼冒火的半大男孩。乡村夜晚最不安定的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处游荡,惹得村里的狗彻夜狂叫。
初下乡时似乎就是这一伙最令女知青害怕,时不时在夜间村道上与他们撞个正着,含糊地搭讪,匆忙地闪身过去,危险过后才敢回身一望,不知他们在黑夜中寻找什么。后来才明白他们寻找的是热闹,而这热闹在那时的乡村具体的就是灯亮。
不光年轻人,老年人也一样,虽然他们并不进屋,但毫无疑问是小屋的亮光才使得他们在黑地里踌躇。出去提水时碰见,照例要邀他们进去坐坐,照例婉拒说就要睡觉了,却并不见走开,灯光使他们想起了什么?是迎娶?是送丧?我无法窥知。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漫长的一生中他们只有几个夜晚灯光通明。
灯光无意中造成了乡村一次次夜间聚会,如此自然无法再看什么书或是写什么日记,但就是在这样的似看非看、似写非写中,我的近视眼还是飞快地从一百多度上升到五百多度,功劳自然归咎于那盏灯。在乡下人眼里了不起的亮灯,至多只相当于城里几支光的夜间灯。
既然说到乡村夜间的亮,自然得说乡村夜间的黑。我害怕乡村夜晚的黑,离开乡村二十多年了,前几天睡觉被一个恶梦吓醒,居然是为梦中得知我又要走夜路了。梦中天还没黑,夕阳的黄色光雾在稻田上弥散,我站在田间小路上左算右算,发现紧赶慢赶有一段路还得摸黑。一吓就醒了。如果不醒接下来我就会去拿衣服,恰如过去常做的一样。在乡间万不得已走夜路(由于我干过土记者,这样的万不得已在我有多次),我总是头上顶一件衣服,既为不让自己看见,也为不让自己听见,更为不让自己回头,这样我才能走到目的地。
自然是积攒了过多的经验教训。我不能说我曾经看到什么,因为我怕说的是我以为看到的什么。同样原因我也不能说我听到了什么。只有不回头我可以明确无误地告诉大家,凡夜行者头上都有三盏灯的说法我想不会就我知道,那是无时不刻不在庇佑后代的祖宗亡人为夜行者点着的,意在驱鬼逐邪或黑暗中任何有害东西。只是它们的存在仰仗于后代的信赖——不能回头,一回头立刻一盏灯熄灭,而我要有效地禁止自己回头。古人素来有“盲人瞎马,夜半临池”形容人处的危险境地。然而若是非得“夜半临池”的话,“盲人瞎马”不失为一种办法,相对来讲或许还是一种仁慈。
怕黑或许是人类共性。二十多年后回想知青小屋,觉得它就像乡村夜间一盏飞蛾飞蠓环绕的大灯。人有强烈的趋光性,只可惜能进化手足的人,何以不能同时进化夜视能力,致使在夜间大大受累?
“大灯”只是暂时现象,不久我们便与乡邻一样吝啬地用小油灯照亮,甚至仗着年轻机灵,摸黑吃饭下河滩洗脚上床。
并不是接受再教育的成果,灯油像当时的肥皂、食糖一样发票定量供应,一个月半斤,只够喂满我们的大灯三次,照亮我们的小屋六个晚上,想奢侈不能。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与夜间能发出幽光的自然物体的关系是大大增强了。不管是月亮是星星是萤火虫,都是我们的“天灯”——我们也像乡人一样亲昵地家常地叫它们。乡人早就使用“天灯”了,不管是田间劳作还是家庭生活。村里有几座老式的小木楼,楼壁上都有一个斗大的圆孔洞,显然不是窗子,窗子另外开着;当然也绝对不会是军事上的?望孔。它的真实作用我住到爱珍家才清楚。上楼后她不点灯,只把堵住圆孔的方砖一拨(它是灵巧地安装在墙壁里的),一道清光就奔流进来。是月光,那个孔洞是专门留待月光的,因此也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叫月洞。由此可见“凿壁偷光”并不是灯火匮乏的中国古代惟一的故事。古代建筑中早就有凿壁这设计,不过它偷的不是邻家灯光而是大自然慷慨的天光。
稍对天空作些观察便可知道,大自然并不把两个发光体同时给一个夜晚,即有亮月的傍晚星星必定不亮,从前作文时我们常在同一时空既描写亮月又描写亮星,实在是一种恣意任性。不过亮星亮月无法同时在一个天空出现实在也是误解,原因仅在简单的对比,星还在,月也还在,不过就是一个亮了另一个便显暗了。当时却悟不得,只觉得大自然也和乡人一样经济节俭。现在来看大概是对“天灯”大抱神秘感之故。
没有“天灯”的日子,大自然也有幽光。那是要贴着地面往前看的,似乎就是地面上的野革、牛粪、小虫、泥块散发的微光,站着看不见,非把脸皮紧贴毛茸茸的地皮不可。我们用这个办法来看生产队长——天黑成这样还不喊收工,把我们忘了吧?果然眼前一层稀薄的微光中有了暗影浮动,似乎是一只狗或一只猫趋近来。慌忙站起身,收拢目光,就怕队长发现我们的眼睛绿光莹莹。
说也奇怪,在乡间“天灯”下度过了那么多夜晚,能够美妙地诗意地回想起来的夜晚却不是在那时间,而是在插队上调以后。是太把它们当作灯了吗?那些亮星夜、亮月夜都太功利地在割稻、脱粒中升起和消失。要不我们就是在黑暗的小屋中睡得死沉死沉,随月洞中的那缕清光寂寞地在屋中来回袅动,对时常累得连洗脚力气也没有的我们,它实在是多情得有点多余。
那些值得记忆的夜晚要说起来也很普通,不过是“天灯”明亮的日子我习惯性地出外走走。我所上调的县城当时还像乡镇,也像乡村与城市尚未能够绝然分开。菜花地会突入城区,而街尾则像辫梢似地甩入广阔田野。沿街走走会见到夹杂其间的农舍,泊定的渔船。农舍前半敞半开的翻轩,渔船上掀开的乌篷,生来是为承受天光,承受来客的,我明白。于是我时不时要进去坐坐,倾听那些几分钟前还素不相识的主人絮絮地讲他们的生平经历。有伤逝有病痛有种种人生不如意,要放在白天放在四壁被电灯照亮的室内讲,那些烦恼会显得很烦恼,那些痛苦也一定很痛苦,而在这样的时刻,夜色如此深沉如此柔软,星月如此美丽如此忧伤,千万年亘古不变的景色,似乎足以使人生的一切烦恼苦难得到依附。要不,讲述者为什么能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呢?我内心的褶皱也在夜色浸濡中慢慢地张开。
告别县城已很久了,同样也告别了“天灯”。夜间偶尔阳台上坐坐,总是惊诧月亮和星星怎么这样远这样小这样冷漠,是耸起的楼脊把星月推远了,把天空割裂了?是浮凸的城市灯光把星月遮暗了,把天空污染了?再出外走走,除了逛商场进影院,再也不可能进翻轩坐船头,听什么人讲叙什么生平。当然更看不到那些亲切地凝视我们的大月亮、大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