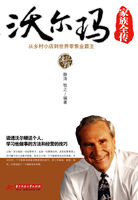看着对面哭的梨花带雨的迟微,韦岑抚额心里默默的叹了一口气,加上迟微,韦岑一周内已经接待了这是第三波向她哭诉自己婚姻有多不幸的朋友了,她从来没有发现自己还有做情感专家的潜质。
迟微哭哭泣泣、说说停停的已经接近一个小时了,前面的纸巾已经堆成了小山,从迟微连说带哭的腔调里,韦岺已经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当然这个事情的经过只是两个人导火索,重点是两人平时生活里鸡毛蒜皮的日积月累。
韦岑不禁想:现在的七年之痒是不是时间都拉长了?她们结婚七年时没看到她们痒痒,怎么这十年了都开始闹毛病了?
一个是这样,两个是这样,三个还是这样。唉,这闹心的生活。
可是韦岑自认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开解者,对着她们的眼泪她总有一种束手无措的感觉,她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宽慰她们。逞口舌之快鼓动她们离婚吧,这肯定不行,不厚道;劝她们不能改变环境就学着适应环境吧,可是听听她们的血泪史,感觉维持如此鸡肋的婚姻实在是让人无奈又无味。本着“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的道德观,韦岑劝起来都索然无味。
“你说,你说,我哪点做的不对了,我上着课,带着孩子,家务还做着,就因为这我一年只接了三门课,就在昨天我还推了我们学院教授的科研项目,幸好我们教授人好,最后还让我挂个名。”迟微如祥林嫂般如泣如诉的不厌其烦的列举着自己的丰功伟绩:“可是他倒好,昨晚他发神经还要给他妈打电话说要和我离婚。就因为我说了一句话他不爱听,这就开发始给我上纲上线,还拔拉出以前的破事儿说我看不起他,说我让他活得压抑了。你说到底是我们俩谁活得压抑,我就差没把他当菩萨供起来,我现在和他说话,我得先把这话在肚子里过三遍,确定这话没有让他发神经的因素我才敢吐出来,你说韦岑我现在这过的是日子吗?”
说到伤心处,迟微又呜呜的哭起来。看着前面空空如也的纸巾盒,韦岑起身打开一包新的放到她面前,然后坐下继续顷听。
“如果我们明天要离婚,他给他妈打了也就打了,可是我们还没到那份儿上,而且他妈心脏还不好,他就不想想如果打了,真把他妈气出个好歹来这可怎么好,然后再弄个我们婆媳不合,你说到时他怎么收拾这个局面?”
“那你就让他打嘛,到时让他来收拾残局。他敢打就应该想到这个后果,他是成年人好不好,你瞎操什么心。”实在听不去了,苏岺蹦出这么一句话,说完她就开始祈祷:主啊,原谅我吧,我不是想破坏他们来着。
“家里的活他是一点都不放到眼里去,那地板都脏成那样了,他也不去想着主动去擦擦。我让他洗衣服,他还嫌我语气不好说我冤枉他,你说他在我的驱赶下也就洗那么一两次,那也叫干活?我说他不干活一点都不冤枉他,我们俩现在真是没法交流,话说不到三句准能吵起来。”
听到这儿,韦岑忍不住想:如果生活都是这般较真儿,这生活里的鸡毛蒜皮还不得成一地鸡毛。
谁说的来着:家,就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说得真好。
家里没有谁对谁错,也分不出谁对谁错。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想让他做什么。”韦岑抽了一张纸巾递给迟微。
迟微接过纸巾擦了擦鼻涕往前一扔,没好气的说:“这还用我和他说,地脏那不是明摆着嘛,脏衣服没洗都不在那儿堆着嘛,那么一大堆还用我提醒他,我干活时也没人和我说,我不是一样天天干。”
韦岑忍不住在心里幽幽的叹了一口气,每个人的婚姻看似都不一样,但是但凡走到索然无味的地步,细细追究起来似乎又那么惊人的相似,油烟酱醋茶洗衣做饭充斥在其中,以致于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带着那么一股子味儿,就连吵架都是这股子味儿引起的。
“你可千万别用女人的思维去考虑男人,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你怎么可以一概而论。首先你得接受一点,男人在家务方面基本处于初级,所以男女在社会上才有分工;其次两个不同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的人在各自的领域里生活了二三十年以后因为婚姻这个东西走到一起,你怎么可能要求他像你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知道你的任何想法。”
“你怎么会把这么理智的理论用在两口子过日子上呢?我没结婚时我不也一样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做,可我还是为了这个家什么都学会了,他怎么就不能牺牲一下。”
“如果你非让他牺牲换来的是你们无休止的争吵,那你们是不是应该换个方法相处?”
迟微有些哑然,随后她低下头,借着擦眼泪的功夫小声的说了一句:“我不甘心。”
韦岑无奈的翻了个白眼,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说:“你要那么甘心做什么,难不成你甘心做的就是你们天天吵架?”
迟微不说话。
韦岑继续道:“多余的话我不说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你回家好好悟吧。我这儿只有一句话:这日子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两个人的相处也是这个理儿,老婆在老公面前撒个娇不吃亏,你高兴了你就多做点,你不爱做了你就告诉他让他来做,致于他怎么做什么时候做你就别去管了,记住适时的学会向生活妥协。”
说完这一堆话,迟微还是不响应,只是把擦完眼泪的纸巾怏怏的扔在面前的纸巾堆上。韦岑知道,迟微应该是有所触动了,其实她也不知道她的理论对迟微有没有效果,但是去改变总比她们这样没完没了的吵要好一些。
一个月以后的一个周末早上,初冬的阳光正好,暖暖的洒进房间里,苏岺一手挚着水壶浇花一手接听迟微的电话。
电话里迟微的声音明朗而又轻快,她和韦岑无边无际的瞎聊着,末了,她悄悄的和苏岺说:“嗯,你的方法貌似还不错,我们俩现在有改变呦。”
韦岺笑着挂了电话,然后继续浇花,阳光穿透花瓣上的水珠在房间里跳跃。
“这方法能不好吗?这可是我总结了十年的宝贵经验。”
2015·扫黄打非·净网行动正在紧密进行中,阅文集团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提交资料。
请作者们写作时务必警醒:不要出现违规违法内容,不要怀有侥幸心理。后果严重,请勿自误。(已有外站作者,判刑三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