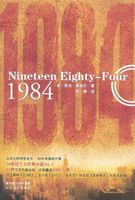他坐在前廊里读一本描写这次战争的历史书。他正在读着他亲身参加过的所有的战役。在他读过的所有书里头,数这一本最有趣了,他觉得。他多么希望书里附上更多地图。他满怀兴趣希望将来会出版附有详细地图的,读起来确实好的战史书,到了那个时候,他一定要把这些书都读遍。现在他才真正开始了解这场战争。他是个好样儿的战士。对于一名好战士来说,好多事情都不太一样呢。
大约在他回家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早上,妈妈走进他房间坐在他床上。她把围裙拉了拉。
“昨天晚上我和你老爸谈了谈,亨路德,”她说,“他同意让你晚上把汽车开出去。”
“是吗?”克里博斯说,听声音他还没有完全睡醒。“你说的是把汽车开出去?是吗?”
“对。你老爸其实已经考虑好久了,他觉得晚上不管什么时候你需要的话都可以随便把车开出去。不过直到昨晚上我们才谈了这件事。”
“我敢打赌是你要他这么办的。”克里博斯说。“不,是你老爸提出来,我们才商量开的。”
“是吗,我还是敢打赌是你要他这么办的,”克里博斯从床上坐起来。“你要下楼来吃早饭吗,亨路德?”母亲问。“好吧,等我穿上衣服就下来。”克里博斯说。妈妈走出了房间。他在洗脸的时候可以听到她在楼下煎什么东西来着。他刮完脸,穿好衣服下楼去吃早饭。就在他吃早饭的时候他的妹妹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封邮件。“喂,哈尔,”她说。“你这个瞌睡虫。都这么晚了,你还起来干什么?”克里博斯看看她。他喜欢她。他最爱这个妹妹了。“报纸拿来了?”他问。她把《堪萨斯星报》递给他。他撕开报纸的牛皮纸,翻到体育版,把《星报》打开,又折了折,然后靠水壶竖起来,用饭碟挡稳,这样他就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报了。
“亨路德,”妈妈站在厨房门口,“亨路德,请你别把报纸弄脏了。弄脏了你老爸就没法再看了。”
“我不会弄脏的,”克里博斯说。他的妹妹在桌子旁坐下来看他读报。“今天下午我们学校又要进行室内垒球比赛了,”她说。“我当投手。”
“好啊,”克里博斯说,“你的胳臂有劲儿吗?”
“别不相信,我投得比好多男同学都好。我跟他们都说是你教我的。其他女同学真的都不怎么样。”
“是吗?”克里博斯说。“我跟大家说你是我的男朋友。难道你不是我的男朋友吗,哈尔?”
“你说呢?”
“难道就因为是哥哥就不能是男朋友了?我可不这么认为。你怎么想得啊?”
“我不知道。”
“你准知道。哈尔,要是我长大了,你也愿意的话,能做我的男朋友吗?”
“行。好吧,就这么定了,你现在就是我的女朋友了。”
“真的吗?我真的是你女朋友吗?”
“嗯,真的。”
“那你爱我吗?”
“哦,呃嗯。”
“你会永远爱我吗?”
“嗯,当然。”
“那你来看我打室内垒球好吗?”
“兴许会来吧。”
“噢,哈尔,别骗人了,你并不真的爱我。你自己心里知道的。要是你真的爱我的话,你一定会愿意来看我打室内垒球的。”
克里博斯的妈妈从厨房里走到餐厅。她手里端着两个盘子,另一个盛着荞麦面饼,一个盛着两个煎蛋和几片脆炸咸肉。
“你出去会儿,可以吗,海伦,”她说,“我有话要跟亨路德说。”她把煎蛋和咸肉放在他面前,又拿了罐枫糖浆给他,让他涂荞麦面饼吃。然后对着克里博斯在桌子对面坐下。
“你可以把报纸放下一会儿吗,我的亨路德。”她说。克里博斯听话地把报纸拿下,折好。“关于以后干点什么,你有什么打算吗,亨路德?”
妈妈摘下眼镜,边说。“还没有。”克里博斯回答。
“你不觉得现在是时候做一下打算了吗?”妈妈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尖酸挖苦的意思。倒是看起来很忧虑。
“说真的,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克里博斯说。“上帝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妈妈说,“你知道的,在他的王国里不会有闲人的。”
“可是我不在他的王国里。”克里博斯说。“我们大家都在他的王国里。”克里博斯像平常那样,觉得有点尴尬而生气。“你知道我多为你担心哪,亨路德,”妈妈继续说下去,“我知道你一定受过很多不好的影响。我知道男人受不起引诱。我听你亲爱的外公、我自己的老爸对我们讲过很多关于内战的事儿,我懂那些。我一直在为你祈祷。我整天地为你祈祷,亨路德。”
克里博斯望着盘子里咸肉上正在凝冻起来的肥油。“你老爸也在担心,”妈妈继续往下说,“他认为你已经丧失了雄心大志,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查莱·西蒙斯年纪跟你一般大,他现在有一份好工作而且就快结婚了。小伙子们一个个都安顿下来了,每个人都决心要干出点名堂来;你可以看得出,像查莱·西蒙斯那样的小伙子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镇上的光荣的。”克里博斯没有答话。“别那个样子,亨路德,”妈妈说,“你知道我们都很爱你,为了你好,我想我得把你的处境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你老爸不想干涉你的自由。他觉得应该让你可以自由地使用汽车。要是你想开着汽车带哪个好姑娘出去玩玩,我们只会觉得很高兴。你知道的,我们愿意你快活。不过你得定下心来找个工作,亨路德。你老爸并不在乎你开始干什么工作。就像他说的,不管做什么样儿的工作都值得尊重。话虽这么说,然而你总得从哪里开始干点什么。今天早晨他让我跟你谈谈,兴许你愿意的话,待会儿你可以顺路到他办事处去一趟看看他。”
“就这些?”克里博斯说。“是的。你难道不爱你妈妈吗,亲爱的孩子?你不愿意为了她做点什么吗?”
“不。”克里博斯说。
妈妈隔着桌子看着他。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忍不住开始哭了起来。
“我什么人也不爱。”克里博斯说。这么说对她有什么好处呢。他没法告诉她,也没法让她明白。其实他心里知道讲了这样的话是做了桩极其蠢的事。于事无补,而且只不过会让深爱他的妈妈伤心。他走到桌子对面抓住她的胳臂。她正用双手掩着脸在哭。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他说,“其实我只是对有些事情很生气。我不是说不爱你。真的。”
他的妈妈还在继续哭。克里博斯用手臂搂着她的肩膀。
“难道你不能相信我吗,妈妈?”可怜的妈妈摇了摇头。“请你,妈妈,请你,请你相信我好吗?”
“好吧,”妈妈哽咽着说,她抬起头,凝望着他。“我相信你,亨路德。”克里博斯吻了吻她的头发。她把脸抬起来盯着他。
“我是你妈妈,”她说,“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记得吗?我把你贴着心抱着。”
克里博斯觉得心里不好受,但是隐隐约约有点恶心。“我知道,妈妈,”他说,“别伤心了,好吗,为了你,我要做个好孩子。”
“那你愿意和我一起跪下来祈祷吗,亨路德?”妈妈问。
他们一起在餐桌旁跪了下来,克里博斯的妈妈先祷告。
“现在你先来祈祷,亨路德。”
“可是我不会,妈妈。”克里博斯说。“试试看吧,亨路德。”
“我真的不会。”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祈祷吗?”
“只能那样了,妈妈。”
于是可怜的母亲替他祷告上帝,之后他们站起来,克里博斯吻了吻他母亲,走出了屋子。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他们现在的生活复杂化。然而,这样做并没有真正触动他的心。他为妈妈觉得难过,她让他再次撒了谎。他要去堪萨斯城找个工作,兴许这样做,她也就会安心了。兴许在他走之前还得再经历一场哭笑,那个多愁善感的妈妈。他不想上他老爸的办事处去。只有这件事他不想践约。他当然也希望生活过得顺顺利利。战争以前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得。唉,现在他必须得跟这样的生活说再见了。不过他还是要到学校的操场去,因为他答应了去看看海伦玩室内垒球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