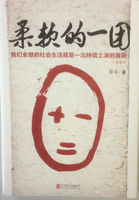他急忙奔回药房。他要为包法利配一副镇定剂,还要写两封信,要编造一套谎话来隐瞒住服毒真相,并让《明灯报》登出一个讣告,以满足那些等待消息的人们。他谎称,爱玛是在做香草奶酪时,错把砒霜当白糖了,等全永镇的人都听到这个故事时,郝梅又回到了包法利家。
他发现夏尔独自(卡尼韦先生刚走)坐在窗边的扶手椅里,直愣愣地盯着客厅的石板地。
“现在您应该,”药剂师说,“决定葬礼的时间。”“什么?什么葬礼?”然后,他用十分惊恐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啊!不,不举行好吗?不,我想把她留在这儿。”郝梅不敢再和他提起葬礼安排的事。最后还是神甫劝说,他才做出了安排。他把自己关在诊室里,拿起羽毛笔,哭泣了一阵子,才写下:
我想让她下葬时,穿着结婚礼服,头戴花冠,脚穿白鞋。头发披在肩上。要三副棺椁,一副用栎木,一副用桃花心木,一副用铅。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主张。用一大块绿丝绒覆盖她的身体。我希望如此。照此办理。
两位先生对包法利这些浪漫的想法大为惊讶,药剂师马上跑过去对他说:
“我认为这块丝绒根本没必要。而且,花费……”“这关你什么事?”夏尔喊了起来,“别烦我!您并不爱她,您走吧!”教士上前挽住他的胳膊在花园里散步。教士对他说人世的东西在天堂里完全用不上,上帝伟大而仁慈,应该毫无怨言地服从他的旨意,甚至还应该为此感激。
夏尔突然大声骂起来:“我痛恨您的上帝!”“您还存在着对抗情绪。”教士叹息道。
包法利丢下他,沿着墙边的果树大步朝前走去,咬牙切齿地用诅咒的眼神望着天空,但是连一片树叶都没有动静。
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夏尔赤裸着胸脯,最后直打冷颤,他回到家坐在厨房里。
6点钟,广场上传来了嘈杂声,是“燕子”到了。夏尔趴在窗边上,看着乘客们一个接一个走下马车。费丽希黛替他在客厅铺了一条床垫,他一头倒在上面就睡着了。
郝梅先生是个达观的人,而且尊重死者。因此,他并不记恨可怜的夏尔,晚上又过来守灵,还带来了三本书和一个做笔记的活页夹。
布尔尼贤先生已经来了。灵床已经移出了卧室,床头点着两支大蜡烛。
药剂师耐不住寂寞,不一会儿就发出一阵感慨,痛惜“这个不幸的少妇”。神甫说现在唯一该做的就是为她祈祷。
“可是,”郝梅又说,“我看,她的死不外乎两种情况:如果是上天的旨意(就像教会所说的),那么她根本就不需要祈祷;如果她至死不悔(我想,这是教士的用语),那么……”
布尔尼贤打断他的话,气愤地反驳说,不管哪种情况都需要祈祷。
“可是,”药剂师反对说,“既然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那还用得着祈祷吗?”
“什么!”教士说,“应该祈祷!难道您不是基督徒吗?”
“对不起,教士,”郝梅说,“我钦佩基督精神。首先,它使奴隶获得了自由,在社会上树立了道德风尚……”
“绝不止这些!全部的经文……”“啊!啊!说到经文,请翻开历史瞧瞧,我们都知道,经文曾被耶稣篡改过。”
夏尔进来了,一直走到床边,轻轻地拉开帐幔。爱玛的头歪向右肩,嘴巴张开着,就像脸下面开了一个黑洞,两只大拇指弯向手心,睫毛上撒满白粉,眼睛被盖住了,上面结了一层薄纱般的白色黏膜,就好像蜘蛛结的网。床单在她的胸口和膝盖之间都陷了下去,在脚趾尖处又高了起来。夏尔感到仿佛有个巨大而沉重的东西压在她的身上。
教堂的钟敲了两下。他们听得见河水流动的声音。布尔尼贤先生不时大声地擤一下鼻子,而郝梅则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
他站在她对面,好看得更清楚些。他看得出了神,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以致忘却了痛苦。
他想起了一些昏睡和催眠术的故事。他心想,只要精诚所至,也许会她起死回生。有一次他甚至凑近她的脸庞,低声喊道:“爱玛!爱玛!”他急促的呼吸,吹得蜡烛的火焰摇摇曳曳。
天刚亮,包老太就到了。夏尔抱着母亲,又是大哭一场。老太太也劝起他节省葬礼费用。夏尔对此非常恼怒,她只好闭口不提。他催促她快点进城,去购买所需要的东西。
夏尔整个下午都是一个人呆着。贝尔特被送到郝梅太太家去了。费丽希黛和勒弗朗索瓦大娘一起在楼上卧室里守灵。
晚上,有人前来吊唁。夏尔站起身,握着客人的手,却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然后,大家挨个儿在壁炉前面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半圆。他们低着头,摇晃着二郎腿,不时地叹息。他们都已极端厌烦,但谁也不想第一个走。
郝梅9点钟再来的时候(这两天来,就只看见郝梅在广场上跑来跑去),带来了一堆樟脑、安息香和香草,还拿来了满满一瓶氯水,用来驱除疫气。这时,女佣、勒弗朗索瓦太太和包老太正在给爱玛换衣服。她们拉下又长又硬的罩布,一直盖到她的缎鞋。
费丽希黛呜咽着说:“啊!我可怜的太太!我可怜的太太!”
“看呀,”客栈女老板叹息道,“她还是那么漂亮,如果不知道,真以为她会立刻起来呢。”
她们俯身给她戴花冠。非得把她的头抬高一点不可。这时,一股黑色的液体从她嘴角流了出来,好像她又在呕吐一样。“来,吸口烟!”他对药剂师说,“吸了烟就不犯困了。”
远处传来持续不断的狗叫声。“您听见狗在叫吗?”药剂师问。“据说狗能觉察到死亡,”神甫应道,“就和蜜蜂一样,有人死了,它们会离开蜂窝。”郝梅没有批判这些迷信说法,因为他又睡着了。
布尔尼贤先生比较能熬夜,又小声嘀咕了一阵,很快,也不知不觉地垂下了头,那本厚厚的黑皮书从手是滑落到地上,他也打起呼噜了。
他们俩面对面坐着,肚子凸起,脸皮浮肿,皱着眉头,在激烈的争辩之后,两人都屈从于人类的共同弱点,他们一动不动地睡着,就和那具尸体没有多大区别。
夏尔走进来,没有弄醒他们。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向她道别。
香草还在冒烟。一缕缕蓝色的轻烟和从窗外飘来的雾气混合在一起。月明星疏,夜色柔柔。
大滴的蜡油滴落在床单上。夏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橙色摇曳的烛光,显得疲惫不堪。
爱玛的缎裙在月光的照耀下波纹粼粼。他似乎看到她的灵魂已从躯体里逸出,朦朦胧胧地融入周围的环境和寂静中,在夜色徐徐的轻风和湿润的香气中袅袅上升。
他突然恍惚看见她坐在托斯特的花园里荆棘篱笆边的长凳上,一会儿又看见她在卢昂,在街上,在他们家门口,在贝尔托的庭院里。他还听见那些在苹果树下尽情跳舞的男孩子们的笑声。卧室里充满了她头发的香味。她的长裙在他怀中发出火花迸裂般的窸窣声。就是她现在穿着的这件长裙!
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他的心怦怦直跳,他用手指尖慢慢地撩起她的面纱。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惊醒了另外两个人。他们又把他拖到楼下的客厅里。
过了一会儿,费丽希黛上来说,他想留爱玛的一绺头发。
“您去剪吧!”药剂师说。可是她害怕,他就只好亲自动手。他的手抖得厉害,以致把她鬓角的皮肤戳了好几个口子。最后他壮起胆子,胡乱剪了两三剪子,在她那覆盖着漂亮黑发的脑袋上留下了几块空白。
药剂师和神甫重又继续守灵。他们不免时时打个盹,每次醒来就相互指责。随后,布尔尼贤先生在房间里洒圣水,郝梅则往地板上倒氯水。
费丽希黛想得很周到,事先在五屉柜上为他们准备了一瓶烧酒、一块奶酪和一大块奶油圆蛋糕。大约凌晨4点钟,药剂师实在熬不住了,就叹气说:
“我是真饿了!”神甫也不用人请,出去做完弥撒就赶回来,然后他们又吃又喝,还一边傻呵呵地笑着。也不知为什么,在经过忧闷的守夜之后,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愉快的感觉。神甫喝干了杯中的酒后拍着药剂师的肩膀,对他说:
“我们将会成为好朋友的。”他们在楼下前厅里碰到刚来的工人们。夏尔不得不忍受两个小时锤子敲打木板的声音。然后,他们把她放进栎木棺材里,又把这副棺材套放到另外两副棺椁里。最外层的棺椁太大,不得不用垫褥里的羊毛绒填在空隙里。最后,一棺二椁都刨好,钉好,焊好了,就把灵柩抬到了门前。房门大开,永镇镇民开始集合。
鲁奥老头此时赶到了。他在广场上一望见黑纱,就晕倒了。
十
爱玛去世后36小时,鲁奥老头才收到药剂师的信。郝梅先生考虑到他年老体衰,有意把信写得含糊其辞,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发生了大事。
老人先像中风似的倒了下去。随后他想女儿还活着,但也可能是死了……他急忙穿上外套,拿起帽子,套上马刺,就快马加鞭地赶来。一路上,鲁奥老头气喘吁吁,焦急万分,有一次差点从马背上掉下来,因为天黑得看不见路,他只能靠声音辨认方向,他感到自己快疯了。
天破晓了,他看见三只黑母鸡栖息在一棵树上。这个凶兆吓得他直哆嗦。他赶忙向圣母许愿,要送给教堂三件祭披,还要赤脚从贝尔托的公墓一直走到瓦松维尔的小教堂。
他一到马洛姆,就高喊店家撞开了店门,直奔荞麦袋,把它倒进牲口槽,又往里面倒了一瓶甜苹果酒。喂饱了小马,立即飞驰而去。
他安慰自己,他们一定会把她救活的,医生们肯定能找到特效药的。他记起以前听说过的那些起死回生的奇迹。
随后,他又感觉她已经死了。他似乎看到她就仰躺在大路中间。当他勒住马缰,幻影立即消失了。
到了坎康普瓦,他一口气喝下三杯咖啡,给自己壮胆子。
他想可能是别人在信里写错了名字。他从口袋里找出了信,却不敢打开。
他甚至还猜想,可能是有人想报复而开了个玩笑,有人喝醉了,搞个恶作剧。再说,她要是真的死了,应该会出现预兆的,可他没有感觉!田野上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湛蓝的天空下,树枝在风中摇曳,一群绵羊悠闲地走着。他望见小镇了。人们看见他伏在马背上,使劲抽打着马,飞驰而来,马肚上出现一条条血淋淋的痕迹。
他认清现实了,一头倒在包法利怀里痛哭起来:“我的女儿!爱玛!我的孩子!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了?”
包法利哽咽着答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飞来横祸!”药剂师分开这两个人。
“现在别提那些可怕的细节!以后我再对老先生说吧。瞧,大家都来了。好了,冷静些,振作起来!”
可怜的夏尔想表现得精神些,反复地说:“好……要鼓起勇气!”“对!”老人大声说,“见鬼,我振作精神!我要送她走好这条路。”钟声响了,一切准备完毕了。要进行葬礼了。他们并排坐在祭坛的祷告席上,看着三个唱经班成员不断走来走去地唱着诗篇。蛇形风管乐师拼命地吹着。布尔尼贤先生穿戴整齐,尖着嗓门唱着。他举起双手,张开双臂,在圣体龛前鞠躬。莱斯梯布多瓦拿着鲸骨杖,在教堂里转来转去。棺材停放在斜面桌旁边的四排蜡烛中间。夏尔直想站起来把这些蜡烛全吹灭。
然而,他尽量使自己做到对宗教的虔诚,幻想来世能与她重逢。他想像她只是去了遥远的地方旅行,要待很长时间。但他一想到她就在棺材里,一切都结束了,她就要被埋在地下,感到无比的悲愤。
这时,从教堂深处传来一阵包铁木杖有节奏地碰撞石板地面的单调的响声,在侧道突然停住。原来是希波利特,他穿着宽大的褐色外套特地装上了那条新的假腿,艰难地跪倒在地上。
唱诗班的一名成员在正殿里绕了一圈,请求人们布施,一个个铜钱投进银盘中。
“请快点呀!我支持不住啦!”包法利喊着,气呼呼地扔给他一个五法郎的硬币。
这位神职人员深深地向他鞠了躬,表示感谢。人们唱着圣诗,一会儿跪下,一会儿又站起,简直没完没了!夏尔记得很久以前,他和爱玛一起来做弥撒,他们当时是坐在右边靠墙的地方。钟声又响了,椅子发出一阵凌乱的推拉声。抬棺材的人把3根杠子从棺材底下伸过去,抬起棺材走出教堂。
这时,于斯丹正从药房里出来,他又急忙退了回去,脸色苍白,步履蹒跚。
人们站在窗口看送殡的队列。夏尔走在最前面,身子挺得直直的。他装出一副坚强的样子,对那些从小巷或家里出来,加入送葬队列的人们点头致谢。
6个男人,一边3个,抬着棺材,慢慢地走着,喘着粗气。神甫、唱诗班成员和两名神甫的侍童吟唱着《哀悼经》。他们抑扬顿挫的声音,在田野中回荡。每到小路的拐弯处,就看不见他们了,但那根银色的大十字架却总是显现在路两旁小树的顶端。
女人们都披着风帽下垂的黑色披风,拿着点燃的蜡烛跟在后面。听着一遍又一遍的祷告,看着昏黄摇曳的烛光,闻着烛油和道袍枯燥的气味,夏尔感到晕眩。
那缀有白色小珠的黑色棺垫,不时被风掀开,露出棺材。疲乏的杠夫走得更慢。棺材一路颠簸着向前行进。
男人们一直走到墓地尽头的草地上,那是已经挖好了一个墓穴。
神父祈祷时,大家在墓穴旁围成一个圈。人们把棺材移到四根放好的粗绳上面。夏尔看着棺材一点点地放进墓穴。最后,大家听到落地声,绳子吱吱响着被抽了上来。
布尔尼贤接过莱斯梯布多瓦递给他的铲子,一边用右手洒着圣水,一边用左手使劲推下一大堆土。一颗颗石子落到棺木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好像是来生的回响。
神甫把圣水刷递给他旁边的郝梅先生。郝梅先生庄重地接过来,又把它传给夏尔。夏尔跪在土里,抓起大把的土往墓穴里扔,一边喊道:“永别了!”还连连向她送去热吻。他爬过去,要和她埋在一起。